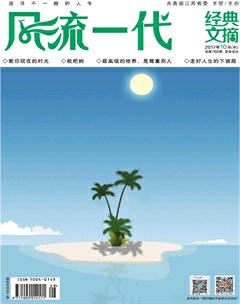為什么人容易過敏?
一碗蘿莉面
過敏可以說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了,花粉過敏、海鮮過敏、藥物過敏……這些相信每一個人都不陌生。導致過敏的東西叫“過敏原”。過敏的癥狀是相似的,每個人的過敏原卻有所不同。過敏原如果是食物、藥物倒還好避免,但如果是花粉、冷空氣或者日光那可就郁悶了,一不小心就中招了……
那么,“過敏”這件看似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事,為什么會存在于我們的身體里?
過敏是怎樣發生的?
日常生活語境下,人們所說的“過敏”往往指的是I型超敏反應。植物花粉,真菌孢子,動物皮屑或羽毛,昆蟲毒液,一些食物比如海鮮、芒果等等,都是常見的過敏原。過敏原其實是一種抗原,在過敏原的首次刺激下,免疫系統分泌一種叫IgE的抗體,這個過程叫做“致敏”。有些人的免疫系統比別人更容易產生IgE,他們就是傳說中的“過敏體質”人群。
“致敏”以后,如果人體不再接觸過敏原,就不會有事。一旦再次接觸到相同的過敏原,免疫系統就收到了IgE發來的警報,迅速召集人馬趕來。這批大部隊中最主要的成員是“肥大細胞”和“嗜堿性粒細胞”,正是它們分泌的物質導致了過敏的各種癥狀:輕則起疹子、皮膚瘙癢、眼睛發紅、打噴嚏、流鼻涕,重則喉頭水腫、過敏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對于過敏,可千萬別掉以輕心,這個小惡魔可是有一百種方法來要你的命。
載入史冊的過敏
盡管“過敏”聽起來是個有點新的概念,但它其實已經被人類觀察了數千年了。最早關于過敏的文字記載,可能是公元前2641年埃及法老美尼斯被黃蜂蜇死的記錄。
除了當事人難受,過敏還以各種方式影響著歷史的進程。古羅馬克勞迪亞斯大帝的兒子布里塔尼庫斯對馬匹過敏,只要一騎馬就會“全身長滿皮疹,眼睛充血,以致什么也看不見”。因此,他失去了在貴族中騎領頭馬的資格,取而代之的是他父親的養子。這位養子就是后來古羅馬臭名昭著的暴君——尼祿。
而據作家托馬斯·摩爾的著作記載,英格蘭國王理查三世還利用過自己的過敏反應進行政治斗爭。他知道自己對草莓過敏,所以在與政敵哈斯廷斯見面之前先偷偷吃了一點草莓。接下來在見面中,理查三世身上起了很多蕁麻疹,他由此指責哈斯廷斯對自己下了詛咒,并要求將其斬首。
為什么要有過敏機制?
我們知道,過敏原常常只是一個警報,過敏的主要癥狀是由免疫系統釋放的各類物質引發的。為什么本該保護我們免受傷害的免疫系統,在這方面這么大驚小怪,瘋狂打擊自己人?換句話說,我們為什么會過敏?
簡單地說,這個問題在科學界至今沒有答案。不過,科學家們一直在根據觀察到的現象提出能解釋過敏意義的假說。
過去一個流行的假說是“寄生蟲論”。科學家們認為,當遠古衛生條件不好的時候,我們的祖先的免疫系統發展出了識別寄生蟲表面抗原、并分泌IgE的能力。這些IgE能極其迅速地動員免疫細胞趕到皮膚、黏膜等處,阻礙寄生蟲的進一步入侵。劍橋大學的寄生蟲學教授大衛·鄧恩說:“你只有大概一小時的時間(來保護自己),否則寄生蟲就會開始在體內存活繁殖。”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衛生水平改善,雖然寄生蟲的威脅不再像當年那么巨大,但免疫系統仍對它們保持著相當的警惕。而一些過敏原的結構就與很多寄生蟲的表面抗原相似。當我們接觸到過敏原時,免疫系統以為這是寄生蟲入侵的信號,立刻舉旗出兵,實際上卻有點小題大做。“過敏癥狀只是人類抵御寄生蟲感染時一個不幸的副反應。”鄧恩說。
不過,耶魯大學免疫學教授、當代著名免疫學家魯斯蘭·梅德斯托夫也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過敏不僅僅是個副反應或警報,它應該有著更加積極的意義。很多過敏原確實是有害的,它們可能激惹細胞膜,損傷細胞,破壞細胞內的蛋白質。他說:“如果你仔細想想過敏的所有癥狀——流鼻涕、流眼淚、打噴嚏、咳嗽、瘙癢、嘔吐、腹瀉——這些癥狀有一個相同之處,那就是它們都在試圖把毒素排出體外。”由此他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過敏癥狀是身體把有害的過敏原排出體外的一種方式。
梅德斯托夫還假設這些IgE對機體其實有保護作用,而不是僅僅能誘發難受的過敏反應。他在小鼠體內再次注射了大劑量的PLA2。這次,從未注射過PLA2的小鼠發生了致命性的低體溫,而已注射過PLA2致敏的小鼠發生過敏反應,但卻逃過了PLA2本身導致的嚴重癥狀。
與鄧恩的觀點不同,梅德斯托夫把過敏的發生比作家庭警報系統:“有時你判斷家里進了賊,不是通過看見了賊,而是通過打破的窗戶。”他認為雖然有時候過敏反應也很惱人,但總體來說,這種機制的存在還是利大于弊的。
過敏的人正在變多嗎?
在西方發達國家,過敏性鼻炎、哮喘等過敏性疾病也在20年前乃至更早開始呈現出了上升趨勢。以澳大利亞為例,1994年到2004年,因全身性過敏反應住院的案例翻了一番,其中有此反應的5歲以下兒童更是增加了5倍。相對而言,發展中國家里過敏性疾病的發病率往往較低。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
目前的一個主流解釋叫做“衛生假說”。這種論點認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衛生條件不如發達國家,孩子們暴露于寄生蟲或其他病原體的幾率更大。早期暴露于寄生蟲能幫助免疫系統發展出自我調控機制,將免疫應答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相比之下,如果環境過于清潔衛生,這種自我調控機制發展不出來,接觸到過敏原以后,可能會產生非常劇烈的反應。這就像一隊訓練有素卻又無仗可打的士兵,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就以為是強敵入侵,結果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在另一方面,也有觀點認為過敏的增加源于人類生產出了越來越多的化學合成物質,它們對免疫系統發出了越來越多的警報。前面提到的梅德斯托夫就持此論點。但一如過敏機制的意義問題,過敏發生率上升確切原因是什么,目前也還沒有明確答案。
目前,“寄生蟲論”和“排出有害物質論”兩個學說誰更符合過敏的實質,科學界還在爭論不休。但無論結論如何,“過敏”這件事很可能將永遠伴隨著人類。所幸的是,科學家們對過敏的認識正在逐步加深,而未來我們可能也會找到更好的方式,來與“過敏”共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