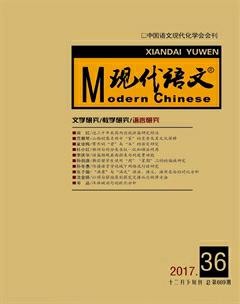語言是“聽”出來的
摘 要:本文通過分析語言的符號性、語言和思維的關系、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得出“反復聽”在語言學習中具有重要性的觀點,闡述了普通話學習中“聽”的內容、“聽”的方法、“聽”和“練”的關系等問題。
關鍵詞:聽 語言 符號 思維 方法 普通話
我國播音主持藝術事業從1940年12月31日第一次播音起,到今天百花爭艷的創作,已經走過了70多年的發展歷程。這70多年里,我國播音主持藝術事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幾代播音主持藝術教育家在對這些經驗和理論進行了總結的基礎上,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播音主持藝術教學理論,如在語音、發聲、朗讀、即興口語表達等方面都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理論和訓練方法。但就目前對“語音”的教學來看,還缺乏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這是播音主持藝術教育的缺憾。《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9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播音員、主持人是全國人民語言的模范,應該練就純正的普通話語音。普通話的推廣有利于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秦始皇統一六國,實現了“書同文”,完成了文字的統一。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地快速發展,特別是隨著高科技迅猛發展,我國人民交往日益頻繁,“語同音”,即全國推行通用語已經提上日程。播音主持語言是經過訓練的藝術化的語言,廣大人民學習普通話則以交流順暢為目的。但兩者在語言物質層面,即語音規范、語法正確,要求是一致的。因此,掌握正確的語言學習方法,不僅對于播音員、主持人專業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對普通話推廣工作也具有重要的作用。純正的語音是“聽”出來的,規范的語法是“聽”出來的,流暢的語流是“聽”出來的。總之:語言是“聽”出來的。播音主持藝術的學習和教學、普通話的推廣工作如果建立在“聽”的基礎上,將事半功倍。
一、語言是“符號”系統
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聲音是語言符號的物質形式。由于語言聲音最簡便、容量最大、效果也最好,因此在人類長期發展過程中,選擇語言聲音符號作為交際工具。語言是代表事物意義的符號系統,其中,詞是語言中最重要的成分。詞分為實詞和虛詞,實詞代表實實在在的意義,虛詞表示語法關系。詞是聲音和意義相結合的統一體。如“水”和“water”兩個詞都代表“由氫、氧兩種元素組成,在常溫、常壓下為無色無味的透明液體,被稱為人類生命的源泉的無機物”[1]。但“水”和“water”分別從屬于漢語普通話和英語兩個不同的語言符號系統,中國人聽到“水”知道它代表的意義,英美人聽到“water”也知道它代表的意義。實際上,語言就是由這樣的一個個實詞符號在語序和虛詞的輔助下組成的系統。因此,掌握了實詞符號就知道了實詞符號所代表的是哪一類事物,掌握了虛詞符號就掌握了修辭、語法關系。
符號包含聲音形式和意義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兩個方面,但聲音符號和意義具有音義結合的任意性,即符號和其所代表的事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這是語言符號的本質,這也是世界上擁有眾多語言的原因。如漢語中“教師”的語音形式是“jiào shī”,義為“傳授知識、經驗的人”[2]。代表這個釋義的聲音形式在英語里是“/ti:t??r/(teacher)”,在西班牙語里是“/pr??fes?(r)/ profesor陽性”或“pr??fes?r?(陰性)”。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著名的哲學家荀子就說過:“名無固宜,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3]恩格斯也說:“正和負。也可以反過來……北和南也一樣。如果把這顛倒過來,并且把其余的名稱相應地加以改變,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確的。這樣,我們就可以稱西為東,稱東為西。太陽從西邊出來,行星從東向西旋轉等,這只是名稱上的變更而已。”[4]形式和意義的結合完全是社會“約定俗成”的,這是語言符號的本質,而意義是聯系字詞和語音之間的橋梁。符號要經過人們約定俗成,才能起交際工具的作用。
二、通用語是“自上而下”推行的符號
語言符號的創制具有音義結合任意性的特點,但在一套語言符號系統中,某一語音與某一語義一旦結合起來,它對該語言的使用者就具有了強制性。因為對于該語言使用者,語言符號需要長期使用,如果隨便更改,就會影響交際。因此,每個人從出生起,就生活在一套現成的語言符號里,只能被動地接受這套語言符號系統。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交往頻繁,而語言的多樣性卻阻礙了社會交際,通用語應運而生。“通用語”是使用不同語言的人進行交際的媒介,它是不同語言背景的人進行交際所接受的一種共同語。如:普通話是我國不同地域、民族之間的通用語,英語是國際間交際的通用語之一。通用語的形成有很多原因,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是政治和經濟。“方言經過經濟集中和政治集中而成為一種統一的民族方言。”[5]我國自古以來就注重通用語的使用,早在夏朝就出現了“雅言”。周朝以后,各朝隨著國都的遷移,雅言的基礎方言和標準語音也隨之修正。中國古代漢民族的經濟政治中心是北方中原地區,因此漢民族共同語就以中原地區的方言作為基礎方言,以王朝京城所在地的地方話作為標準語音。金、元、明、清四代建都北京。北京作為國家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北京話影響逐漸加大,并作為通用語言傳播到全國各地。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以北京話為官方用語——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主導推廣的標準音,使北京話成為在全國范圍內流通最廣的語言。這為北京話成為當今民族共同語的標準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世界其他各國通用語的形成也有著類似的過程。如公元1066年,法國人威廉一世征服英國,在法國人統治英國的三百余年間,法國人在英國大力推行法語作為英國的通用語。這是現代英語詞匯中存在大量類似法語詞匯的原因。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它雖然沒有全國統一的通用語,但50個州中已有31個州通過立法規定英語為通用語。
通用語一旦經過國家立法推行全國后,就具有“自上而下”的強制性,要求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遵守通用語言文字使用的規范、標準和有關規定。我國現行的語言文字地位一律平等,但通用的范圍不同,分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民族自治地方、少數民族聚居地方通用語言文字兩個層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普通話、規范漢字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在全國范圍內通用,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數民族聚居地方。在民族自治地方和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當地通用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可同時使用。這就用法律的形式確定普通話、規范漢字作為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地位、公民學習和使用普通話以及規范漢字的權利和義務。endprint
三、語言的習得過程
語言和思維形影不離,人在思維時總得用一種語言,人在學習一種語言時也是在學習一種思維方式。思維是指人類通過比較、分析、綜合以認識現實世界的過程和能力。嬰兒從生下來到學會母語,需要花幾年的時間。從兒童學習語言的過程可以看出,語言的習得過程是這樣的:開始的時候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一周歲左右會說一些單個實詞,后來逐漸發展到會說幾個詞的句子。大致五六歲時,能自由運用語序排列各種實詞、虛詞,造出各種各樣的句子。學說話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認識世界的過程、思維發展的過程。
首先是獨詞句階段,即用單獨實詞表示事物的階段。如:孩子看到“車”,聽到大人說“chē”,他就將語音“chē”和“車”這種事物聯系了起來;看到“船”,聽到大人說“chuán”,他就將聲音“chuán”和“船”這種物體聯系起來了。詞是一類事物的名稱。孩子經過模仿和糾正,學會了一個詞,把詞與它所代表的那類事物聯系起來,這樣他就認識了這類事物。在這個階段,孩子只會用單個的詞表達意思,思維能力主要表現為詞和某類事物聯系,初步學會了概括。其次是雙詞句階段,孩子學會詞語的組合造句。如:孩子借助于詞識別了車和船以后,又聽周圍人說“大車”“小車”,“大船”“小船”,他因此又辨識出了“大車”和“大船”的共同點,“小車”和“小船”的共同點,進而把物和物的特征區分開來。后來如果他看到“飛機”,他就可以把“大”和“小”加在“飛機”上,區別兩架大小不同的飛機。這時,孩子不僅注意到不同事物之間的區別,而且會把統一的事物分析成不同的要素,如“大”“車”,還注意到不同事物的共同特征,初步學會了抽象。“車跑”“船動”之類的句子也是在這個階段學會的。
獨詞句階段和雙詞句階段是孩子學習語言過程中的重要階段。獨詞句體現了對實詞和事物聯系的認識。雙詞句體現了造句的基本原理,即選擇需要的詞,按照學會的語序將實詞組合成句。雙詞句階段時,孩子已不僅知道詞與事物的聯系,而且已知道詞與詞之間的關系。之后進入實詞句階段,進而掌握表示語言單位之間的關系的語序和虛詞,逐步擺脫事物具體形象的影響而越來越注意語言本身。孩子在語言學習過程中,從周圍人那里學來的現成的句子是有限的,但孩子能夠理解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句子,也能說出從來沒有說過的句子。可見,人類通過學習詞匯和語法,造成無數千變萬化的句子。
四、“反復聽”是學習語言的根本技巧
母語學習是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習得的。除了母語以外,學習其他任何一種語言,都很難獲得如同學習母語一樣的語言學習環境。因此,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是學好通用語、外語的重要保障。
從語言是一套符號、語言和思維的關系、孩子學習語言過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語言是“反復聽”出來的。人類從出生以后,就是在不斷的“反復聽”的過程中,將一定的語音與意義聯系在一起,從而掌握了母語。因此,“反復聽”是學習語言的不二法則。但很多語言學習者忽略了母語學習對于普通話、英語等其他語言學習的借鑒作用,尚未領悟到“反復聽”在語言學習中的重要性,沒有掌握到好的學習方法,即使花了很多時間卻沒有取得好的學習效果。每個人看問題都有自己的角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葛蘭老師在談到學習方法時,要求學生“背誦課文,以積淀文化素養”[6]。葛蘭老師是北京人,她從小在普通話的語言環境中長大,她的語音是比較標準的。對于她來說,播音主持藝術專業的學習是進一步加強口腔控制、字音控制以及文化積累,因此“背誦課文”這種方式適合于她。但對于某些方言地區的學生,反復背誦課文即是在反復重復方言,這樣背誦得越多,離普通話標準語音就越遠,南轅北轍,無法實現普通話語音的糾正。市場上有很多普通話、英語教材講授語法、詞匯知識,這無可厚非。但語法、詞匯的學習是輔助學習者盡快掌握語言規律的捷徑,很難代替學習語言“反復聽”的過程。語言學習必須經過“反復聽”的過程才能學成。
“反復聽”是學習普通話的真諦,那么需要聽什么、聽多少遍呢?學習通用語就如同練字一樣,是學習一種規范。因此選擇學習的模板非常重要——這是直接關系到學習效果的第一步。很多人練習毛筆字將王羲之、顏真卿的字作為練習的模板,練習鋼筆字則將龐中華的字作為練習的模板。練字是眼看手寫,學習語言則是耳聽嘴說。普通話的學習也需要很好的“聽”的材料作為學習的模板才能取得良好的學習效果。如果模板沒有選擇好,就會被不純正、甚至錯誤的發音引向歧途,而一旦形成錯誤的發音習慣后,又需要時間加以改正。由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組織審定、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編制,姚喜雙、侯玉茹、于芳、方明四位老師錄制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是學習普通話的首選模板。
語言是一套傳遞信息和感情的符號系統。學習語言的目的就是熟練記憶、掌握、運用這套符號系統,而記憶、掌握、運用語言符號的規律和要訣在于重復:語音的標準度、語法的正確度以及語調、語感的培養都是在“反復聽”的過程中才得以記憶、學成的。母語的學習是在無數次反復、試錯、糾正的過程中學到的。學習普通話也需要大量、反復的聽的過程才能將普通話語音學到位。“Listen to the tape back and forth,until you can remember the lesson”[7]。“反復聽磁帶,直到通過“聽”,將課文背下來”。[8]這是學習英語的正確方法。這種學習方法完全可以作為學習普通話的借鑒,即反復聽《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聽20遍以上,直到其中的文章都能隨口背下來為止。完成“反復聽”《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之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出版的系列朗誦作品也可以成為“反復聽”的模板。
反復聽的過程中,不僅記憶了語音、語調,還培養了語感。語感是比較直接、迅速地感悟語言文字的能力,是語文水平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對語言文字分析、理解、體會、吸收全過程的高度濃縮。“反復聽”標準普通話,是積累、培養語感的重要途徑,也應該成為中小學語文教學的重要內容。但由于外國中小學語文考試只考查書面語言能力,因此絕大多數中小學重視書面語言教學,而忽視了口語教學。事實上,在“聽、說、讀、寫”四項訓練中,“聽、說”能極大地促進“讀、寫”的發展。endprint
任何科目的學習一般都要經歷一個由模仿到創造的過程。語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際,在此基礎上,語言還具有審美功能。播音員、節目主持人作為語言工作者,不僅要向受眾傳遞信息,還要通過“準確規范、清晰流暢;圓潤集中、樸實明朗;剛柔并濟、虛實結合;色彩豐富、變化自如”[9]的語言給受眾以美感享受。特別是由于普通話語音“頭腹尾”的特點,對發音的口腔控制、吐字控制有著很高的要求,必須經過專業的訓練才能獲得優美的發音。語言的訓練應當建立在足夠量的“反復聽”、語感培養的基礎上。如果“反復聽”得不夠,那么語音、語調記憶就不夠準確,在練習的過程中,發音、語流就會有偏差,不純正,很難取得良好的練習效果。
學習語言,還需要學習語言中的思維方式。思維是人腦的機能,是對外部現實的反映;語言則是實現思維、鞏固和傳達思維成果(思想)的工具。思維和語言統一構成人類所特有的語言思維形式,它們是人類意識中兩個互相聯系的方面。人類具有思維能力,但各個民族思維方式卻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一個民族認識客觀世界的特殊方式,學會一種語言也就學會了該民族的獨特的思維方式。語言的差異性不僅表現在符號系統不一樣,而且也表現在思維方式具有民族性。詞匯意義和色彩、語法規則都體現著不同民族的思維特點。漢語習慣使用不及物動詞造句,而英語則大量使用及物動詞造句。“我昨晚睡得好”對應的英語是“I had a good sleep last night.”英語是一門將事物和人放在同等重要地位上的語言。漢語則是以人的動作為中心。這些思維方式可以通過學習得以掌握,但要真正作到說話出口成章,如果沒有“反復聽”作為基礎,將是很難實現的。通過“反復聽”,可以記憶、進而習慣于一種語言的思維方式。作為我國的通用語,普通話的思維方式基本上是被全國人民接受的,但對于一些南方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的人來說,普通話的思維方式和方言思維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別,因此在學習普通話過程中,需要學習普通話的思維方式,而普通話的思維方式的學習,“反復聽”是最好的途徑。
注釋:
[1]http://baike.baidu.com
[2]http://baike.baidu.com
[3]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
第3版,第27頁。
[4]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
第3版,第27頁。
[5]姚喜雙《播音主持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3月第1版,
第213頁。
[6]葛蘭老師2010年6月在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講課錄音。
[7]孫崢,2004年4月在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講課錄像錄音。
[8]郝險峰,2005年3月在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系講課錄音。
[9]吳弘毅,《實用播音教程——普通話語音和播音發聲》,中國
傳媒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258。
(羅佳 北京 首都師范大學科德學院傳媒學院 102602)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