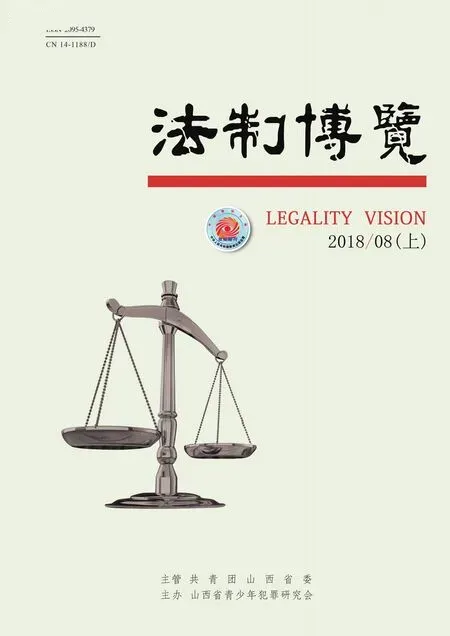未成年人犯罪的三重分析及立法重構
張 源 王 妍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未成年人犯罪特點之分析
未成年人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但是由于教育的缺失、低俗暴力文化的傳播等社會因素和未成年人認知力、自制力、辨別力較低等自身因素的綜合影響,使得未成年人犯罪呈現日趨增多的趨勢。因此,有必要針對未成年人的犯罪特點進行分析研究,從而更好的實現刑法的懲罰犯罪與保護法益的目的和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之間的銜接。筆者分別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和北大法寶網中以“未成年人”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并結合其他學者的觀點,總結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幾個主要特點:
(一)主體年齡呈現降低趨勢
進入青春期這一特殊時期的未成年人,思想逐漸成熟,其已經有了自己的對社會的初步認知,并且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日漸形成,自我意識逐漸變得強烈,極易產生逆反心理與家長和學校對立。在這個階段,未成年人對社會上的事物缺乏正確的辨別能力,極易被各種不良因素所誘惑,蒙蔽心智,做出后悔莫及的事情。另外,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原因,很多家庭都只有一個孩子,家長們對孩子過分的寵溺和不正確的教育引導對于日趨降低的未成年人犯罪年齡有一定的影響。
(二)主體文化層次較低
未成年人在犯罪前多數都未曾得到系統的文化教育,極易受到社會不良文化環境的影響,這將直接導致他們對社會上的事物缺乏正確的辨別能力。文化教育的缺失也導致法制觀念的淡薄,更有甚者,在其犯罪以后竟還毫無意識,渾然不知其已經違法犯罪,將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本該在學校接受教育的年紀,卻過早的進入了社會,受到不良社會風氣的影響,一步步走向了違法犯罪的地步。
(三)預謀性案件所占比例逐漸增大
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和應用,大量犯罪題材的影視、文學作品涌入普通大眾的生活。未成年人極易受到影視、文學作品的影響,為了追求所謂的刺激,效仿其中的犯罪手段。對于搶劫、強奸等常見的暴力型犯罪,他們于平常生活中形成的法律認知,足以使其辨清是非,做出較為恰當的選擇。部分未成年人已經明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是在犯罪,甚至已經懂得的利用自己未成年人的身份來規避法律責任,其主觀惡性已經十分明顯。①
(四)單獨作案減少,共同犯罪增多
樂于合群是未成年人的特點之一,未成年人正處于叛逆期,不愿意接受別人的約束,此階段的未成年人有著自以為成熟的思想,認為家長們對其正確的教育和引導是對自己的過分約束,習慣按照自己的行為方式去做事情。尤其是對于一些有著相同經歷、相同想法的同齡人,更樂于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效仿影視劇中的社團、幫派,行著所謂的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哥們義氣。相關研究也有所揭示,當前已出現一些由未成年人組成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團伙。
二、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基本原則之分析
(一)從寬處罰原則
我國《刑法》對于從寬處罰原則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其第十七條條第三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應當”就是必須,即對于此年齡階段的未成年犯罪人,即使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段殘忍,危害很大,在量刑時也必須從輕或者減輕處罰。②
(二)不適用死刑原則
死刑的執行方式分為: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執行。在現行法律下,對于未成年人,不僅不能適用死刑立即執行,也不能適用死刑緩期執行。但是在我國1979年頒布的第一部《刑法》中卻出現了例外情形。《刑法》(1979版)第四十四條規定了犯罪時不滿十八歲不適用死刑。但是在其后又加入了已滿十六歲不滿十八歲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別嚴重,可以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一規定,首先是違反了自己確立的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的規定,削弱了法律的嚴謹性與權威性;再者,犯罪行為特別嚴重并沒有具體的標準,賦予了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可能會造成同案不同判的情況出現。這一情形直到1997年才被改變,《刑法》(1997版)將原《刑法》(1979版)之四十四條后半部分刪去,從而正式確立了未成年人不適用死刑原則。
(三)盡量適用緩刑原則
由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主體特殊性,決定了對未成年犯在判處刑罰時要同成年犯有所區別。未成年人相較于成年人,其自控能力和辨別是非的能力較差,但是其可改造性較強。對未成年犯判處刑罰的目的不光是對其過錯行為的評價,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刑法改造未成年人,而緩刑就十分符合這一目的。通過緩刑,不僅可以讓未成年人認識到自己的錯誤,還能讓其回到社會上接受監督改造。而且緩刑的適用能有效地避免未成年犯罪人因為被判處短期自由刑而產生“交叉感染”等不利影響。③對未成年人盡量適用緩刑這一原則的確立,筆者認為應當追溯至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雖然我國《刑法》(1997版)規定了可以宣告緩刑,但是其并沒有針對未成年人單獨設立,并沒有達到對未成年人的特殊保護的目的。
(四)雙向保護原則
這一原則區別于上述原則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不過分的強調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而是綜合考慮未成年犯和受害人之間利益保護的平衡。首先,未成年人犯罪確實給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造成了一定后果,對受害人產生了法益侵害,必須要進行懲罰才能維持社會穩定,安撫受害人,保護其法益,同時維護法律權威和社會秩序;其次,未成年人犯罪有其復雜性和特殊性,對于未成年犯的懲罰要慎之又慎,區別對待,既要達到對未成年人的懲罰目的也要盡量給予未成年人以特殊的保護。該原則在我國的確立應當追溯至1982年聯合國大會通過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北京規則》),該規則明確了對未成年犯適用刑罰時對未成年犯合法權益和社會利益就要兼顧。
三、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之分析
如前文所述,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分為三段,并且以十四周歲作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該設置立法者自有其考量,但是從1979年至今,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立法背景和立法時所考量的因素也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動。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逐漸增多,年齡逐漸降低的背景下,若還是以十四周歲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筆者認為恐有不妥之處。對于以未達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為由逃避刑罰處罰的惡意嚴重我國現行法竟無法進行規制,難道這竟成為罪犯逃避處罰的理由嗎?法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難道變成了未成年人的避風港了嗎?犯罪筆者擬對我國現行法政策進行分析,結合國外的相關立法,代籌我國未成年人形勢政策之改進。
2015年10月18日,13歲的劉某(初三)與兩位玩伴趙某(12歲,初二)、孫某(11歲,小學六年級)在湖南邵東縣廉橋鎮新廉小學殘忍地殺害了鄉村教師李某,之后掩蓋現場,照常上課上網。此事在當地引起軒然大波,如此惡劣的事件何以會在三個未滿14周歲的在校學生與受人愛戴的教師之間發生呢?究其原因竟只是三人發現教師李某獨自一人,想殺人搶錢。在實施一系列的犯罪行為之前,劉某說“我們還有14歲,就算打死人了,也不用坐牢。”這就證明劉某已經很清楚地認識到未滿14周歲的人的一切不法行為都不承擔刑事責任。也正如他所說的,三人被公安機關抓捕后送往了當地的工讀學校進行教育、改造。
此種事件并不是個例。2013年重慶,一名年僅10歲的小女孩用近乎殘忍的和其年齡不相匹配的方式結束了一名嬰兒的性命。2013年11月25日,10歲的女孩李某在電梯內對一名1歲大的男嬰原原拳打腳踢,后又將男嬰扔出電梯外,并疑致男嬰從25樓墜落受傷。被害男童的父母報案后,公安機關以施暴者李某未滿14周歲為由不予立案,被害人父母只能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
不可否認,未成年人犯罪不僅是因為其自身的原因,還有社會和家庭深層次的原因,家庭教育引導的缺失和社會管理監督引導的弱化都是造成未成年人日趨增多的原因。但案件既然發生了就要尋找解決方法,很明顯,我國刑法現行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應對當前頻發的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已然乏力。而且,由于法律的明文規定,使得部分犯罪的未成年人無法受到法律的制裁,其也無法認識到自己的所做事情的社會危害性,無法達到法律教育的目的,司法的公平公正也在人民群眾心中有所動搖,也明顯違背了“罪行相適應”原則。
我國在制定第一部刑法典時經濟還比較落后,文化教育并不完善,物質生活水平相較于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還有很大差距,甚至解決溫飽都是問題,一個14周歲的少年有可能才剛剛上小學或是根本沒有上學,其對社會的認知與自身的思想并不成熟。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立法者以十四周歲為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更為妥當,也符合當時中國的國情。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獲得了快速地發展,尤其是近些年,信息爆炸式的傳播,使得未成年人接觸到越來越多的各色各樣的信息。這些信息正在潛移默化的影響著未成年人,使得未成年人的心理提前成熟,甚至達到了成年人的心理水平。在此背景下,若還是對未成年人適用原來的法律,已經明顯不合理。既然不合理,就需要改變。如果不變,那么何談懲罰犯罪,何談保障人權,何談刑法目的之實現?當法律規定成為了法律適用的絆腳石,當立法精神成為了犯罪分子逃避制裁的理由,當法律這一不容踐踏的凈土成為了犯罪費的避風港,何談法治國家,何談依法治國?
四、刑事責任年齡之立法重構
針對我國目前因未成年人犯罪未達最低刑事責任年齡而逃脫法律制裁的困境,筆者認為應當引入英美法系中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某些情況下通過“惡意”來“補足年齡”,這樣既可以避免部分未成年人憑借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的保護來逃避刑法懲罰,也可以到達懲罰犯罪之目的和對未成年犯的改造。
(一)“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概述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理論雛形出現于5世紀中葉的的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其對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和我國相同,均為十四周歲,但是,依據其教會法的規定,十二周歲至十四周歲間的未成年人,并非絕對不會承擔刑事責任,而是要依據特定案件發生后通過對未成年人的認知能力、控制能力、辨認能力的分析來進行判斷。
近代法學意義上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出現在英國,是由英國著名律師布雷克斯頓在《英國法釋義》中提出的,布雷克斯頓在書中首次闡述到要對未成年人的主觀惡意進行區分認定,對于明知是錯而執意為之的應認定為惡意,此時年齡雖未達十四周歲也應追究其刑事責任。④受布雷克斯頓的影響,英國在刑事司法領域開始逐漸適用“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并且形成了對于刑事責任年齡的三分法:“(1)十周歲以下的人不能成為任何犯罪的主體;(2)己滿十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推定不能成為任何犯罪的主體,但是如果檢察官能夠證明被告人具備了刑法規定的主客觀要素以及被告人知道自己行為的錯誤性,那么就可以推翻這個推定;(3)十四周歲以上的人是成年人,可以成為任何犯罪的主體。在“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確定以后,其所規定的可被推定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年齡范圍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也在不斷變化。比如:1933年英國在《兒童和少年法案》第五十條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改為八周歲;而在1963年,又根據社會環境的變化在《兒童和少年法案》的第十六條中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改為十周歲。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不斷提高體現了英法律對社會的適應,但是也引起了英國國內針對“惡意補足年齡”規制的質疑。最終,英國議會于 1998 年頒布法案,廢止了對 10-14 歲的兒童可推翻的無刑事責任能力的推定。我國香港地區也引入了“惡意補足年齡”規則。香港地區以十周歲和十四周歲將刑事責任年齡分為三個區間:(1)十歲以下的為完全無責任年齡時期。并且該規定不可突破,不能以任何原因對十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施以刑罰。其規定在香港《2003 年少年犯(修改)條例》第三條。(2)十歲以上十四歲以下的為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時期。(3)年滿十四歲的為完全刑事責任年齡時期。根據該規定,對于十歲以上十四歲以下的未成年人,除非檢方能夠證明該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明知是犯罪行為而故意為之,否則他們將會被推定為無刑事責任能力人。并且,對于該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其實施犯罪時的年齡越小,推翻這一推定所要求的證明力度就越大,對證據的要求也越充分。⑤
(二)“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制度重構
我國刑法確立“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制度,需要從制度層面賦予其現實可操作性,在制定該制度時應當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惡意”的判斷標準。惡意與否屬于主觀心態,很難通過具體的細則予以規定,也很難直接有證據予以證明,因此,對惡意與否的判斷應當建立在對未成年犯的全面調查之上,綜合考慮其認知水平、理解能力、行為方式、人身危害性。筆者建議,此處的認知水平應當以相同年齡段的未成年人普遍的認知為準;理解能力也應當限于較低水平,即有一定的辨析能力即可;行為方式,應當限于以常人所不會運用的方式去侵害他人的健康權與生命權;人身危害性指的是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不能僅簡單的預估可能性,而應當對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家庭環境、成長經歷等進行全面的分析調查。
2.主體范圍。在美國的法律體系下,十四周歲是分水嶺,十四周歲以下的美國法律善意的默認其缺乏刑事責任能力,但是如果控方能夠提供打破善意的證據,證明被告人具有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那么被告人就會面臨刑事懲罰。但是七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就算善意被打破,也不承擔刑事責任。而在我國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下,筆者認為,主體范圍界定在已滿十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為宜。
3.案件類型。我國《刑法》第十七條規定了八種限制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應當承擔責任的罪名。“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主體范圍是已滿十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根據舉重以明輕,對于“惡意補足年齡”規則也應當限于此八種罪。
4.我國實行嚴格的“罪刑法定主義”,因此若引入“惡意補足年齡”規定,我國刑法必須增設關于“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的條文,筆者建議在我國《刑法》第十七條第一款后邊增設該條款:已滿十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明知行為的性質但仍故意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 注 釋 ]
①張遠煌,姚兵.從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點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全面貫徹[J].法學雜志,2009,11:20.
②趙秉志.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問題研究(二)[J].山東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1,3:8.
③胡江.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新動向——以《刑法修正案(八)》為視角[J].江西警察學院學報,2011,5:91.
④張鴻巍.少年司法通論.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89.
⑤胡春莉.未成年人刑罰制度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