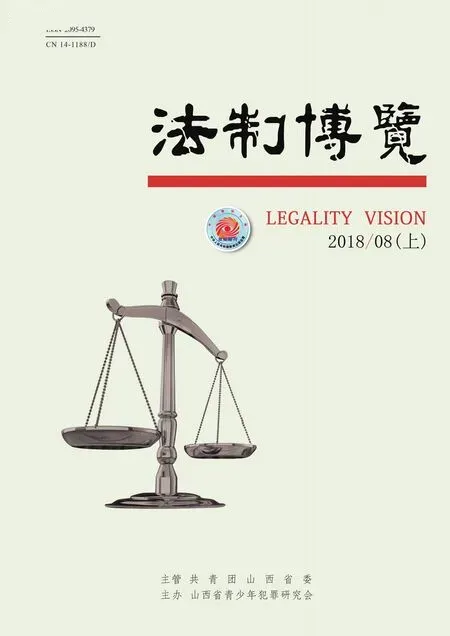淺析共享經濟中的居間合同關系*
吳靜瑄
江蘇警官學院,江蘇 南京 210012
在大數據時代信息革命浪潮的驅動下,我國“互聯網+”這種共享經濟模式已經滲透到從消費到生產的各產業環節,推進著產業創新與轉型升級。現有的共享模式主要存在于交通、住宿、辦公和金融相關行業,如國外的Uber、Airbnb等企業,國內的滴滴出行、螞蟻短租等企業。這些共享經濟模式下的企業對傳統經濟模式產生巨大影響外,還對法律制度產生深遠的影響[1]。除了市民熟知的租賃合同、承攬合同等,在共享經濟發展的影響下,居間合同及其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也受到了實踐的挑戰。
一、共享經濟模式內部法律關系分析
愛彼迎(Airbnb)是一家聯系旅游人士和家有空房出租房主的服務型網站,旨在為用戶提供多樣的住宿信息。共享經濟包括三個法律關系主體分別是共享經濟平臺、共享資源提供方以及共享資源需求方。共享平臺為了達成閑置資源提供方與資源需求方之間的交易,要承擔相關平臺運營與管理等服務。閑置資源供給方將自己的相關信息憑借共享經濟平臺所提供的配套服務設施發布,以達成實際發生于共享資源供給方和資源需求方兩個民事主體之間的交易。對于需求方要想順利完成交易,實現閑置資源的合理利用,必須謹慎鑒別共享平臺所發布關于提供方閑置資源的相關資料和數據。
因此以共享平臺為媒介的經濟模式中會產生兩種合同。一是合同由供給方與需求方自行決定是否成立,共享平臺在提供相關信息后退出法律關系,也就是傳統的線下供需雙方服務合同;二是共享平臺與閑置資源供需雙方各自訂立合同,即線上的共享平臺介入合同。
二、傳統居間合同的特征
根據《合同法》,居間人所受委托內容的不同,居間合同可分為媒介居間合同指居間人僅為委托人提供訂約媒介服務的居間合同;指示居間合同指居間人僅向委托人報告訂約機會的居間合同[2]。
與一般民事法律合同對比,傳統的居間合同包括五個顯著特征:第一,居間合同的標的是居間人實施的具有居間性的行為。居間人為委托人提供訂立合同的機會,不直接參與雙方的談判交易。第二,居間人須按委托人的指示和要求進行居間活動。第三,居間合同是雙務有償合同。居間人必須向委托人索要報酬,若是沒有報酬,則不能成立居間合同。居間合同成只需要供需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產生效力,不以當事人的現實交付為成立條件。第四,居間人報酬請求權具有不確定性。委托人對于居間人的給付義務依附于委托人與第三人是否能夠順利訂立合同,居間人對于合同訂立與否沒有實際的控制權,所以居間人獲得報酬的權利也不受其自身控制。第五,居間人具有相對獨立性。
三、共享經濟模式對居間合同的影響
共享平臺與閑置資源供需雙方之間所形成的民事法律合同關系,雖然帶有傳統居間合同的外部特征,但是這類合同更近似于民事關系中的雙邊代理。在共享經濟模式中,共享平臺其獨立性不如傳統居間合同強,共享平臺參與合同訂立的過程。在合同訂立之后,共享平臺仍存在于法律關系中,并且需向供需雙方承擔一定的義務。在共享交易模式中,共享經濟資源供需雙方是否能夠順利達成交易合作,關鍵在于共享經濟平臺能否分別與雙方訂立合同。因此,共享平臺有義務對供需雙方進行一定約束,供需雙方也應當履行共享平臺單方提出的各種條件。
然而,居間合同履行過程中存在明顯的雙邊道德風險問題,并且往往成為合同訴爭的根源[3]。為了避免此種情況的發生,共享平臺大多會對雙方交易進行適當監管。從平臺的角度來說,共享平臺必須對需求方與供給方的基本信息進行審核;建構較為完善的信用體系,以確保陌生人之間的交易安全;建立完善的監督和懲罰機制,特別是在目前立法缺失的情況下,要保證供需雙方在權利利益受到侵害時,可以使用簡便、有效的救濟方式進行自身權利維護。
四、結語
作為新型電子商務模式,共享經濟模式固然會帶來一國的經濟發展,提高國民生活質量。但是缺少法律規制的共享經濟在迅速膨脹的過程中,也使得司法實踐中的民事糾紛處理更為棘手。因此,明確共享經濟模式中居間合同權利義務、責任主體等方面的界限,才能更好地了解共享經濟居間合同中不同于傳統居間合同法律特性,在共享經濟實踐領域更好立法、司法、執法,以實現社會經濟與法律制度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