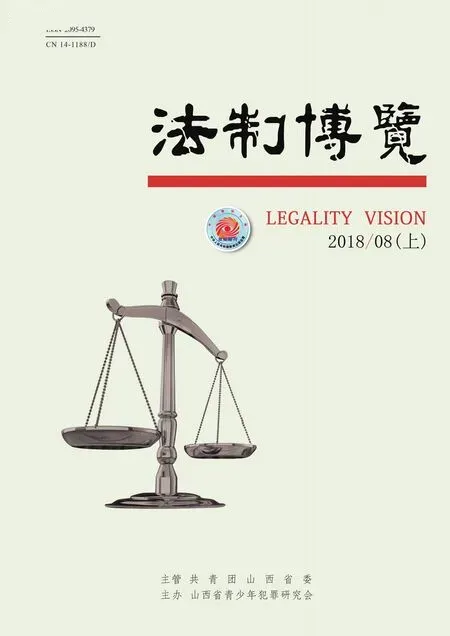關于環境法院建立的價值目的與追求研究
——從回應型法看
梁 真
江西理工大學,江西 贛州 341000
一、問題意識的引入:現實存在
針對有關數據的研究表明,有關環境問題專門的環境法院受案數量是明顯少于傳統法院量。環境法院作為解決當前環境生態污染的案件的一種重要路徑,但是受案量比之傳統法院受案量低的現實狀況,不少學者為此對于環境法院的建立存在質疑的言論,對于此其存在背后的價值目的與追求探討成為說明上述現象存在的更合理的解釋。上述的現狀勢必是一種環境法院發展中的必經磨難。
二、環境法院建立的價值目的與追求
“回應型法”視域下環境法院的價值目的與追求的分析,首先需厘清環境法院當前的現狀;在現狀的實際基礎上,以其“回應型法”當做成有效的知識工具,在應然的層面上,進而探尋法律目的價值導向。筆者選擇從回應型法的角度出發,深度探索環境法院建立背后的所體現的價值目的與追求。
(一)追求正義、司法公正
對于環境立法來說,環境的價值觀將成為代表環境法目的理念的基礎和出發點,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在倫理道德觀念上的對“正義”所表現出的最為科學、最為完美的一種表述形式。[1]以此,將正義作為環境法院的價值目的與追求顯得尤為重要,會成為一種重要的思想淵源。在回應型法中,尤其強調重視公共利益與實質正義。[2]
(二)鼓勵公民參與
從回應型法的角度來看,將公民參與作為環境法院的價值目的與追求是符合當前的國情與現狀的。環境狀況的大大改善,僅僅從政府社會層面出發,似乎總是心有力而力不足。提高整個公民群體的環境生態安全意識,使之切切實實感受到自己所做就是為自己為子孫為民族的大事要事。著重將公眾參與到的人群從城市拓展到農村,將群體從高知識分子的群體轉向受教育水平較低的群體,開展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加大農村城鎮地區偏遠地區的環保投入,鼓勵當地群眾對于依然存在的環境污染大膽起訴訴告。
(三)樹立環境法院的權威
環境法院價值目的與追求的設定必須要具有肯定性的權威。實現這一目標,第一要將普遍化的目的轉化為具體的目標。目的能告知“我們真正要干的事”。[3]環境法院被筑入到解決當前環境污染事業的社會結構,它能使其判決具有活力并因此而獲得徹底的權威。在環境法院的實踐中對這種權威性的追求,會引起法律變化,不符合當前的需求的被否定和矯正,符合的繼續一如既往的支持。在當前的中國現狀中,新環保法被稱為史上最嚴的環保法,以法律重新修訂部分法條的形式,從企業、環保部門、當前所處的整個政治社會經濟環境出發,對有關的處罰問題進行明確的規定,使之在環境法院做出更為符合案件程度本身的最佳判決。
(四)踐行可持續發展方針
人類的進步必須不斷依賴技術革新和聯合行動,因此它們常常被用來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然而,在人類發展中出現的環境問題、以至于無法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卻威脅著人類自身的生存。對于當前存在的有關環境問題,這是不能滿足全體人民基本需求的,這是全體人民需求的“絆腳石”。環境法院應竭盡所能義不容辭。確立了明確的目標、嚴格地執行法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對環境有害的副作用。可持續發展作為一條探索實踐中找到的維持生態平衡維持地球生態系統繁榮穩定的發展道路,將其作為環境法院的價值目的與追求是再合適不過的。
(五)審判的專業性
“回應型法”要求法律能夠更好地回應社會需求,因此這對法律機構的能力來說也是一個挑戰,法律機構也應相應地提升自身的能力來實現此目的。環境訴訟是具有特殊性的,環境法院審判的案件的專業性特別強,這是因為此種類型的案件具有隱蔽性、復雜性和長期性的特性。并且有關環境的生態功能和損害認定的有關問題必須足夠專業。另外,環境法院的法官人員,必定要具備相應的環境專業知識,以致形成專門化的法官隊伍。環境訴訟案件的集中審理審判,從價值追求與目的角度,充分利用了司法手段專業性達到保護生態環境的最終目的。
(六)滋養法治建設
回應型法理論中存在的一種要求就是要通過對社會當前存在的問題與當前大眾的需要的認知,以其目的的引導來完善立法、司法和執法等活動,解決社會存在的弊端,滿足當前的社會需要。當前,環境法院的建立抓住了中國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期。但是環境法院建立也面臨著愈多的社會問題,環境法院對于諸如環境生態污染問題的解決,不僅僅是社會問題得到有效解決,并且對于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提供了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