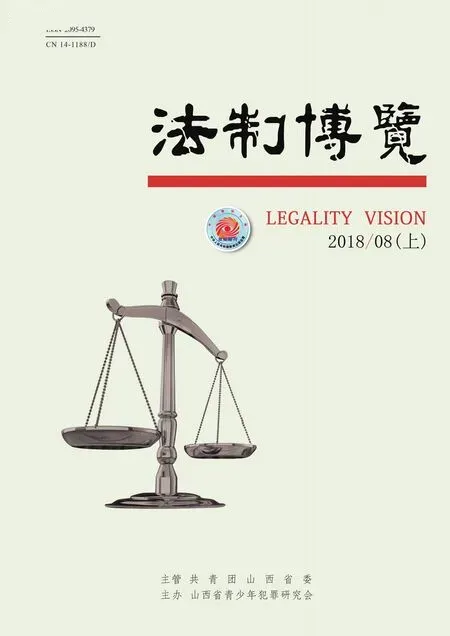論私法公法化的發展
——以商法強制性規范為切入點
梁恒瑜
天津工業大學人文與法學院,天津 300387
一、商法強制性規范的概念
對于商法強制性規范概念的定義問題,本文將其分為商法規范和強制性規范的界定兩個方面。
關于商法規范,我國目前尚未存有完整成形的商法典,因此仍無統一說法。本文在此參考王保樹教授對商人法規范淵源的論述,試從商法規范的淵源角度進行定義:1、民法通則關于調整商事關系的一般規定;2、商法單行法中調整某一類具體商事關系的規定;3、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釋;4、商事法規(包括地方性商事法規)的規定;5、商事規章。
強制性規范是與任意性規范相對的概念。我國有法理學家認為此二者的劃分是根據權利、義務的剛性程度;而我國的私法學家則更偏重于從法律關系當事人的意愿問題進行解答,史尚寬先生認為,強行法,指不問當事人意思如何,必須適用之規定,與任意法相對。強行法又可分為強制規定與禁止規定,強制規定是指法律命令為一定行為的規定,禁止規定則為法律命令不為一定行為的規定;梁慧星先生認為,強行法,因所規定的事項涉及國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的維持或基于其他公益上的理由,不允許個人依自由意思予以變更而要求必須遵守,即排除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
從上述相關表述可見,商法規范作為私法,自然秉承著一般私法即民法的基本概念和思想。因此本文對商法強制性概念的定義遵從民法意思自治原則并結合法理學說中的權利義務,具體表述為:商事活動中,商事主體不得以協議的方式或者單方行為等意思自治方式進行變更的內含國家強制的商法規范。
二、商法強制性規范的公私法價值分析
“法的價值是一定的社會主體需要與包括法律在內的法律現象的關系的一個范疇。這就是,法律的存在、屬性、功能以及內在機制和一定人們對法律要求或需要的關系,這種關系正是通過人們的法律實踐顯示出來的。”由此,可見法的價值可從與人的需要相聯系,因此本文中對法的價值定義為法本身所固有的、不依賴于人和人的需要而獨立存在的、能夠在法律實踐中對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的滿足具有積極意義的一種特性。
(一)商法強制性規范與私法價值
私法主要是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在本文中尤其指平等主體間的交易活動所涉及的關系,因此筆者將私法價值概括為效率與安全,且以效率為重,而一般私法中的誠實信用、公序良俗等民法原則認為是私法價值的映射。
而商法其本身基本原則決定了其特有得商法性質的強制性規范。目前我國對于商法自身特色的基本原則與價值的論述紛爭不斷,既有范健教授的商法四原則,顧耕耘教授的三原則說,趙萬一教授的五原則說等都是主流觀點。然而最受學者們統一認定的只有商事交易效率原則與安全原則,這兩項原則也是最能體現商法強制性規范在私法價值上的合理性與必要性。
(二)商法強制性規范與公法價值
目前學界對于公法價值也沒有統一的學說,有學者認為公法的價值在于以民主方式規范政治秩序,核心為民主;也有學者從憲法角度出發認為公法的基本價值是公平。本文認為,作為按照利益與私法區分開來的公法,其維護國家利益與公共利益基本是從限制權力的角度出發,輔以懲戒性的手段,從表現形式來看,這毫無疑問體現了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與追求。無論是從其追求實體公平與程序公平的實施內容,還是從其以公眾對公平期待值最高的司法作為救濟的最后一道屏障來說,公法都毫無疑問是以公平正義為且唯一為終極目標。
作為商法強制規范中具有公法性質的部分,自然是符合公法本身及公法價值的追求目標。
(三)小結
畢竟在市場經濟飛速發展的現在與全球化貿易的不斷展開,多樣性的經濟現象中所包含的不正當競爭和壟斷等完全有可能使市場出現與維護競爭秩序截然相反的局面,那么商業活動的干預自然是需要國家的強制性干預,這種強制性干預體現在與市場緊密相關的商法中是必然結果;除卻市場的發展需要,商事活動的靈活與敏捷緊緊聯系著當事人的利益,作為經濟活動中的理性人,交易雙方必然都想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交易安全的確定并非易事。除此之外,此外,由于交易活動中強勢地位的營業組織所掌握的信息的優勢地位,使組織及其行為都將影響對方甚至是第三人的利益,長此以往,社會及國家的利益也將被累及,因此,商法中必須要出現強制性措施。
三、商法強制性規范之隱患擔憂
商法的公法化——這種國家強制力介入的強制性規范——并不意味著商法就因此被劃分到公法領域,它只是一個滲透著公法因素的私法領域,體現的是國家對于經濟領域的一定干預。這種干預所出現的商法與行政法、刑法等公法相互交叉的局面無法改變商法的私法屬性,這些公法法條起到的只是輔助作用。然而目前我們最擔憂的就是公權力在商法中肆無忌憚的放大,如何遏制這個問題并加以解決將是商法強制性規范的重點。
僅從商事主體來看,公權力的過度積極干預就包括以下問題:商事主體資格界定爭議。我國主要實行的是將商事主體作為特殊民事主體的定位方案,并通過法律來對商事主體的資格予以規定。然而法律中未曾歸集的攤販、沿途叫賣者等是否屬于商事主體,這一問題至今存在爭議。究竟是否該以公權力界定來解決經濟生活中既存事實的概念呢?筆者認為單純以法律規定來抹凈經濟生活中的既成事實是十分不可取的,法律來源于生活而又推動生活的發展;商事主體資格準入。我國由于立法的多元化,對于商事主體的登記有著許多不同標準。而等級標準的過于嚴格和周期的過長,都是對于商事主體準入市場的一道巨大障礙。
而且毫無疑問,公權力的過度干預則會導致交易成本加大,社會腐敗程度增大,并且在商事活動中顯失公平。
四、結語
社會的呼聲推動了商法公法化現象的出現,商法公法化使商法中的強制性措施顯著增加,這也是公私法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正常現象。
但并非所有的強制性措施都是公法屬性的,這其中固存著許多私法屬性的適應社會需求而生的強制性措施。二者在功能和價值上并不相同,所以準確來說,公法性質的強制性措施才是私法公法化的成果。但是公法化并未剝奪商法作為私法的特性與活力,畢竟作為私法商法更多強調的是參與主體的意思自主,私法規范在商法中使用的更多,地位也更高;公法的滲入可以看成是私法自我調整不順的彌補,這點在公法的修補性彌補性功能中有所體現;而商法對于效益價值的追求也必會一直為商法注入私法活力。
充分利用公法強制性措施的輔助功能,并為其劃定合理范圍,積極引導商法的發展,才能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的良好運行創造一個優秀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