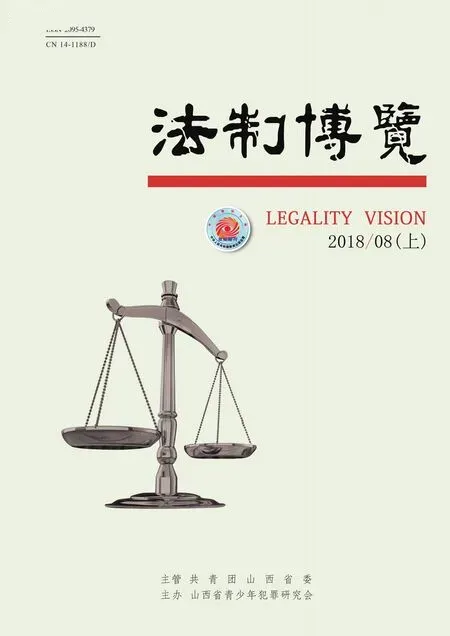民事訴訟中法官觀點釋明義務探究
毛夢霞 董麗麗
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釋明權又被稱作為“闡明權”在民事訴訟的過程中,如果當事人沒有明確的注重或者矛盾、不準確的時候,為救濟的人彌補辯論上的不足和缺陷,促使法庭能夠得到當事人提出的證據,法官啟發當事人通過提問的方式,使當事人能夠全面的對事件進行陳述。
一、我國法官釋明權制度的現狀
我國在《民事訴訟法》上并沒有明確的對其進行規定,但是也有類似的規定去限制。例如其一百二十四條中規定“案件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訴訟”等這些內容如果稍微分析一下就能夠發現其對法官的職權進行限制,而沒有真正對釋明權進行解釋[1]。
我國在司法的解釋上有關于釋明權的規定尤其是在《民事證據規定》上對釋明權進行進一步的規定。其中的第三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向當事人說明舉證的要求以及法律后果”等明確的對人民法院在當事人的舉證上提供可依據的法律后果。但是整體的說,我國還是有很多的不完善的地方在對于釋明權的規定上。
二、我國法官釋明權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立法不完善,對適用的釋明范圍過窄
任何權利都應該在法律所規定的范圍里進行形使,否則即為濫用權利。釋明的范圍的問題即是釋明制度的核心,使用立法對法官的釋明權提供法律依據[2]。我國的法系有比較詳細的對法官的釋明權額范圍,我國在對訴訟法解釋上,只有極少的法官根據釋明權去對范圍進行行使,內容也對法律的方面有涉及。
(二)觀念滯后,法官怠于行使釋明權
滯后的觀念是長期立法的缺陷。在實踐中得以體現,即法官采用消極的態度對待行使釋明權,對起訴、舉證的環節都認為其是當事人的事情,當事人對知識缺少正常的審判,無法得到法官的引導,甚至當事人在舉證和不適當的主張,不了解的法律規定上,法官不能對當事人進行說明與提示[3]。
(三)法官難以把握釋明的尺度
法官在審判實踐中行使釋明權有很大的自由的裁量權,若行使失當,則會當事人的權利有所損害,所以法官在對釋明權行使的時候需要對必要的尺度進行把握。
(四)沒有建立不當釋明的救濟機制
法官在訴訟的過程中不當的對釋明權的行使上,容易出現很多的問題,如果不能對釋明的職責進行履行和解釋等,不可避免的對當事人的權益進行損害。完善救濟的機制的必要的組成部分,也是保障當事人的權利的必要途徑[4]。
三、完善我國民事訴訟中的法官釋明權制度
(一)明確法官釋明權的行使原則
法官在行使釋明權的時候要保持中立、客觀的態度,這樣才能對當事人進行均衡其訴訟能力的差異,保障其中立性;釋明應該公開的進行。在法官的釋明上不能對法律進行違法,不能有暗箱操作,一切需要公開。透明;釋明全的行使要限制在一定的尺度內,這一尺度既不能使法官消極的對釋明權行使,也要防止釋明過度,確保對任何一方的權益不損害[5]。
(二)完善法官釋明權制度的具體構想
對法官的釋明權行使范圍的確定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其過于廣泛的范圍,職權主義會容易被陷入,反之又不能對當事人的缺陷進行彌補[6]。
在不同的訴訟環節,釋明的行使的內容也會各有側重。
四、總結
法官在對法律觀點的指出有一個枝節的問題,但是如果在對民事訴訟的制度上要實現精致的目標,就不能費小心思在這樣的小問題上。與此同時,它在當事人的訴訟中體現出訴訟的理念,也就代表了“司法為民”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