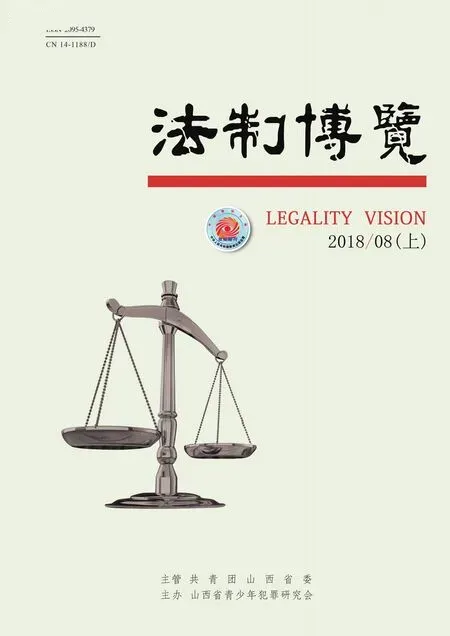社會法學研究應當吸取經濟法學研究的教訓探究
趙雨秋
西南林業大學,云南 昆明 650000
社會法學與經濟法學都是第三領域法律研究的重點內容。在我國,經濟法學研究展開更早,發展至今其研究深度和廣度均明顯優于社會法學。所以,在社會法學的研究過程中,可以充分借鑒經濟法學研究中得到的各種教訓,并將其應用于社會法學研究中,以推動我國社會法學加快建設步伐。
一、調整對象方面
(一)經濟法調整對象研究所得的教訓
在經濟學研究過程中,在調整對象研究方面,得出的最大教訓有以下兩點:
第一,對調整對象的地位過于看重。大多數研究學者提出,經濟法與其他法律最基本的區別就是調整對象,并且經濟法學的研究起點就是調整對象[1]。所以,一些學者耗費了巨大精力用以研究調整對象。然而在社會法學中,雖然調整對象也具有重要意義,但是這意義遠沒達到經濟法學中決定生死的問題,僅僅是其中的一項研究因素。
第二,很多對立觀點成立的基礎都建立在以下假設上的,一種社會關系僅能夠接受一個法律部門的調整。舉個例子來說,如果行政法可以調整縱向經濟關系,但是那么經濟法學就無法對其實施調整;如果橫向經濟關系的調節是通過經濟法學來實現的,那么就不能接受民商法調整。這就意味著,經濟學法與其他法律在調整對象上沒有形成明顯界限。但實際上,任何一種社會關系都不會僅僅受到一方面因素影響,因此基礎不成立也使得對立觀點不成立。
(二)給社會法學的啟示
在社會法研究過程中,必須給予調整對象一個合理的位置,同時用正確的思路展開研究,防止經濟法學調整對象相同問題在社會法學領域再次出現。所以,首先,社會法學的研究要確保建立在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以保障市場正常運行為目標,使社會經濟得到正常發展。其次,在此基礎上,要充分探究民商法、行政法是否能夠在這一前提下展開研究,推動社會法進一步完善和發展,發揮其他法律無可替代的作用,為市場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轉保駕護航。另外,對于市場經濟體制的特殊性,在社會法研究中必須給予正確對待,結合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特殊問題,給予全面深入的探討和分析,從而推動社會法不斷發展。
二、研究順序方面
(一)經濟法學研究順序的教訓
一方面,經濟法在研究過程中,總論與分論的順序是顛倒的。在其他學科領域內,通常的研究順序都是先分論,再總論。事實上,然而在經濟法領域,也應該以先分論,再總論的研究順序展開。然而,我國的經濟法研究,采用了顛倒的研究順序,先研究抽象問題,這樣一來,就會為總論建立制造了很大的困難,導致主體、責任等研究很少,層次性制度研究十分缺乏[2]。
另一方面,總論與分論存在著嚴重的脫節現象。總論研究本應與分論密切聯系,并以分論作為總論強大的理論支撐,再全面結合立法、案例使部門法得到全面完善。然而,我國經濟法研究,總論與分論嚴重脫節,這就導致總論的研究缺失了堅固的基礎,顯得十分空洞。
(二)給社會法學的啟示
經濟法學研究在研究順序方面已經給我們提供了教訓,因此在社會法學的研究過程中,必須堅持先分論,再總論的研究順序,防止出現與經濟法學研究相同的問題。如果直接社會法學研究成果作為總論展開研究,必然會導致其角度過于片面,以此為基礎制定的制度也無法完善。所以,在社會法學研究中,首先應以各個相關社會法部門為入手點,針對這些部門的相關制度、既有案例展開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形成各個社會法部門的總論。然而,以各個社會法部門的總論與分論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再展開社會法學的總論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夠建構起完善的社會法體系。此外,在總論研究過程中,必須密切聯系在社會經濟改革中的各種現實問題,必須密切聯系這些現實問題的相關法律對策。比如,公平價值是社會法學研究中的一個研究對象,在對其展開深入研究時,首先要對內涵展開深入探討,然后對相關依據和要求做深入研究,最后就其與價值目標的聯系找到相關點。這些研究內容作為公平價值的基本內容,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然而除此之外,在相關制度方面存在的問題以及這些問題的成因,也必須要展開深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夠讓公平價值制度不斷完善,不斷發展。
三、小結
總的來說,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社會法學與經濟法學都是重點研究內容,對社會的發展同樣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國的經濟法學的研究起步較早,在研究過程中獲得的經驗教訓,能夠被社會法學研究充分借鑒。對于社會法學研究來說,應積極借鑒寶貴的經驗和教訓,才能加快研究步伐,推動社會法學的完善和發展,為維護社會穩定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