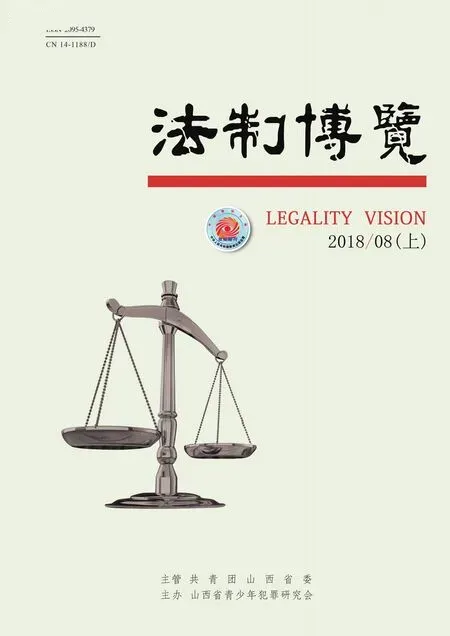侵權行為結果產生的是債還是責任
張媛媛
華南師范大學,廣東 廣州 510000
一、前言
如何更清晰劃分債與責任的界線,完善民法法律體系尤為重要。侵權行為結果產生的是債還是責任,這一論題產生激烈討論,筆者認為侵權行為結果產生的是責任。
二、侵權行為結果是責任的理由
(一)侵權之債的特殊性
就法定之債而言,部分學者會將侵權責任等同于侵權之債,進而認為侵權行為后果產生的是侵權之債。但筆者認為不能只依據侵權之債的命名就認定侵權行為的后果是債。侵權之債雖然含有債的字樣,但其它法定之債更多體現在私法領域,當事人擁有高度自治性,可就債務責任的分擔、債務的履行期限、債務的實現方式進行協商。而侵權責任自身帶有懲罰功能,它不僅是當事人違約衍生出的救濟手段,更是因當事人違法產生的法律后果,所以決定了當事人不得就部分侵權救濟事由進行協商約定。
就無過錯責任而言,其排除了民事協商的可能,以法定形式確定了侵權責任的存在。無過錯責任并不以民事義務為連接點,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存在的余地。其次,由于無過錯責任缺乏違背民事義務的基礎,因此不能夠進行濫用,所以對無過錯責任的責任承擔額度也做出了規定,《侵權責任法》第七十七條規定:“承擔高度危險責任,法律規定賠償限額的,依照其規定。”例如可參照國務院頒布的《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賠償責任限額規定》中第三條規定①,可分析得出,侵權之債相較于其他法定之債,具有懲罰性而非補救性,侵權之債存在法定情形,法定情形之下便無協商可能。
(二)國家強制保障的可能性
國家強制力保障的介入是侵權責任區別于債的重要特征。部分學者認為,當侵權行為發生,當事人會進行有關損害賠償的協商,只有在協商未果或者義務未履行的情況下,當事人才會尋求國家司法救濟。因此認為侵權行為的結果是先產生債,后產生責任。
就前部分——即“債”而言,當侵權行為發生后,當事人之間雖存在協商可能,但此時的協商并不等同于民事領域——例如合同協商的情形,該協商在意思自治的水平上大打折扣。如精神損害賠償而言,《精神賠償解釋》沒有規定精神損害賠償的具體數額,但法官擁有自由裁量權,數額實際有上限。當事人協商存在限制,這宛如一堵隱形的墻,只有在范圍之內才有協商的余地,一旦越界,當事人更情愿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其二,侵權責任法對責任構成、賠償上限等內容做了較多說明。即便是沒有規定法定侵權,當事人為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尋求司法救濟的可能性比因合同違約尋求司法救濟的可能性更高。若侵權行為中有第二階段的出現,即國家強制力來保障雙方當事人的利益。
(三)民事利益因素的介入
當事人之間的侵權行為被認定為責任的原因還在于,債與責任之間的民事利益介入程度不同。
就合同之債而言,當事人之間以前、現在或將來仍會處于合作聯系之中,這種對現階段與未來的合作期許,很大程度上能緩解當事人的違約損失,當事人一般會協商。此外,合同違約對損失采取“填平原則”,即使通過司法救濟途徑,當事人的利益訴求并不會得到更大滿足。其二,不當得利之債與無因管理之債都是因先有利益的存在,出現了當事人利益天平的偏斜,便隨之相應出現了對利益平衡的債權請求權。
但是就侵權責任而言,當事人先前的民事利益介入程度較低。以常見的“乘客在乘坐公交車”為例,乘客與司機之間是一種臨時合同關系,這種關系僅在乘客乘坐公交汽車到達目的地之間維系。所以就大部分侵權行為而言,當事人都是因“臨時”、“短暫”的侵權行為發生而產生關系,當侵權責任風險分擔完成后,當事人之間在以后聯系的密切性很小,加之救濟手段的多樣性,促使雙方為爭取更多權益而尋求司法救濟,因此將侵權行為認定為責任更準確。
三、結語
有關債與責任誰是侵權行為產生結果的問題,關鍵在于把握債與責任的密切關系,筆者更傾向于將侵權行為結果定性為責任,這是從侵權救濟手段的多樣性、侵權之債的特殊性、國家強制力介入的可能性等方面出發,從而得出的想法。
[ 注 釋 ]
①“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以下簡稱承運人)應當在下列規定的賠償責任限額內按照實際損害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民用航空法》另有規定的除外:(一)對每名旅客的賠償責任限額為人民幣40萬元;(二)對每名旅客隨身攜帶物品的賠償責任限額為人民幣3000元;(三)對旅客托運的行李和對運輸的貨物的賠償責任限額,為每公斤人民幣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