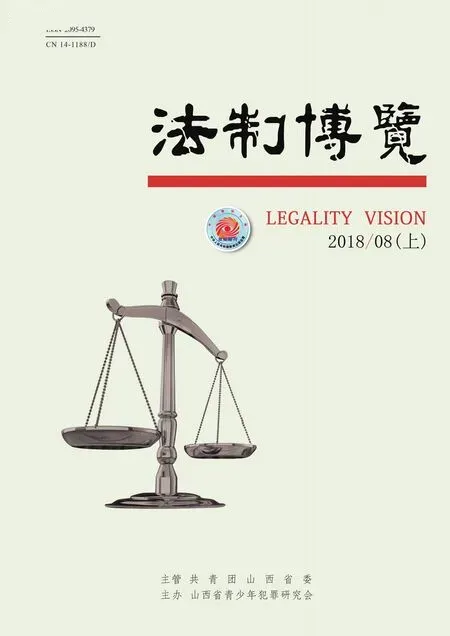淺析重大誤解的歷史淵源以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張 磊
江西財經大學,江西 南昌 330013
“重大誤解”并非民法學即存的概念。“誤解”“錯誤”并非在民法中所即存,嚴格意義上的“誤解”僅指民事主體作為相對人受領表意人意思時所發生的理解錯誤。而“重大”可以認為是對事物判斷的相對性質的判斷程度及比例的范圍。最早出現“重大誤解”法律層面內容的來自于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71條之規定,行為人對行為的性質、標的物的品種、質量等的錯誤認識,使行為后果與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重大損失的,均可以認定為重大誤解。從分析與實證的角度來講,我國民法學概念中的“重大誤解”的范圍是應當從更為廣義的范圍來講的。
“重大誤解”在進行概念理解與延伸時,首先應當對其民法意義上的范圍進行歸類,民法范疇的“重大誤解”是一種法律行為,而《民法總則》第131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是民事主體通過意思表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的行為。該法條與以前的《民法通則》中“公民或法人”的民事主體在范圍上有所延伸,畢竟現實社會中是存在“非法人組織”這一其它類型民事主體的。那么“重大誤解”也離不開“民事主體”、“意思表示”、“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等民事法律行為這一上位民法學概念,當然“重大誤解”也應當是合法行為,與民事法律事實及其他法律行為也是有別的。
我國《民法總則》對“重大誤解”制度的產生是由其社會背景及歷史原因的,雖然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原則,是民事法律行為的出發點,只有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才有可能形成相應的民事法律行為,也是產生相應具有法律效力的行為的前提。由于行為人在意思表示時,對于錯誤的表意由其自身原因造成,應當由其自己來承擔錯誤所帶來的不利后果,但意思自治是以真實意思表達為實現法律效力的前提,不是出于行為人真實意思表示并進而出現具有法律效力的行為,那么強令并非出于真實意思表示的行為人的就其其意思表示行使法律約束力,則不僅有違意思自治的立法本意,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民事主體在民事領域不允許有錯誤”的這一有些荒唐的觀點。我國《民法總則》對重大誤解規定應具備以下構成要件:
一、有意思表示且意思與表示不一致
“重大誤解”應當首先有行為人的意思表示,行為人有作出民事法律行為的意思表示,并且其所意欲表達的意思與其真實的意思想法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矛盾的,只有存在這樣的客觀前提才有可能構成重大誤解,當然這也是重大誤解的先條件之一。
二、表意人須有不符合事實的認知錯誤
表意行為人存在對法律事實的認知錯誤,表意人往往會由于客觀或主觀上的原因對事物及事實判斷錯誤,或認知錯誤,導致對自己的權利與義務作出錯誤的處分行為,從而受到不必要的損失,這也是構成重大誤解的要件。
三、表意人須無使表示與意思不一致之故意
表意人在作出錯誤判斷的意思表示的動機與出發點不應當是故意,及主觀方面沒有任何希望該意思表示成就的愿望,并沒有任何追求錯誤意思表示所導致結果出現的主觀打算,即其通常是處于過失等其他非故意因素而導致錯誤意思表示的出現。
四、錯誤須在交易上被認為重大
錯誤的程度應當是存在一定的幅度范圍,只有在“重大”的程度是在方才可以被認定為“重大誤解”。1)民事行為中公認的重大情形,例如對通常市場價格的認定,行為錯誤的違背該價格行為,如將勞力士手表以普通上海手表價格賣出,并不認識勞斯倫斯“幻影”,卻以普通國產汽車價格出售并辦理相應過戶手續,這都是可以認定為重大程度的。2)雖非針對重要事項但卻足以造成誤解方重要損失的誤解。例如機器設備的零部件出售,可以安裝但是相應配置參數不一致,低配置的零部件足以造成對設備的使用造成安全隱患,這種誤解也是可以被認為是重大的。
在以上的構成要件中,要件一、二是關于“重大誤解”的基本構成要件,對于要件三、四則是“重大誤解”的限制性要件,其目的在于限制可得構成“重大誤解”從而使民事法律行為能夠撤銷的行為,以維護交易安全。
在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經濟高速發展,國家法律要保護交易的安全性,但允許“重大誤解”,“欺詐”,“脅迫”,“乘人之危”,“顯失公平”等法律制度的存在,是提高經濟效率,保護交易及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法律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