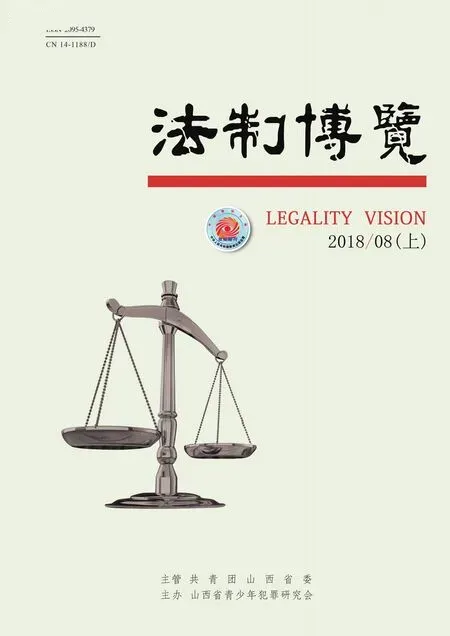民法總則修改未成年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最低年齡界限合理性探討
徐 璐
延邊大學法學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一、修改的背景及必要性
(一)現實社會生活的快速發展
中國改革開放已有四十年,經濟和社會的飛速發展,民眾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也有目共睹,隨之而來的還有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現在的少年兒童接觸的各種社會事物的范圍也比改革初期接觸到的大得多。種種原因使得未成年人的智力及意思表達能力大大提高。起草《民法通則》的時候,正處與改革開放之初,未成年人很少接受外來因素的影響;入學年齡普遍偏高,受教育的方式與渠道單一。基于整體的考量,把十周歲這個年紀當做未成年人無民事行為能力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之間的界限是合理的。四十年的改革讓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互聯網已經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樣一個時代出生并長大的兒童接受著現代化的教育、紛繁復雜的事物,使他們擁有的社會經驗也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的意思能力的表達也受到了非常大影響。立法者不能忽視這種變化,原來的年齡界限也已不能適應變化后的社會現狀。
(二)對相對人權益保護的需要
我國一直強調要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要求交易穩定與安全。筆者認為仍舊堅持十周歲的年齡標準,不利于維護現代社會交易雙方的正當權利。如果按照原來的標準舉例來說,一個不滿十周歲的小學生用父母給的零用錢,購買學習用品和零食的這種交易行為應該是無效的,他的父母如果并不認可這種購買行為的話,他的行為還將自始無效。這樣的規定對于交易的另一方來說是不公平且不穩定的。特別是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許多未成年人有著與實際年齡并不相符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成熟,僅僅從外表上,商家做出善意的判斷后與其進行交易,卻被其監護人以其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對交易行為進行否定,這種情況多有存在和發生的話將極大地損害交易的穩定,是對契約精神的破壞。網絡購物中這種現象更為嚴重,交易相對人很難對沒有直接見面交易的對方的年齡進行判斷,更無法判斷網絡另一端的人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二、修改的合理性探討
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并非一個僵硬的制度,因為不論年齡下限這個界限設定在一個什么樣的年齡,都不會限制剝奪未成年人的自由,也不會對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產生消極后果。因為,當未成年人的年齡未達到界限的時候,可以主張未成年人實行的行為和該未成年人的年齡、智力相適應;當未成年人的年齡超過界限的時候,可以主張未成年人實行的行為需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同意、追認。有意思能力和沒有意思能力的未成年人都被法律庇護。但是,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卻不論什么情況都無法獨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因為,如果法律允許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獨立實施一定的行為,就會變成不嚴格的無民事行為能力制度,甚至可以說變成了自由較小的限制民事行為能力制度。從這個方面來說,“十周歲”下調至“八周歲”,使得曾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的8至10周歲未成年人的行為自由更大,同時他們的合法權益仍被法律保護①。
其實《民法總則(草案)》的四次審議稿一直都是堅持將未成年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最低年齡界限定為六周歲,但是因為爭議很大,反對的聲音很多,甚至有人希望保持原來十周歲不變,直到最后的草案的審議報告公布,吸納了代表們和其他各方的意見,將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下限從六周歲調整至八周歲。我認為,這也一定程度上其實是各方意見的互相妥協,是立法部門統籌兼顧的一種折中的做法。
法律必然要依國情變化而變動,所以就目前我國情況而言,八周歲的界限是合理的。從生物學角度而言,兒童在七歲時大腦重量就已經接近成人,八至十周歲未成年人在大腦發育方面成年人基本相同。其次,從社會學角度而言,物質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互聯網的蓬勃發展、新型消費方式的興起的環境里,未成年人參與民事活動能力和心理成熟程度顯著提升。最后,據我國《義務教育法》規定,六周歲是法定入學年齡,條件不具備地區可以推遲到七周歲。可見,大部分八周歲的兒童已經上了小學二年級,具備了一定知識,認識和控制能力提高,明顯優于剛入學的6周歲兒童。6周歲的兒童認知和辨識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不夠高,很容易收到成年人和環境的影響。所以,在未成年限制民事行為能力最低年齡界限的下調成為必要的條件下,將這個年齡界限調整至8周歲比調整至6周歲更加的合理。
[ 注 釋 ]
①朱廣新.民事行為能力制度的體系性解讀.中外法學,Vil29,No3(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