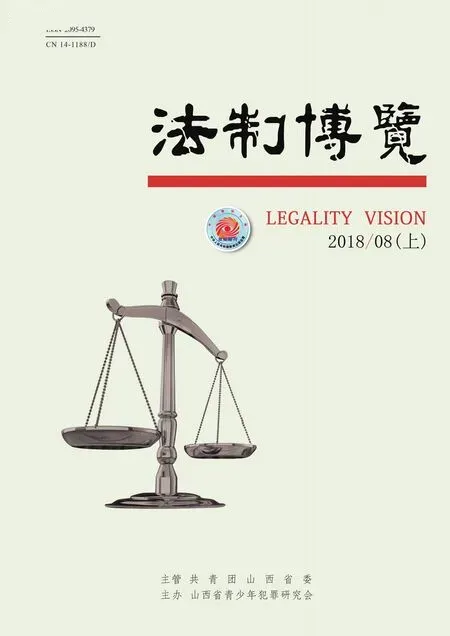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下民事法律關系中關于“重大誤解”的定義問題淺析
王詩琪
沈陽師范大學法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4
一、重大誤解的法定含義在網絡民事關系中立法基礎
我國《民法通則》和《合同法》以及最新的《民法總則》均未對何為重大誤解做出詳細規定。相比之下,《民通意見》第71條規定則具體很多,但是仍然未對“重大誤解”予以明確定義。《民通意見》只是單純列舉了“重大誤解”的情況范圍。具體是否構成重大誤解還要在司法實踐中具體案件具體分析。這是基于《民通意見》對于重大誤解這種定性,為互聯網時代下的網絡民事法律關系里的重大誤解提供了立法基礎和理論基礎。同時也為因重大誤解導致意思表示不真實的當事人提供了救濟機會。
二、網絡購物中的“重大誤解”
在我國大量的網絡民事關系主要是以網絡購物方式呈現的,隨著互聯網經濟的日漸壯大,網絡購物的標的物也逐漸從衣服家電向汽車房產轉變。因互聯網購物具有程序化以及虛擬化特點固在網購中的買賣雙方的意思表示皆由網絡為媒介進項傳遞,那么這種方式能否真實表達買賣雙方的意思表示就成了如何認定重大誤解的重點。首先互聯網的程序性,互聯網程序性是一種網絡交易的自動化,將我們傳統的交易形式以程序的方式表達出來與日常生活的交易并無差別。只是新技術條件下的新形式并不阻礙買賣雙方意思表示的真實性。其次網絡購物的虛擬性,很多時候買方在貨物到貨達成交易前,對于購買物的部分性狀如質地,材質等并無直觀的感受只是通過網絡以圖片或者文字等方式展示。而這一特點則極易產生“重大誤解”而根據《民通意見》的相關規定無論買方是否存在主觀上的過失均以“重大誤解”為由變更或撤銷買賣合同這樣顯然對賣方利益是極大的侵犯。在筆者看來當網絡購物中買方以“重大誤解”為由請求法院撤銷合同時,法院應對存在重大誤解事項予以審查只有在雙方基于買方主觀存在過失心態且賣方對于標的物的網絡表述可能使不特定的其他人產生歧義,并且賣方知曉或者應該知曉這種歧義的情況下才能認定為重大誤解。如果賣方對于標的物的網絡表述沒有任何理由知道或應當知道會產生誤解時那么不應當認為是重大誤解。
三、互聯網金融服務中“重大誤解”
互聯網金融有別于傳統線下的客戶經理對客戶的金融服務模式。互聯網金融依據這些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實現支付、理財、資金融通等。通過互聯網為載體規避了原有金融服務的諸多服務成本如紙質合同服務人工以及資金的轉移憑證等。在節省金融服務的成本同時帶來風險也暴露無遺。第一,互聯網金融服務中大量出現的格式條款完全是由經營方獨立制定的。在沒有專業人士指導下部分當事人難免會對格式條款的一些內容產生誤解、忽視導致意思表示不真實。第二,在傳統人對人金融服務中業務員在往往能有效的對金融服務的內容予以說明并提示客戶可能存在的風險。從而有效規避一些不必要的意思表示障礙。基于以上原因。在互聯網金融服務中對于合同中如出現的易產生誤解的條款未做解釋的或合同有隱藏不利于客戶重要條款嫌疑的當事人主張重大誤解要求撤銷或者變更合同的法院應予以變更或撤銷。
四、涉及虛擬財產的民事法律關系中的的“重大誤解
虛擬財產一詞由來已久,但一直以來民法框架并未給與嚴格定位。直到今年《民總》正式實施其虛擬財產的地位才給與立法肯定。但《民總》并未對虛擬財產的所有權類型予以明確劃分。使其以一種游離在知識產權和物權中間的狀態。筆者認為盡管虛擬財產在現實的民事法律關系中具有諸多不穩定。但是并不影響在民事法律中對于虛擬財產存在“重大誤解”的定性。根據《民通意見》的規定既然虛擬財產已被《民法總則》我國民法所保護的個人財產其地位就和傳統財產具有同等地位。對其種、質量、規格和數量等錯誤的認識應列為重大誤解。
隨著互聯網日漸占據日常民事關系的比重逐年升高,對于互聯網時代下民事法律關系的諸多立法規則都有很多不相適應的地方。本文意在通過類型化的民事法律關系在原有立法基礎上對重大誤解予以新的解讀。并希望在以后對相關司法解釋出臺提供相應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