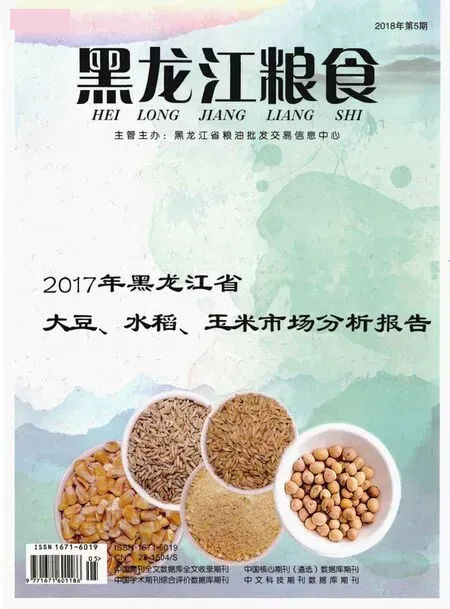常懷憂患意識糧食安全之“弦”不可松
□ 丁 聲 俊
(接上期)
4、現代服務薄弱,農民困擾重重。隨著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進程,經濟社會結構發生了、發生著巨大變化,對現代化服務業的需求出現“六大新趨勢”: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三農”對其需要更加迫切、更加強烈;生活性服務與生產性服務的需求量均明顯增長,日益趨向專業化、社會化、綜合化;在發展傳統服務業的同時,更需要建立信息化、電子化、新業態等現代化服務業網絡;虛擬化、無形化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對誠信體系建設及要求日益迫切和日益嚴格;城鄉服務將日益融合化、一體化;對專業的、高技能服務業人才的需要量越來越多、越來越高。
然而,我國農村的現代化服務業還是一個“大短板”。主要表現是:服務總量不足和服務質量不優并存;服務的旺盛需求與服務的供不應求同在;尤其是農業糧食產業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及農產品市場的快速擴展,所需要的信息化、電子化等現代化服務手段與專業人才跟不上需求。迄今,我國農業政策一輪又一輪,資本一波又一波,提供了多種服務工具。然而,廣大農民仍然受現代化服務的制約和困擾,其主要表現包括:服務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強烈突出;服務供給成本高企與品質欠佳、渠道不暢與品種單一明顯;信息服務不靈和科技服務不力普遍。造成這些困擾的根本原因是農村智力服務欠缺。由于智力服務薄弱,農民不懂得現代化服務知識和技能。例如,現代市場意識普遍淡薄,經營能力亟待提高。更突出的問題是信息不靈,由于信息網覆蓋面有限,加之大量農民不會使用現代信息工具,導致農民不知生產什么、生產多少,或什么時候生產、為誰生產。其結果是屢屢發生“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現象。這充分說明,農業農村要持續穩定發展,除了市場化、規模化之外,在農村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加強現代化服務的內容。
5、農民主體地位失落,變成被雇傭勞動者。社會理想主義者呼吁:要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這“三讓”是令人憧憬的目標。實現這一美好夢想的根本,還必須有另外的“三讓”做保障。即:讓農民在農業農村中真正占據主體地位;讓廣大農民真正成為農業農村社會經濟的主人;讓廣大農民具有傾訴話語的權利和機會。總之一句話,要讓農民真正當家作主。然而可惜的是,農民對有關自身權益的農業農村發展和改革的措施、表達話語權的平臺和機會甚微。例如,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涉及廣大農民的根本權益,農民理應擁有充分的話語權,但相反,農民的話語常常得不到尊重,甚至受到漠視,危害農民土地權益的事件普遍發生,對農民造成的損失也最嚴重。不少地方違背土地流轉的原則和策略,忽視農民意愿,漠視農民的主體地位,導致土地流轉亂象叢生。
土地流轉“亂象”的主要表現有六方面:一是土地流轉主體混亂。各地土地流轉中,村民小組、村民委員會,甚至鄉鎮政府、縣區政府取代農戶決定土地流轉的問題多有發生,由“開放熱”造成大量耕地被占用。二是土地流轉行為混亂。農戶隨意流轉與基層政府強制流轉并存,口頭流轉與書面流轉共生,有償、低償、無償流轉同在。“以地生財”誤導濫用耕地,一些地方寧肯以“犧牲耕地”為代價也要換取所謂的“政績”。三是流轉土地用途混亂。有些地方土地流轉后“非農非糧化”傾向明顯,用來建墳園、建房、建窯,甚至非法變相建賓館、搞房地產經營等。四是土地“資本化”混亂。大量城市工商資本下鄉,給農村注入了“資金”,但實質上是以不同形式“買斷”土地經營權,原承包農戶只能獲得“流轉費”,土地流轉后的新成果絲毫享受不到,一切收入全部歸“資本”所占有。五是土地流轉市場混亂。許多地方的土地流轉還處于自發、無序、混亂狀態,農民權益蒙受損害。加之,沒有具體的法律條款進行規范,農民的合約意識薄弱,所以轉出方、轉入方之間經常會出現毀約或棄約現象。六是職能部門監管混亂。迄今相關職能部門對土地流轉的監管頗多混亂,越位、錯位、不作為問題多有發生。例如,“越俎代庖式”土地流轉就是主體錯位、權力越位的表現,對于土地流轉后“非農化”“非糧化”問題更是視而不見、熟視無睹。此外,由于糧食比較效益低,還造成耕地撂荒,作為國土資源中精華的耕地大量被占用和浪費了。
導致土地流轉產生亂象的原因有多種,包括法律法規的、思想認識的、經濟利益的等等,可概括為:對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法律效力認識執行不到位,導致違法流轉;不同村鎮之間土地流轉的補償標準不統一,導致產生矛盾;農村基層組織協調處理糾紛的能力不足,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糾紛解決機制;法律法規宣傳不到位,以及信息不對稱、地源虛假、法律意識淡薄等。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非法的土地流轉導致農民喪失“主體地位”,流轉后的土地種與不種、種什么與種多少、取得的收益怎樣分配等事務,就與出租土地的農民沒有絲毫關系了。新型經營主體和農民之間的關系就完全變成了土地租賃和被租賃、雇傭和被雇傭的從屬關系和附屬地位,必然抑制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充分發揮,這是最為令人憂慮的。
三、采取戰略措施,確保“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的名詞,最早產生于上世紀70年代中葉。當時,糧食形勢風雨驟變,爆發了二次大戰后30余年里最嚴重的糧食危機。市場供求失衡,安全儲備系數由18%下降到14%,世界谷物價格暴漲2倍以上,廣大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許多國家和地區爆發糧荒和饑饉,世界陷入嚴重糧食危機。
(一)“糧食安全”的提出及內涵的豐富發展
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早敲響“糧食安全”警鐘。面對世界糧食形勢的風云突變,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早敲響“糧食安全”的警鐘,并在1974年舉行了“世界糧食會議”,提出了保障“糧食安全”的警告,要求各國谷物庫存量要達到各國糧食安全的最低水平,即相當于當年谷物消費量的17%~18%。世界糧食大會形成的文件,成為動員各國為保證世界糧食安全的行動綱領。此后,糧食安全的內涵不斷延伸和充實,主要包括:從糧食安全的外延上看,從國家層面延伸到家庭層面,乃至個人;從內涵上看,從數量安全充實到質量安全、再到營養安全,乃至可持續安全。“糧食安全”內涵的延伸和豐富,就等于向世界又一次次發出警示,讓世界保持警醒。
自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早敲響“糧食安全”的警鐘以來,國內外相關機構和專家學者對糧食安全的概念進行了界定。迄今,國內外關于“糧食安全”的定義不下數十種之多。這里,列舉幾種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定義:(1)1974年世界糧食大會通過的“糧食安全”的定義是“一個國家的糧食儲備要相當于當年糧食消費量的17%~18%,這被視為糧食安全線。”這里所說的糧食,指的是谷物。(2)1983年愛 ·薩烏馬的定義。1983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總干事愛德華· 薩烏馬提出的新概念是“糧食安全的最終目標是,確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時候既能買得到、又能買得起所需要的基本糧食。”(3)1992年國際營養大會的新概念是“在任何時候人人都可以獲得安全營養的糧食來維持健康動能的生活。”(4)2001年世界糧食安全委員會的定義“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得足夠的、富有營養和安全的糧食。”(以上見:丁聲俊《科技革命、制度創新與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研究》,(內部研究報告),2005年1月)。
糧食安全的本質性特點。前述國內外普遍接受的“糧食安全”的定義,內涵逐步豐富,外延相應擴展,構成了逐步更加完整的概念,具有本質性特點:一是整體性。這是“糧食安全”諸特性中最根本的特性。它是指系統結構的有序性和關聯性,為保障糧食安全需要進行“整體設計”,提高糧食“供給側”結構質量,與不斷升級的“需求側”結構地動態性協調。二是人權性。即:糧食安全不僅是關系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整體的“糧食安全”,而且指不管是富國、還是窮國的每個家庭、每個居民、在任何情況下都有享受足以保障身體生理需要的糧食的權利,即生存權。三是戰略性。即不僅單單是糧食供求平衡的問題,而且是緊緊關系經濟安全、乃至國家安全戰略的大事。不管環境和形勢怎樣變化,都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戰略主動。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四是動態性。即“糧食安全”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國民經濟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農業糧食生產、供給、流通和消費等條件的變遷而變化,保障“糧食安全”的內容、方式等都必須和必然相應轉變。五是可持續性。即不僅保障當代人的糧食安全,而且還要保障后代人健康生活的能力,而且一代又一代傳承、持續下去。這就要求徹底摒棄拼投入、拼資源的“兩拼”的增長方式,采取環境友好型的生態農業的發展道路。
(二)嚴治土地“亂象”,保護和利用好“天下糧田”
古典經濟學的一個觀點認為,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現在有人否定這一觀點是徒勞的,因為它揭示出土地是基礎資源的客觀性和稀缺性。本文所說的“天下糧田”,是廣義的大概念,包括國家的陸地、河流、湖泊、內海、領海等,是主權國管轄的國家全部疆域。在人多地少的我國,在大力保護與利用好土地中的精華耕地的同時,還要逐步治理、保護與利用好其他國土資源,像廣闊的山地、草地、丘陵地、湖海、江河、濕地,乃至沙地等,提高其質量稟賦,都會成為更有價值的資源,產生巨大的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當然,也開辟和加強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新資源基礎。
耕地是農業糧食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其存在是非人力所能創造的,是固有的不可移動性、地域性、整體性和有限性的“天下糧田”。耕地還是一種稀缺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不僅有經濟社會功能及其相應的價值,更具有生活和生態功能。尤其是對于我國農業糧食生產,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和發展的生命線。基于這一邏輯,保護“天下糧田”就是保護農業糧食的生命線。從發展趨勢看,人類對它的依賴和永續利用程度的增加是不可逆轉的,而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由這些特點決定在人多地少的我國,保護耕地更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它是基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需要,也是基于社會穩定和諧的需要,還是保護耕地自身稀缺資源的需要。適應這種需要,必須像愛護和保護大熊貓一樣,愛護和保護“天下糧田”。(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