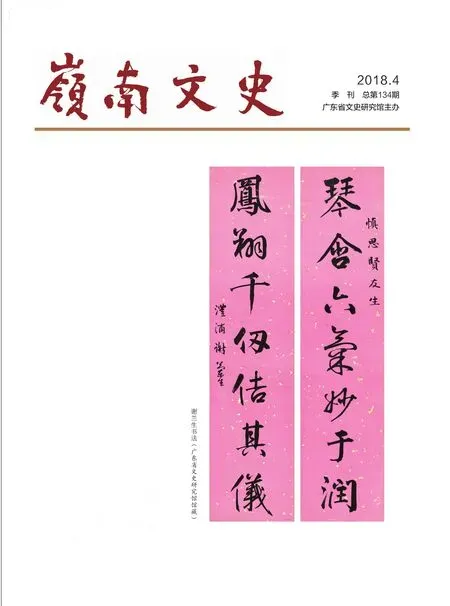嶺南民間信仰多元融合形態表現形式
——以惠東神明信仰為例[1]
倪新兵 陳政禹
歷史上嶺南是民間信仰最為豐富的地區之一。《漢書·郊禮志》中云:“是時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2]可見,從漢代起,嶺南人就有信鬼敬神的傳統。至明代,這種習俗更是逐漸發展為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粵俗尚鬼神,好淫祀,病不服藥,惟巫是信”。[3]嶺南人信鬼敬神的傳統,為民間信仰形態的探討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源。
惠東作為嶺南地區的一部分,其境內不僅有哺育客家文化的山地丘陵,還有著顯示潮汕文化背景的海岸地帶。所以,惠東地區的神明信仰既包含有客家文化要素,又與潮汕文化存在著相當密切的聯系,還兼有海洋文化特色。同時,歷史上由于遠離中央王朝,惠東地區存在很多粵俗巫鬼信仰的遺存。這些特定地緣因素和多元文化傳統使惠東的民間信仰別具特色。進入21世紀,在區域民間信仰研究成為研究熱點的趨勢下,惠東地區的神明信仰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為推動當今嶺南地方文化建設和為促進嶺南民俗旅游資源開發提供參考。
一、惠東民間神明概況
惠東民間神明信仰是惠東民眾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的習俗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是惠東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寫照。在惠東地區,各類廟宇幾乎遍布街頭巷尾、路旁樹下、鄉間小屋(有的是成年人不能直腰進入),甚至連一些怪石、巨樹也成為崇拜對象。有時一領幔帳,甚至一個香爐,便可成為一處供奉神祇的場所。[4]可見民間神明信仰的興盛。
就時間維度而言,惠東民間神明信仰體現出文化延續性。惠東很多寺廟宮觀具有久遠的歷史,以道教寺廟為例,梁化鎮梁化屯的城隍廟建于梁武帝肖衍天監二年(503),自建廟后便香火鼎盛。[5]而九龍峰譚公祖廟建于明宣德九年(1434)末,清道光三年(1823)重修。至今保存完好。[6]以佛教寺廟為例,自唐初佛教傳人惠東境內,相繼建有西來古剎、拈花寺、南山龍巖寺、寶華寺、中山寺、天成庵、玄妙庵、普照庵、榜山寺、龍船庵、云山寺、東蓮禪寺等寺院。其中西來古剎位于新庵鎮西北方的梅嶺山脈,宋仁宗在位年間(1023—1063)所建。拈花寺位于惠東縣城北郊的觀音山,建于明崇禎十三年(1640)。這些寺廟目前都保存完好,信眾云集。
從民間信奉的神明種類看,惠東的神明信仰主要分為六類:一是佛教神明,如彌勒佛、觀音等;二是道教神,如譚公、玄天大帝等;三是女性神明,如媽祖、王母、馮仙姑等;四是祖宗神,如畬族的祖公信仰等;五是土地神,包括有些伯公信仰;六是自然神,如山神、石神等。
二、山海融合下的惠東民間神明信仰
惠東民間神明信仰在其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出現山區之神和海洋之神互通融合的狀況。這種現象在譚公信仰和媽祖信仰中表現最明顯。
譚公最早作為惠東山區地帶客家人所敬奉的地方神而存在。關于譚公的來歷,據清光緒間修《惠州府志·仙釋》載:“譚公道者,歸善(惠東)人也。居九龍山修行,不記歲月。每杖履出山,一虎隨之,或為負菜,往返與俱,人其訝之。既歿,有祈雨祈者輒應。山故又庵,甚靈異。”[7]可知譚公為惠東九龍峰人,在九龍峰上修道成仙。后來眾人以為得其庇佑,在九龍峰上建廟供奉他。可見,譚公最初是被惠東人作為求雨護境的山區之神而存在。隨著惠東地區海洋生產活動的頻繁,譚公從最初意義上的山神、鄉土地域神,逐漸衍化成為一個海神。在惠東地區的譚公醮會中,惠東民眾會抬著寫有“一帆風順”的海船模型以及象征漁業豐收的各種魚蝦模型進行巡游,其巡游的路線除譚公廟周圍的各個村莊外,更是會沿著海岸線到達巽寮灣一帶。在惠東出海的船只上,也貼有譚公廟請來的靈符。[8]這充分說明譚公的海神屬性。今天的譚公信仰更是隨著惠州客家移民遠播海外。[9]惠東九龍山的廟宇被看作是譚公祖廟,香港、泰國等東南亞各地以及美國有些地方都有從九龍峰引出香火而建立的譚公廟。譚公誕也成為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地區信眾長期保留的傳統祭祀、朝拜習俗。
在稔山范和石門山上的雷鳴庵以及鐵涌鎮的駱村,建有馮仙姑廟,奉祀的是惠東本土神靈馮仙姑。傳說馮仙姑是一位為爭取婚姻自主、沖破封建樊籬的一位堅貞不渝的烈女。[10]馮仙姑最早也是地區性的護境山神,后來隨著客家人的遷徙傳播海外,與呂仙姐、北極仙姐、地母娘娘、華岳三娘、七仙女、桃花仙姑、龍母和龍女等神靈一樣,成為馬來西亞華人的信仰。[11]在港澳漁民中被廣為奉祀的海神朱大仙也源自惠東的山區地帶。20世紀20年代,一位吳姓漁民承諾建廟供奉朱大仙,在香港大澳興建了龍巖寺。[12]如今,朱大仙已成為港澳漁民的保護神。供奉朱大仙為主神的信仰群體被人們稱之為“契爺”。每年農歷三月至六月期間,信眾們會進行水、陸“打醮”儀式。[13]作為護境神的“城隍”在惠東平海一帶也作為海神存在,當地有規模盛大的城隍廟醮會。醮會按照連續舉辦三年、停三年、再連續舉辦三年的傳統進行。這里的醮會稱為福醮,一般都是在每年的農歷九月開始。[14]如今城隍廟醮會已成為惠東海濱漁民盛大的祈福活動。惠東內陸地區的農神也越洋成為保護海外華人的海神。旅泰華僑陳百貞將家鄉的農神越洋帶到泰國一帶敬奉,在泰國“山仔”海濱建造神農廟。后來神農廟年久失修,人們又在百本公學舊址新建神農宮,把“山仔”農神位恭迎過來,成為泰國第一座“神農宮”。[15]
惠東地區的海神也有向山區護境神轉化的現象,這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媽祖信仰。媽祖信仰在惠東地區非常興盛,僅范和村就現有媽前烈圣宮、溪壩鳳凰池媽宮、市場邊媽宮(又稱眾神媽廟)、大路街媽廟四大媽祖廟,其中以鳳凰池媽宮歷史最為久遠。此廟最初建于范和新厝,周圍都是海灘。相傳有一年山洪洶涌,沖毀了廟宇,媽祖神像漂進了大海,一直飄到巽寮灣的鳳凰池,卡在岸邊的石縫里。當地人發現后欲取出神像未能成功,便在原地燒香叩拜媽祖并建起廟宇,不少人慕名前來參拜。后來范和村人也前來祈福,發現大殿內供奉的竟是范和村當年被洪水沖走的媽祖神像,于是要求把媽祖神像請回范和村。幾經爭執,最終雙方達成協議,各自供奉半年,每年農歷五月初二日把媽祖神像從惠東巽寮灣接回范和村過端午節,又在每年農歷的十月十五日把媽祖神像送到巽寮,讓媽祖回巽寮過冬至和春節。兩地供奉一尊媽祖神像,和睦如一家。這一傳統已經延續近300年。[16]如今惠東的媽祖信仰從特定的海洋群體擴展到大眾人群,祈望媽祖從保護海上平安和漁業豐收向保護家宅安寧和人丁興旺轉變,成為所供奉區域的鄉土地域神。在惠東的黃埠鎮,當地人施工和護宅都會請媽祖神符。[17]
三、地域融合下的惠東民間神明信仰
惠東是一個族群多元且混雜的地理單元,潮汕族群和客家族群共居于此,在一些地區還居住著作為百越族土著民之一的畬族,他們的民間信仰保留了一些百越巫鬼信仰的成分。
惠東的福佬民系多聚集在沿海一帶。他們的信仰帶有潮汕特色,普遍信仰的神祇有玄天上帝、三義帝君(即劉、關、張)、關公、雙忠公(即張巡、許遠)、三山國王、天后圣母、慈悲娘娘、七圣夫人、風雨使者、注生娘娘、福德老爺(即土地)、花公花嬤(司多子多女)、公婆母(司兒童生活)、天公、孔子爺、韓文公(即韓愈)、城隍爺、太子爺、安濟圣王、文章爺、魁星爺、趙公元帥、田元帥、神師爺(即魯班)等。[18]供奉這些神明的廟宇多在惠東福佬人聚集的地區,如惠東鹽洲島有天后宮、玉虛宮、三圣宮、三王宮、協天宮等,這些廟宇多供奉天后、北帝和赤帝等神明。[19]客家民系拓荒種植的農耕經濟生活和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使客家人信仰的神明多為鄉土護境神,如譚公、關帝、北帝、道教三尊、李大將軍、水仙公、觀音、林爺仙、醫帝、福德、呂洞賓、城隍等。[20]可見,在惠東地區,潮汕福佬民系的信仰帶有更多的海洋特色,其信仰的神明也更為龐雜。
惠東畬人信仰保留了百越巫鬼信仰的一些元素,有崇狗的習俗。相傳,上古高辛王登基后,皇后患耳病,醫官在她的耳中取出一條黃蟲,用金籃扣之,黃蟲卻變成了一條五色斑文的“龍犬”,號曰“盤瓠"。時遇番兵犯界,盤瓠揭榜,過海取得番王首級旋歸。后“龍犬”變體,成“人身狗頭”,高王加封盤瓠并授官到廣東為王。自后,畬人便崇盤王為自己的始祖。[21]每逢春節、端陽、中秋等節日,畬人都要在祠堂正中懸掛祖公(人身狗頭)的畫像,同宗的男女老幼聚會一堂,由長者帶領,先將三牲擺在門外,把香燭插在豬頭上,主持者口中念念有詞,請在外打獵的盤王歸來,此為“喊祭”,然后把三牲挪入堂內向祖公朝拜。[22]如今惠東畬人的信仰也與客家人的信仰相融合,普遍信奉土地公、灶神、田頭伯公、文昌爺、譚公等神明,其中以譚公爺信仰最為典型。[23]
惠東沿海范和村的神明信仰是地域融合的一個典型例證。范和村村民的主要成分是客家人和福佬人。在這里 “無地無時無神仙”,無論是山頂、海濱,還是街市、巷頭,隨處皆有神靈落腳。人們共同祭祀的神明有馮仙姑、譚公、桃花姑娘、玄帝、文昌帝君以及陳鴻猷、沈敬德、楊沛霖三孝廉,在村口的城隍廟門口還供奉“勸善大師”。[24]客家和福佬的神明信仰在這里十分融合。在鹽洲島,福佬與客家神明并祀祭拜的現象更為明顯。如在白沙村在總神廟協天宮,關帝、媽祖、譚爺、三界爺、李將軍、福德等神共祀一處。[25]這些來自不同地域的神祇,一同接受福佬和客家信眾的敬拜。
在神明信仰的地域融合中,一些神祇逐漸成為各個族群的共有之神,如三山國王信仰。這一民間信仰源自潮汕地區,從元代起,其信仰便擴展至惠州地區,“潮之三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遠近人士,歲時走集,莫敢遑寧。”[26]三山國王成神于隋代,其原型是三位名為連杰、趙軒及喬俊的異姓結拜兄弟在農歷二月二十五日這天同時受命于天而顯化為神。在宋太祖征太原時,因其助戰有功而加封三山國王。[27]三山國王信仰傳入惠東后迅速發展,成為惠東各地普遍敬奉的神靈。客家人將其與譚公合祀,如在九龍峰譚公祖廟,其左廂房就供奉三山國王。[28]其廟宇也遍布惠東各地,除筆者調查的惠東稔山鎮和黃埠鎮有三山國王廟外,鐵涌鎮的三多村王爺坳、趨洲鎮巽寮鄉、坪山鎮等也多有分布。[29]
四、佛道融合下的惠東民間神明信仰
中國宗教發展的一個特點是佛、道在同一個生存空間和文化的調攝下,漸趨一致。[30]這種狀況在惠東民間的神明信仰中特別明顯。道教傳入惠東約在南北朝時,梁武帝肖衍天監二年(503),在梁化立郡筑城(今梁化屯)立城隍廟。而佛教則于唐代初期傳人惠東境內,傳人后在境內相繼建有西來古剎、拈花寺、南山龍巖寺、寶華寺、中山寺、天成庵、玄妙庵、普照庵、榜山寺、龍船庵、云山寺、東蓮禪寺等。[31]
佛教和道教傳入惠東地區后,與惠東民間神明信仰產生“互化”效應,一方面惠東本地的巫鬼文化為佛教的水陸道場和道教的齋蘸法事提供了效法雛形;另一方面惠東民間神明信仰也與佛教中的因果輪回思想相融會,同時突出了道教中的鬼神迷信成分。在這種情況下,惠東民間神明被大量收編進入佛道神明譜系。
在惠東民間神明信仰中,民間神明和道教、佛教是相互交織的。這首先體現在佛道神明共祀于同一座廟宇之下。如在惠東平山觀音山的拈花寺,寺內佛道共廟。[32]惠東鹽洲島的民間信仰,在其前寮村的麥姓教師的祖屋正廳,供奉著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護國庇民天后圣母、北極真武玄天上帝、敕封襄濟譚公仙圣、都天致富財帛星君、威昊顯赫水仙大王、翰苑蜚聲田大元帥、本家正直福德爺爺、東廚賜福司命灶君這九尊神。[33]可謂是“上穹碧府下黃泉”,佛教道教、神仙鬼怪無所不包。在惠東稔山一帶,居民家宅和出行的船上都貼有從廟中請來的各類神符,這其中既有佛教神明也有道教神明。如在一艘船上貼的神符有“彌佛靈符、玉皇上帝靈符、譚公靈符和王母娘娘靈符”,在另一艘船上貼的是“南海觀音、天后、華光大帝、玄天上帝和馮仙姑”。[34]可見,佛道二教都在惠東的民間神明信仰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這種佛道融合特點也明顯地體現在各種醮會儀式方面。如在惠東新庵舉行的西來古剎法會上,其程序是:第一天:開光請神科儀。從西來古剎請出佛祖(神像),開光。第二天:分燈科儀。啟請佛祖降臨醮壇,聽取主醮法師面陳奏疏。第三天:宿啟道場。向神壇五獻,行朝天科儀,誦朝天寶懺1至10卷。第四天:行三官科儀。禮拜天、地、水三官,誦三官寶懺。第五天:行禮斗科儀。誦太上南北斗延生延壽真經,揚幡、午供、五獻。第六天:誦朝天謝罪玉皇寶懺,誦九幽拔罪懺1至10卷。第七天:行靈寶祝香科儀。禮三佛。行普渡科儀。放燈,放生。第八天,散醮,將佛祖護送回西來古剎,大擺宴席開葷。[35]西來古剎佛教法會的儀式和流程與九龍峰譚公祖廟的道教醮會有很多相似之處。九龍峰譚公祖廟的醮會儀式流程為:第一天是開光請神科儀,第二天是分燈科儀,第三天是宿啟道場,第四天行三官科儀,第五天行禮斗科儀,第六天誦朝天謝罪玉皇寶懺、誦九幽拔最懺1至10卷,第七天行靈寶祝香科儀、行普渡科儀、行普施科儀(施孤),第八天散醮(將譚公神像請回祖廟,醮官職事大擺宴席開葷)。[36]可見,西來古剎法會和九龍峰譚公祖廟醮會除儀式中敬拜的神明不同外,其科儀流程和儀式中所誦的經文都是一致的。
惠東山區的一些民間俗神,其信仰儀式也與佛教的水陸道場和道教的齋蘸法事相似。如惠東高潭鎮的林爺仙信仰。林爺,名林四,惠東高潭侯田村人。傳說他在雙下潭(今高潭水庫大壩附近)“得道成仙”。后人便在他成仙的地方立廟祀念。在高潭圩門口有七年一度的的紀念林爺仙的林爺醮會。該醮會自20世紀50年代中斷,直至2004年恢復為第一屆,2012年進行了第二屆。醮會的流程為正月初四日埔壇,正月初五日醮會接醮會份內的神明(包括西來庵佛祖),正月初六日各燈篙接神,正月初七日酬醮開始,正月初八日各燈篙進香,正月初九日醮場內上刀山,正月初十日至十二日出游三天,正月十三日正醮,晚上施食并送齋神回壇。正月十四日開葷祭天神并送所有神明回壇,后散醮。[37]可見,惠東山區內的俗神醮會儀式以佛教神明為主,其儀式流程也采用道教的醮會流程。
一些學者認為,隨著佛教在世俗社會影響力的增大,許多民間信仰神靈通過受戒、絕血食、齋食等佛教形式轉向佛教。[38]這種現象在惠東各地的醮會儀式前都有表現。如在惠東鹽洲島李甲村,在每年正月進行的三圣宮舞火龍儀式前幾天,村民要進行齋戒,以示虔誠。[39]
綜上所述,惠東民間神明信仰的佛道界限并不明顯,信仰中的功利色彩突出。如在惠東平海古鎮,鎮上所供奉的神祗達100多個,各種神廟也以百計。[40]惠東神明信仰這種“無論佛道,多多益善”的實用功利色彩,有其深厚的歷史根源。惠東依山靠海的自然環境使生活在這里的客家和福佬居民形成“登山可樵,出洋能漁”的包容性生產方式。因此在惠東地區形成籠而統之的全神崇拜,本著“有用則信,暫時無用也不得罪”的功利性原則,其神明信仰打破佛道的界限。同時佛道也樂于利用民間信仰擴大其影響,借助民間信仰龐大的信眾,謀求其在地方社會的發展。
惠東神明信仰作為嶺南文化的組成部分,具有傳承傳統文化、增加文化認同的社會功能。因此要研究梳理好這些民俗信仰文化資源,對其進行“提純復壯”,使得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挖掘、提升和發展,為嶺南地區鄉村振興建設“美麗鄉村”和“特色小鎮”建設增加更多的文化內涵和文化魅力,加速實現文化振興。
注釋
[1]本論文為廣東省教育廳2017年重點平臺及科研項目:《工學結合模式下高職院校思政課實踐教學與專業實訓融合研究》2017GWTSCXO62成果。
[2]《漢書》卷二〇《郊祀志下》。中華書局,第1241頁,1962。
[3][明]王臨亨:《粵劍篇》。載《元明筆記史料叢刊》,中華書局,第77頁,1987。
[4][10]廣東省惠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惠東文史》(第8輯),第71頁,1989。
[5][6]惠東縣地方志辦公室編:《惠東縣志》,中華書局,第888頁,2003。
[7]清光緒七年(1881)修《惠州府志》卷四十四《人物》。
[8] 2017年11月筆者在惠東范和村譚公太平清醮會田野調查所得。
[9]石滄金:《海外華人民間宗教信仰研究》,學林書局,第215頁,2014。
[11]朱金濤:《吉隆坡華人寺廟的研究》,馬來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68。
[12]鄭煒明、陳德好編著:《醮會道釋—港澳朱大仙信仰的人類學田野調查》(2008-2012),澳門理工學院,第7頁,2013。
[13]鄭煒明、龔敏:《香港朱大仙信仰的來源、建醮與展望》。《民間文學年刊》2009年第3期。
[14]王子軒:《平海古城城隍廟醮會博眼球》,《惠州日報》2015年10月31日第A8版。
[15]惠東縣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惠東縣僑務志》,第21頁,1992。
[16]惠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內部資料。
[17] 2017年2月筆者在惠東黃埠鎮田野調查所得。
[18]葉春生、施愛東主編:《廣東民俗大典》(第2版),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第364頁,2010。
[19] 《中國海島志》編纂委員會編著:《中國海島志·廣東卷》(第一冊)。海洋出版社,第551頁,2013。
[20] 資料為2017年在惠東稔山鎮、黃埠鎮、高潭鎮和白盆珠地區調查所得。
[21]劉志文主編:《廣東民俗大觀》(下卷)。廣東旅游出版社,第556頁,2007。
[22]廣東省惠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惠東文史》(第二輯),第71頁,1990。
[23]包國滔:《惠東畬族歷史文化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第61頁,2017。
[24]劉桂儒:《走進范和》,南方日報出版社,第12頁,2009。
[25][33] 鄭振滿、陳春聲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建人民出版社,第430、426頁,2003。
[26]清順治十八年(1661)修《潮州府志》第十二卷《古今文章》。
[27]沈麗華、邵一飛主編:《廣東神源初探》,大眾文藝出版社,第138頁,2007。
[28]陳訓廷主編:《惠州風物擷勝》,廣東人民出版社,第172頁,2016。
[29]吳金夫編著:《三山國王文化透視》,汕頭大學出版社,第17頁,1996。
[30]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86頁,2008。
[31]惠東縣地方志辦公室編:《惠東縣志》。中華書局,第888-889頁,2003。
[32]廣東省惠東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惠東文史》(第6輯),第116頁,1998。
[34] 2017年5月筆者在惠東范和村田野調查所得。
[35]《西來古剎法會》,惠州市非物質文化研究中心內部資料。
[36]《九龍峰祖廟廟會》,惠州市非物質文化研究中心內部資料。
[37]2117年10月筆者在高潭鎮調查所得。
[38]曹剛華:《明代佛教方志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175頁,2011。
[39] 2017年2月筆者在惠東鹽洲島李甲村田野調查所得。
[40]李清華:《東江民間會節的模式與當代利用初探》。《神州民俗》(學術版)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