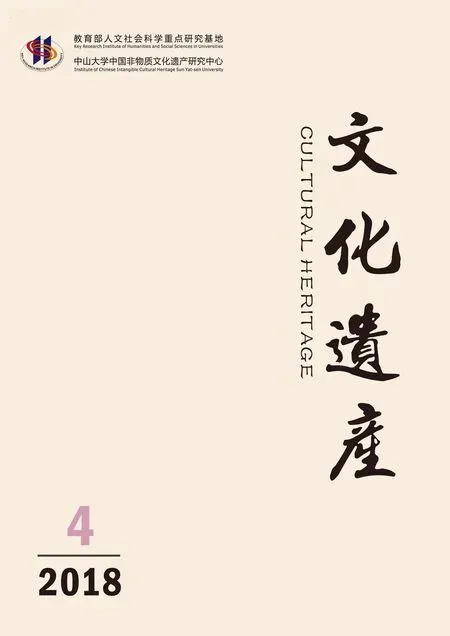從梅花拳“拜師禮”看近現代華北村落中的禮俗互動*
張興宇
引 言
長期以來,從禮俗之二元視角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內在性質、運轉機制等問題展開分析與討論,已在學界有著悠久的傳統。早在20世紀初葉,王國維對甲骨文中的“禮”字予以生活化的解讀,將禮定義為一種敬神祭祀的方式,并提出“古者行禮以玉”“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等觀點*王國維:《觀堂集林》(外二種),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4頁。。錢穆更是認為:“其實人生一切行事皆屬禮。此一‘禮’字,便把人生徹頭徹尾,無大無小,無不歸納……自周公孔子以來,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多禮的民族,中華文化亦成為一多禮的文化。”*錢穆:《雙溪獨語·篇六》,《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第113頁。顯然,他是將“禮”作為認識中國社會的核心概念,據此標志與西方社會的分野。20世紀90年代以來,又有學者特別關注中國傳統社會各階層對于禮的不同運用狀況,以科大衛關于華南宗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為代表。科大衛將“禮儀標簽”視為理解中國社會基本性質的重要概念:“禮儀在中國傳統社會扮演著重要角色,而宗教和法律的結合往往透過禮儀表達出來。通過接受禮儀的改動,中央和地方相互之間的認同得到加強。”*科大衛:《國家與禮儀:宋至清中葉珠江三角洲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5期。劉志偉提出,華南宗族往往是將自身血統來自中原的“歷史記憶”,作為在帝國秩序中獲得“合法”身份的文化手段。通過認同國家文化的方式,強調自己行為合乎禮法,炫耀功名以及宗族門第*劉志偉:《地域社會與文化的結構過程》,《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就是說,禮儀不僅作為一種文化標簽而存在,它還在國家大一統進程與地方社會生活的雙向互動中發生了在地化的推演。
近年來,部分學者進一步將研究視野聚焦于民間社會,注意從禮俗的互動邏輯入手重新理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在同一次筆談*趙世瑜、李松、劉鐵梁:《“禮俗互動與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三人談》,《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中,趙世瑜將禮俗問題視為中國的多元文化被統一到一個整體之中的關鍵性問題,認為通過禮儀制度的設置,禮與俗在很大程度上被緊密地結合起來,越來越密不可分。劉鐵梁則注意到,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傳統的民間禮俗,不僅用于維持基層社會秩序,而且對于國家禮治目標的實現具有決定性作用。張士閃將“禮俗互動”視為中國傳統社會中最重要的文化政治制度設計,認為這種互動實踐奠定了國家政治設計與整體社會運行的基礎,因而應該成為“理解中國”的基本視角*張士閃認為,“禮俗互動”的核心要義在于借助全社會的廣泛參與,將國家政治與民間“微政治”貫通起來,保障社會機制內部的脈絡暢通,以文化認同的方式消除顯在與潛在的社會危機。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顯然,上述學者關于禮、禮儀、禮儀標簽、禮俗互動等的層進研究,深化了對于中國社會性質的認知。本文即循此路徑,以冀南鄉村梅花拳為個案,聚焦其拜師禮在近現代華北民間社會的傳承、運行機制及生活實踐,試圖對華北民間社會中禮俗互動的具體機制予以顯微鏡式的觀察與探討。
一、何以為師?何以為徒?
師徒傳承,往往被民間武術組織視為其在鄉村社會生長、發育的基本制度。師徒傳承方式促進了民間各類拳種的獨立發展,形成了眾多的武術流派*凌靜園:《武術師徒傳承模式的文化分析》,《中華武術》2013年第4期。。一定意義上看,師與徒既是維系“師門”關系的基礎性要素,也是民間社會進行師徒禮儀實踐的核心組件。因此,首先應對“師”、“徒”的概念內涵予以厘清。
眾所周知,在中國古代社會,關于“師”的內涵闡釋以唐代文學家韓愈最為典型。如其在《師說》中所言:“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羅斌編:《唐宋八大家散文鑒賞》(第1卷),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5年,第28頁。。此處點明了為師者的職責和功能所在,即傳道、授業、解惑。而在日常生活范疇,人們對于為師者通常慣用師傅和師父兩種稱謂。若從詞源學角度辨析,師傅一般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代指傳授技藝的人,二是指對有技藝的人的尊稱。在儒家經典《谷梁傳·昭公十九年》中曾有記載:“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陳戊國點校《四書五經》(下),長沙:岳麓書社2014年,第1603頁。此處的師傅即指老師之意。在中國傳統社會,通常將帝者之師統稱為師傅,如一般把太師、太傅合稱為師傅;在民間社會則普遍流傳著“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的鄉土俗語。而在封建社會時代,師傅也專指對僧尼、道士及衙門吏役的敬稱。過去在工匠商業、梨園曲藝、武術等傳統行當中,相對于徒弟而言,師傅享有著絕對的行業權威。
至于師父一詞,從廣義層面看,其與師傅同義。雖然二者都泛指從事教學、教導工作的老師,但師父一詞更強調師徒之間情若父子的倫理關系。過去尤其是在工匠、梨園、武術等傳統技藝領域,一般是由師父負責收養徒弟,直至最后技藝學成,謂之“出師”,在中國傳統社會也普遍流傳著“一日為師,終生為父”的民間俗語。莊士敦認為,雖然師生關系沒有列于“五倫”——“五種人倫關系”之列,但卻與其中“兩倫”密切相關,即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和朋友之間的關系。因此,中國人的規范要求學生要像尊重父親那樣尊重老師*[英]莊士敦:《儒學與近代中國》,潘崇、崔萌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頁。。因此,在師父和徒弟之間,二者日常關系往來相對密切,隨之搭建了一種擬制的“父子”親屬結構。
有師必有徒,民間通常將“師徒”并稱。徒弟多是代指從師學藝之人,亦常見于中國古代小說、戲曲等文學作品之中。例如,在《西游記》中曾載:“你這去,定生不良。憑你怎么惹禍行兇,卻不許說是我的徒弟。”*(明)吳承恩:《西游記·悟徹菩提真妙理,斷魔歸本合元神》。這里提及的“徒弟”,便專指師父傳道授藝的對象。又如明代賢臣王恕曾在《王端毅奏議》(卷十三)中提及:“且道士之稱受業師,則曰師父;于師前自稱,則曰弟子,此理之正也。”他描述了師父和徒弟之間的上下互動結構關系,也就是說,為師者應當講究師道,為徒者則應遵守徒道。在中國傳統社會,圍繞著“師”、“徒”等核心概念,逐漸衍化形成了師生關系、師門組織和師道規矩等多重社會交往框架。一方面,師父與徒弟之間有著比較嚴明的等級關系,并且“師”的身份要明顯高于徒弟。比如在傳統工匠行業,徒弟拜師之后,雖然享有“家人”的身份和名號,但其實地位相對低下。而在民間社會,亦廣泛流傳著“三年徒弟,三年奴隸”的說法,足見徒弟之身份常常處在低位。另一方面,徒弟在從師學藝時,往往先要經受極為艱苦、苛刻的生活考驗。這不僅能磨煉徒弟的精神意志,也由此樹立了相對嚴苛的師門管理規矩。
當然,大多數情況下,師父在傳授技藝時,并非是完全和盤托出,往往會自留一手,以防“教會徒弟,餓死師傅”。從本質上而言,“師”的主要職責和任務是傳授“徒”在某一領域生存或生活的技能。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師”與“徒”之間始終缺乏真正的血緣關系基礎,其實卻通過擬制血緣關系的社會身份確立過程,營造出了一種看似權威的、長久的師徒禮儀關系。
二、“三師調教”:梅花拳拜師禮的實踐與延伸
可以說,中國傳統社會的諸多行業已注意到師徒關系在拓延個體社交網絡的重要媒介作用。以梅花拳為代表的民間武術組織,特別重視師徒關系的維系與擴展。在華北鄉村地區的梅花拳組織內部,存在著一種非常典型的師徒禮儀互動模式。其中,基于“三師調教”的拜師收徒機制而構建的“師徒”邏輯框架,顯示出對于師徒之間結構關系的推重。
夫我國拳術派別之眾百有余門矣,但溯其源泉則一也。蓋學拳者側重于身體之一部,而展其所長,另創一家,于是門派生焉。迄今尤能保持原有狀態者,僅梅拳耳。……其內容基本則五勢四門架子八方成拳擰拳梅花樁等。五勢為大順拗小敗五勢是也。勢如梅樹之花葉也,而架子如樹之根干河之源泉,惟其變化又惟其特長矣,茲分志之*燕子杰:《中國梅花樁文武大法》,青島:青島出版社1998年,第237頁。。
這段文字出自一份流傳于河北省廣宗縣鄉村的清乾隆年間手抄本拳書——《梅拳秘譜》。一直以來,梅花拳在華北鄉村地區廣泛流傳,民間百姓習練此拳者甚眾。與其他單純講究武功技法的民間拳術不同,梅花拳一般采用文場、武場相結合的習練方式*梅花拳武場主要習練武功技法,文場則以“天地君親師”的祖師敬拜為典型特征。唐韶軍、戴國斌:《對梅花拳名稱來源的考證》,《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尤其是梅花拳的文場修煉,通常以“秘不示人”的神秘形象展示給外界,因而顯異于中國其他民間拳派門類。在近現代華北鄉村社會,梅花拳這一植根于民眾日常生活之中的鄉土拳術,以其獨特的健體、修心、娛樂和教化等多重功用,持續影響著冀、魯、豫一帶鄉民的禮俗生活傳統。綜而觀之,鄉村梅花拳的日常拜師收徒儀式主要包括兩種類型:一是村民單純為學習梅花拳拳法技藝的武場拜師方式,另一種則是以祖師敬拜為典型特征的文場拜師方式,而梅花拳的文場是該拳派的領導核心*燕子杰:《論梅花拳的文場與武場》,《社會科學研究》1991年第3期。。通常說來,拜師收徒儀式主要由梅花拳文場師傅統一組織安排,梅花拳弟子將其稱為“當家人”,這也預示著他們在處理村落梅花拳公共事務時要比旁人付出更多的精力和物力。鄉村梅花拳自身形成的“文武合一”自治組織方式,內含著比較特殊的拜師禮儀結構,具體表現在以“三師調教”為典型的拜師禮儀實踐中。
第一,“三師調教”是確立梅花拳師徒名分的主要依據。“三師調教”作為梅花拳內部特有的拜師禮儀運作機制,三師分別代指引師、送師和恩師*張士閃:《民間武術的“禮治”傳統及神圣運作——冀南廣宗鄉村地區梅花拳考察》,《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在村落社會生活中,文與武構成了鄉村梅花拳“開道度人”價值訴求的基本內容*周偉良:《梅花拳信仰研究——兼論梅花拳的組織源流》,《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實際上,鄉民如果只是為了學習梅花拳拳法技藝而舉行的武場拜師流程相對簡單。按照鄉村梅花拳的民間禮數,村民學拳拜師入門時必須遵循“三師調教”的儀式化程序,這也是確立梅花拳師徒名分的主要依據。一般而言,村民初始學拳多在青少年時期進行。當他們的梅花拳拳術功法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如果個人仍有意向繼續鉆研學習,梅花拳文場、武場師傅才會為其統一組織集體拜師收徒的入門儀式。而且,對于習拳者將要拜師的具體對象,村民本人事前并不知曉。“拜誰為師”需由梅花拳文場、武場師傅商議后再做決定。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主要根據拜師者習練梅花拳的功底水平酌情分配,一般是拜本村不同姓氏或外村的梅花拳武場師傅為師。例如,北楊莊梅花拳弟子王英武,他自幼習練梅花拳,尤其擅長梅花拳腿功,二十七歲正式拜師入門。當時梅花拳文場師傅給他安排的引師為本村老拳師王占,送師是梅花拳“當家人”邢銀超的母親,授業恩師則為谷常相村梅花拳名師谷景華*被訪談人:王英武,男,北楊莊村民;訪談人:蔣帥;訪談時間:2015年4月6日;訪談地點:北楊莊。。事實上,就梅花拳的拜師禮儀規矩而言,所謂“三師調教”中的引師、送師和恩師主要起到了見證人的象征性作用,它同時意味著鄉村梅花拳組織內部通過“師徒”關系建立了一種身份象征和認同機制。
第二,“三師調教”是強化梅花拳師徒禮儀的根本基礎。具體說來,“三師調教”中的引師、送師和恩師所承擔的師徒責任各不相同。涂爾干認為:“人們對事物進行分類,是要把它們安排在各個群體中,這些群體相互有別, 彼此之間有一條明確的界限把它們清清楚楚地分開來。”*[法]涂爾干、[法]莫斯:《原始分類》,汲喆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頁。在廣宗縣各鄉村普遍流傳著“送師大、引師小”的說法,恩師是指拜師入門后真正的指導老師。梅花拳收徒又分為兩類,一類徒弟是授業門生,他們多數繼承了家庭上一代習練梅花拳的武術傳統,而且所找的引師、送師也皆為村內梅花拳群體的熟人;另一類是創業門生,他們屬于家庭接觸梅花拳的第一代弟子,引師、送師、恩師都需經梅花拳文場師傅商議之后才能確定。當鄉村梅花拳組織拜師儀式時,一般先按照拜師人數情況擬定三至五位參與拜師儀式的梅花拳文場師傅成員,然后再由他們統一商議安排具體的拜師程序。正式拜師前需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由拜師者自愿選擇進入梅花拳文場或武場。梅花拳文場師傅依據拳班內部的輩分排序,經引師、送師、恩師等進行了所謂的“三師調教”程序后,最終完成拜師禮儀。其中,“三師調教”中的送師(保師)身份非常重要。他既是對新入門梅花拳弟子人品的身份擔保,之后也是約束弟子日常行為的名譽象征。進而言之,徒弟原本代表個人行為,一旦進入師門,也就加入了象征地域社會自治力量的武術權威組織。梅花拳的師門組織、送師組織和更寬泛的地域武術組織在無形之中對新入門梅花拳弟子產生一定的約束力和控制力,這也是其強化梅花拳“師徒”禮儀的根本基礎。
第三,“三師調教”是展開梅花拳師徒禮儀實踐的重要渠道。梅花拳拜師之后進行師徒禮儀實踐的主要方式,是通過營造、培養師徒之間一種“情同父子”的親密社會關系來實現。在鄉村梅花拳內部流傳著“梅花拳,父子道”“天下梅拳是一家”等多種說法,梅花拳師徒之間可以互稱“父子爺們”。梅花拳又被稱為“父子拳”,這也是在強調梅花拳弟子之間的一種非血緣“擬親屬”關系。此外,依托親人、熟人與陌生人三者之間的互動結構關系,也是鄉村梅花拳組織展開師徒禮儀實踐的重要路徑。其中,親人關系是以傳統家庭的血緣和姻緣的親屬關系為基礎而建立。例如,早年間雖然北楊莊梅花拳武場練拳活動面向全體村民,但文場知識最初只允許在邢氏家族內部傳播,直至后來才逐漸借助姻親關系向村內王氏、劉氏等其他家族拓延*被訪談人:邢尚娥,男,北楊莊村民;訪談人:張興宇,周連華;訪談時間:2016年7月10日;訪談地點:北楊莊。。熟人關系是以地緣為聯結紐帶,它通過地理實體范圍進行界定。近至街坊鄰居,遠至周邊村落,鄉民多是在一個距離有限的地理實體范圍內組建日常生活圈子。在村落社會生活中,文與武構成了鄉村梅花拳“開道度人”價值訴求的基本內容。*周偉良:《梅花拳信仰研究——兼論梅花拳的組織源流》,《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梅花拳師徒禮儀實踐中的武場傳藝和文場傳道行為,通常基于這種熟人關系不斷往外傳播。陌生人是指處于村落日常生活邊界之外的人群,這一類人群既可能是來自外地的梅花拳弟子,也可能是普通的陌生人。因此,按照梅花拳的師徒禮儀規矩可迅速判斷陌生人的“底細”,確定身份后即可決定是否與其進一步交往。需指出的是,鄉村梅花拳組織構建的“親人-熟人-陌生人”這一師徒禮儀實踐框架還可以互相轉化。盡管如此,鄉民在村落日常生活中仍難免會出現各類問題,這種框架只是梅花拳師徒禮儀實踐的一種“理想型”模式。
三、梅花拳拜師禮與鄉村社會
正是由于梅花拳拜師禮及其相關師徒禮儀規矩的存在、運行,才使得這一民間武術組織在鄉村社會中顯得更加神秘、神奇與神圣。大致說來,經由梅花拳拜師禮形成的一種擬制血緣關系,使其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民間武術組織,并內化、凝結于鄉村社會的日常交際網絡之中。再者,與鄉土村落中其他自治組織形式相比,梅花拳拜師禮的神圣感實際上還與鄉民日常節日生活體系中的神圣感緊密相連。而且,在梅花拳拜師禮的基礎之上,構建了一個組織相對龐大的“師門”社會群體。
(一)拜師帖:“門戶”身份的確認
在鄉村梅花拳組織內部,普通村民一旦經過“三師調教”程序確認了梅花拳弟子身份之后,也意味著他被這一群體成員在師徒“門戶”層面所接納。戴國斌曾從武術社會學的獨特視角,詳細闡釋了“門戶”觀念對中國傳統武術門派的影響。他認為,門戶成員之間的社會關系,以一種準家族的方式進行互動。這種準家族方式,其實間接明確了師傅與徒弟之間的日常交往身份,即擬制的親屬關系,圍繞著師傅這一親屬核心,師傅與眾多徒弟之間形成了一個小范圍的社會關系網絡*戴國斌:《中國武術的文化生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4-105頁。。梅花拳弟子一旦拜師入門后,在眾多弟子之間便形成了一種“擬親屬”社會關系結構,并深刻融入到鄉民的日常生活領域。如果從“師”的角度來講,師徒之間具有“義”的職責*唐韶軍:《生存·生活·生命:論武術教化三境界》,上海體育學院201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66頁。。這種師徒關系表面上看起來與梅花拳“子不拜父為師”的傳統規矩有所矛盾,但它更強調梅花拳師徒“門戶”間的倫理親情觀念,這實際上也是梅花拳增強內部凝聚力與群體認同感的“抱團式”運作機制。
首先,書寫拜師帖,是一種確認梅花拳師徒名分的紙質憑證。實際上,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使用文字書寫的書面文本在鄉民日常生活中較少出現,除非其在某些方面對鄉民具有特殊的社會作用和意義。我們在村落社會中比較常見的書面文本包括家譜、碑刻、地契文書等民間文獻,拜師帖作為拜師禮中不可或缺的書面文本,梅花拳尤其強調“無帖不成師徒”。時至今日,廣宗鄉村梅花拳仍傳承著拜師之后互存拜師帖為證的民間習俗。這種拜師帖一般是用紅紙黑字書寫,帖中內容要把引師、送師、恩師及拜師人員的姓名信息一并寫明,拜師帖需經具有一定文字功底的梅花拳文場弟子執筆。例如,過去北楊莊梅花拳弟子邢尚斌文、武功力深厚,且擅長書法,所以該村書寫拜師帖的具體事務皆由他來完成*被訪談人:邢尚娥,男,北楊莊村民;訪談人:張興宇,周連華;訪談時間:2016年7月10日;訪談地點:北楊莊。。書寫拜師帖時,新入門梅花拳弟子的輩次要參照師傅的輩次往下自然順延一輩,并在拜師帖的落款處標明拜師時間。在舉行完簡單的敬茶、敬酒、鞠躬或磕頭等梅花拳拜師儀禮之后,已成師徒的梅花拳成員之間要各自收存一份拜師帖。它不僅是“師門”內部以后進行社會交往的重要憑據,也是鄉村梅花拳組織篩選成員的一種出入渠道。但是,這種拜師憑證并不必然指向所謂秘密社會的關系聯結,或者走向與國家政治相背離的社會自組織制度。它主要通過內部的師徒名分確立,連同拜師禮之中的祖師訓條、師門規矩等“門戶”身份,建構一種相對穩定的師徒傳承系統。如北楊莊梅花拳武場師傅王尚信收藏的拜師貼所示:
拜師帖
拜帖:引師李玉普,送師邢尚寶,拜廣宗縣北楊莊村十四輩孫王尚信師傅大人臺下門生,本縣件只鄉西宋村徒韓子潤叩拜,二零一五年古二月二日吉時。
拜帖:引師霍德慶,送師王奇亮,拜廣宗縣北楊莊村十四輩孫王尚信大人臺下,本村十五輩孫劉金亮晚生叩拜,公元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拜帖:引師李玉普,送師張文同,拜廣宗縣楊莊村十四輩孫王尚信大人臺下,威縣東平村十五輩孫趙振群晚生叩拜,公元二零零六年五月初八日。
其次,拜師帖既是確認梅花拳成員師徒關系的標志物件,也是維持日常師徒關系的關鍵憑證。通過上示拜師帖內容可以看出,北楊莊梅花拳武場師傅王尚信平時傳授拳技所收的徒弟,所涉地域范圍既包括本縣本村的鄉民,也不乏外縣外村的梅花拳習練者。王尚信身為拜師人員的“授業恩師”,日常主要承擔著指導梅花拳拳理、傳授拳技的職責。這些梅花拳弟子在拜師之后,每逢年節還需到師父家中探望以示尊敬。當然,在梅花拳拜師禮這樣一種特殊的禮儀規定之中,引師雖然并不承擔日常的武術教授職責,甚至僅僅在拜師禮的儀式現場出現之外,以后師徒二人可能再不相見。但它之所以需要在此正式場合出席,其實內含著鄉土社會更為深厚的禮俗運作邏輯,此即李松所謂禮俗之間的“互滲和諧”狀態*李松認為,禮與俗的互動主要包括三種方式:一是互滲和諧,二是各行其道,三是沖突模式。趙世瑜、李松、劉鐵梁:《“禮俗互動與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遷”三人談》,《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此外,梅花拳拜師與傳師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概念。所謂拜師一般要拜輩分比自己大的師傅為師,但傳師則不拘泥于此范疇。如在梅花拳內部流傳著“梅花拳倒卷簾,徒弟倒把師傅傳”的說法。在鄉民看來,梅花拳弟子之間交流拳術功法無需顧忌年齡大小之分,只有技藝高低之別。而且,由于鄉民日常生活圈子的地理距離差異所限,跨村落的梅花拳弟子之間的社會交往頻度并不一致。這也表明,中國傳統鄉土村落并非是封閉性的,鄉民利用梅花拳拜師帖來密切跨越地緣的組織關系。由此串聯起各個鄉村,形成了廣宗地區獨特的梅花拳社會組織網絡。通過拜師帖與師徒之間的日常交往機制,促使鄉村梅花拳組織內部的師徒“門戶”網絡不斷強化和鞏固。
(二)拜祖師:“神圣”的社會組織聯結
事實上,縱觀梅花拳拜師禮走向神圣化的變動過程不難發現,其主要依托一套“天地君親師”的敬拜祖師禮儀在村落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就鄉村梅花拳組織而言,“天地君親師”的祖師敬拜模式有助于強化群體成員的師徒禮儀認同感和日常“神圣感”的聯結。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民間敬拜“天地君親師”的習俗由來已久。據余英時考證,“天地君親師”觀念的生成經歷了一個從民間社會逐漸發展而來的系統過程。他曾引用清楚廖燕(1644-1705)所著《二十七松堂集》卷十一中《續師說》一文解釋道:“宇宙有五大,師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親;五曰師。”文末亦有魏禮評語云:天地君親師五字為里巷常談,一經妙筆拈出,遂成千古至文。張履祥(1611-1674)在《喪祭雜說》中曾載:家禮祠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其稍知禮者,則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親師,而以神主置其兩旁。據此,余英時推斷在明末地方社會敬拜“天地君親師”的習俗已經流行開來,但當時并非家家戶戶都立有“天地君親師”五字的牌位或“紅紙條”*余英時:《現代儒學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7-169頁。。這既是“天地君親師”祖師敬拜禮儀產生的社會基礎,同時也是拜師禮植根于鄉土社會的主要表現。
不僅如此,陳獨秀在《舊思想與國體問題》一文中曾描述過民國時期中國鄉村百姓供奉“天地君親師”的民間習俗:“鄉里人家廳堂上,照例貼一張‘天地君親師’的紅紙條,講究的還有一座‘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原載于《新青年》3卷3號,1917年5月1日,第3頁。。魯迅亦在其雜文《我的第一個師傅》中提及“天地君親師”:“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著一塊牌位,用金字寫著必須絕對尊敬和服從的五位:‘天地君親師’”*魯迅:《且介亭雜文末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第89頁。。另外,依據車錫倫的研究表明:明清時期的民間秘密宗教羅教、天地門教等都曾供奉過神主牌位“天地君親師”。他推測“天地君親師”的概念很可能由明代民間秘密教團首先提出,后來逐漸為鄉土社會普遍接受*車錫倫:《“天地君親師”牌位的出處》,《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費孝通也曾指出,中國社會的基本聯系是親屬關系,它從血緣上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師生關系則是擬制親屬關系,“天地君親師”中的“親師”就是從親屬關系到師生關系的典型表現*王慶仁等編《吳文藻紀念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頁。。由此可見,“天地君親師”的祖師敬拜觀念在中國鄉土社會具有相對深厚的歷史根基和比較久遠的民間傳承脈絡。
具體到梅花拳師徒在日常生活中進行的“天地君親師”祖師敬拜活動來說,鄉民尤其重視、強調以精神皈依為基本表現形式的祖師敬拜禮儀。其實它的根本發展動力在于,祖師敬拜禮儀的背后連接著更為寬廣的地域社會的人神互惠機制*正如劉曉春在考察明清以來番禺地區迎神賽會傳統時指出,不同血緣群體重新建立的地域社會聯合,是人神互惠結構的慣性發展。劉曉春:《“約縱連橫”與“慶敘親誼”——明清以來番禺地區迎神賽會的結構與功能》,《民俗研究》2016年第4期。。目前較據代表性的觀點是,在鄉村梅花拳內部雖然有“大架”梅花拳和“小架”梅花拳之區分,但多數認同“大架小架是一花,五爐六爐是一家”,并且他們都講究敬奉“天地君親師”*唐韶軍:《梅花拳何以成為“義和拳運動”的主導力量》,《民俗研究》2013年第6期。。在廣宗縣梅花拳文場師傅收藏的一份《梅拳秘譜》中,詳細記錄了梅花拳內部敬拜“天地君親師”的說法*此份《梅拳秘譜》由廣宗縣前魏村梅花拳文場師傅李玉普收藏。:
庭訓數載,惜乎未能文成,但文事固重,武備亦不可不習。武藝獨稱高強,如固國名將,能周游四方千余里,一時之從學門徒者,不下數百人。我先君先語,以作善事,敬“天地君親師”。
據梅花拳祖師之一、清朝武探花楊炳所著的《習武序》一文記載,梅花拳拳堂敬拜規矩,是把“天地君親師”牌位置于非常顯要的位置的*(清)楊炳:《習武序》,該手抄本由北楊莊村民邢尚娥收藏。。梅花拳師傅在傳授梅花拳文場、武場技藝的過程中,通常也會向弟子講授敬拜“天地君親師”這一祖師禮儀的意義價值。不過,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在村落日常信仰生活實踐中,鄉民對于梅花拳“天地君親師”的概念認知并不完全一致,其日常敬拜禮儀往往會依據個體的實際生活需求隨時做出變通。比如對于“天地君親師”,現今鄉村梅花拳弟子就流傳著一種很通俗的解釋:“天”代表風調雨順;“地”代表五谷豐登;“君”代表國泰民安;“親”代表父母親人;“師”代表授業傳道*被訪談人:邢銀超,男,北楊莊村民;訪談人:張興宇,蔣帥;訪談時間:2015年4月7日;訪談地點:北楊莊。。雖然“師”在“天地君親師”的排序中列后,但在拜師禮中卻又以“尊師”的名義予以特別凸顯。不言而喻,借助拜師禮,“師”在“天地君親師”的神圣序列中獲得圣化,而這一禮儀也因此成為締結梅花拳師徒關系的神圣紐帶。
(三)拜師禮:德行、規矩與鄉土實踐
張士閃認為,既處于鄉村社會之中,且成為一種組織傳統,意味著梅花拳必然是鄉村社會文化體系的一部分*張士閃:《民間武術的“禮治”傳統及神圣運作——冀南廣宗鄉村地區梅花拳文場考察》,《民俗研究》2015年第6期。。盛行于冀南北楊莊一帶的梅花拳師徒組織,其典型的鄉土運作特征即是男性結社、互助自治。梅花拳拜師禮與鄉村社會生活緊密相連,在其內部還傳承著一系列較為“嚴苛”的與拜師禮儀相關的德行與規矩。一定程度上看,規矩意味著禁忌,鄉村梅花拳的內部拜師禮儀規矩是其維持組織神圣性的重要方式,而梅花拳這一神圣之物也需要持續地采用禁止性措施來對其進行保護*[英]道格拉斯:《潔凈與危險》,黃劍波等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7頁。。一方面梅花拳武場的技藝傳承特別注意師徒之間日常生活的德行熏陶,另一方面梅花拳文場師傅在組織內部享有一定的師徒禁忌權威,其本質都是在圍繞梅花拳拜師禮構建村落社會的“師徒”邏輯框架。
其一,德行修養是梅花拳拜師禮儀日常實踐的價值導向。梅花拳武場師傅尤其注重對其弟子的日常德行教導,他們在傳拳授藝的過程中也特別強調武德的重要性,這屬于一種鄉土道德價值觀的教化熏陶。梅花拳師徒之間通常將德行修養視為習武的首要前提,即“師有師德,徒有徒德”,此亦要求梅花拳拜師禮儀在日常生活中予以踐行。具體說來,鄉民一般從幼時開始學拳,這種德行修養教育長期貫穿于他們的習武生涯之中,在村落中還流傳著許多與梅花拳拜師禮儀相關的民間俗語。例如:“學武難,學武難,難倒名師受真傳”“傳武難,傳武難,傳給匪徒惹禍端。”其實,梅花拳弟子想把武術水平提升到一定高度,不僅意味著在拳理技法層面比別人付出多倍努力,更為關鍵的是要始終注重對自身武德的涵養。梅花拳門內流傳的“五要五不要”等規矩,則時常提醒這些梅花拳成員不可隨意招惹是非*“不許保鏢護院,不許欺師滅祖,不許欺男霸女,不許采花盜柳,不許偷偷摸摸。沒有武德,你練再好的拳也沒有,反而對社會還是有害的。你有了功夫,不能光想著欺負人,而是得多做好事。”被訪談人:邢銀皋,男,北楊莊村民;訪談人:周連華;訪談時間:2016年7月9日;訪談地點:北楊莊。。梅花拳師徒之間的德行高低與否,也直接影響著其在村落梅花拳組織體系內的權威與地位。同時,梅花拳具備的禮儀教化功能,意味著它在面向村落整體生活時有了更高的道德追求。相對于梅花拳武場的道德教化而言,梅花拳文場的教化知識更加豐富。在鄉村梅花拳內部,長期秘密流傳著大量拳譜、經卷等民間文獻資料。文場師傅善于借助此類文本教育門內弟子積德行善,言傳身教,并在村落日常生活中作出表率。因此,德行修養成為梅花拳拜師禮儀日常實踐的重要判斷指標。
其二,遵循規矩是強化梅花拳拜師禮儀實踐的鄉土底線。既成梅花拳師徒之后,他們二者都需遵循其內部傳承的禮儀規矩。具體說來,涉及到村落梅花拳內外的大事小情,皆需聽從文場師傅的統一指導,即“文場領導武場”。鄉村梅花拳組織在碰到集體性公共事務時,需由文場師傅負責統籌安排,其內部又多采用群體磋商的自治方式予以施行。例如,當村落梅花拳武術隊受邀外出參加表演活動,需先咨詢文場師傅的意見。而在梅花拳武術技法的訓練教授方面,武場師傅則更具發言權。正如馬林諾夫斯基所言:“文化根本是一種‘手段性’的現實,為滿足人類需要而存在,其所取的方式卻遠勝于一切對于環境的直接適應。而且,文化在滿足人類的需要當中,創造了新的需要。”*[英]馬林諾斯基:《文化論》,費孝通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第99-100頁。鄉村梅花拳組織隨同拜師禮儀而生成的各種民間規矩,本身蘊含著豐富的鄉土禮俗意涵。梅花拳師徒共同遵循的內部規矩,其實正是這一民間武術組織進行拜師禮儀實踐的鄉土底線。總之,德行與規矩是梅花拳拜師禮儀與鄉土社會發生作用的一種特殊方式。
結 語
綜上所述,從鄉村梅花拳的拜師禮中可以發現,以梅花拳為代表的民間武術組織,主要是在與鄉村日常生活的禮俗互動邏輯中,獲取自身在鄉土社會中的合法性與權威性的。誠如張士閃所言:“民俗文化畢竟貫穿著一方民眾的生活智慧與集體意志,承載著民間社會千百年來形成的道德觀念、精神需求、價值體系等,構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群體行為規范”*張士閃:《禮俗互動與中國社會研究》,《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作為廣泛意義上的中國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梅花拳禮儀傳統的生成、發展和傳承過程,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鄉村社會語境密切相關。事實上,在鄉村社會中的其他組織形式中,也經常運用師徒的名分、禮儀及行為實踐,標示禮儀,影響社會。民俗文化本身也是一個整體系統,常常借禮之名,行俗之實;或禮俗并用,化俗成禮,形塑為不同的民俗傳統。卻又依托于一個個村落或跨村落的生活共同體,不斷強化以禮俗為表征的鄉村價值觀。
換言之,梅花拳拜師禮儀實踐及相關活動,如果脫離了更廣泛鄉民的認可與參與,便將失去鄉村生活根基,喪失其傳承動力。透過鄉村梅花拳背后的師徒傳承機制,可以發現武術禮儀與鄉土禮俗傳統的互構態勢。表面上看來,梅花拳作為鄉村社會一種特殊的武術組織形式而存在,但在日常生活中,它與廣泛意義上的鄉村禮俗生活始終處于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互動之中。梅花拳師徒之間通過擬制血緣的社會身份確立過程,營造出一種看似權威的、長久的師徒禮儀關系,并以“三師調教”的內部規則予以強化。圍繞師徒形成的“師門”關系網絡,通過交往話語、行為與周邊鄉土社會發生連接,孕育了村落社會層次分明、顯隱兼具的禮俗互動模式。尤其是在以梅花拳為典型的鄉土社會,以梅花拳拜師禮為代表的傳統武術禮儀,深刻影響著當地民眾的日常生活,形成一套至為深厚的禮俗運作機制。此時,梅花拳的特殊禮儀規定,與其所處鄉土社會的民俗生活互相交織、融合,卻并不完全混同。梅花拳依然會努力強調拜師禮等儀式的神圣與神秘特性,而鄉村社會也依舊遵循其固有的生活形態。就在這種有分有合的文化生態中,梅花拳作為鄉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獲得了傳承動力,并對村落社會的禮俗傳統發生著持久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