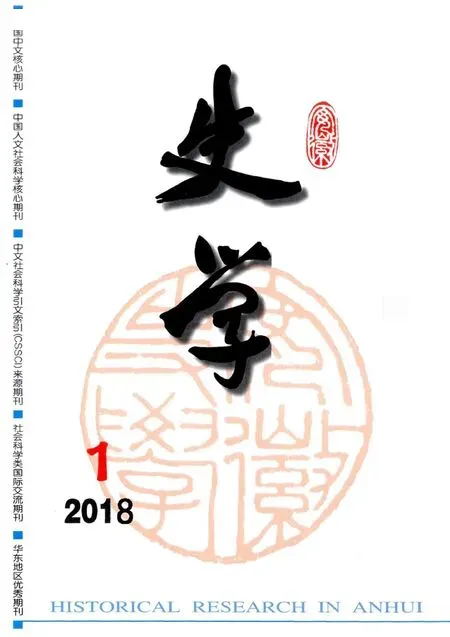劉秉璋學術活動述論
——兼論湘、淮軍精神氣質之異
吳懷東 尚麗姝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引程晉芳、周永年語)桐城派風格之散文是清嘉慶朝至民國初白話文運動興起前散文發展之主脈。1929年梓行的劉聲木(1876—1959年)《桐城文學淵源考》《桐城文學撰述考》,發心于鄉梓情結,是桐城派作為散文創作主流終結后對桐城派進行初步總結的兩部重要著作,也是桐城派研究的奠基之作,其確認了桐城派作家范圍及桐城派研究的大致輪廓。學術界對這兩部著作研究比較充分,雖然對劉聲木其人及其著述背景亦有所研究,不過并不深入。劉聲木在劉秉璋諸子中排行第三,在《萇楚齋隨筆》中對乃父劉秉璋讀書、著述活動情況記錄甚詳,以顯示自身學術其來有自且淵源深厚,惜乎學術界并未據此深究。本文即著墨于此,討論劉秉璋的學術活動及其特點。
劉秉璋乃晚清淮軍著名將領,其軍政活動已受到當今史學界的關注,而其學術活動則尚待清理。
劉秉璋(1826—1905年),字仲良,安徽廬江人,《清史稿》有傳。劉秉璋咸豐十年(1860年)中進士,被選為庶吉士,授編修。劉秉璋與潘鼎新早年赴京應考即拜入李鴻章門下。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軍占據江寧,劉秉璋隨欽差大臣張芾至皖南。李鴻章受曾國藩派遣組建淮軍進入上海鎮壓太平軍,即奏調劉秉璋于麾下。劉秉璋遂入淮軍,逐步成長為李鴻章所器重之大將,是淮軍十一大支中慶字軍的主要領導者。劉秉璋一生經歷了淮軍興起、發展、轉型等主要階段,在淮軍主要將領轉型為地方軍政領導后,其才能得到彰顯,地位更加顯赫。據王爾敏先生考察,與湘軍不同,“淮系將領,官至督撫者人數很少,早期只有張樹聲、劉秉璋,稍晚又有潘鼎新、劉銘傳兩人,一共四人。”*王爾敏:《淮軍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頁。其中劉秉璋轉任封疆大吏后積極作為,政聲卓著:任浙江巡撫,精心組織并取得了近代史上難得的浙江抗法勝利;后官至四川總督并主政長達8年之久(1886—1894年),保持了藏區以及西南地區的基本穩定,終因堅決抵制西方勢力在四川的傳教、開礦等行為而遭罷免還鄉。劉秉璋亦武亦文、文武兼備的身份在淮軍將領中異常醒目,在他的軍政活動中也顯示了傳統思想的深刻影響:在擔任四川總督期間,身為李鴻章一手栽培的地方大員,處理四川教案時能自覺堅持愛國立場,敢于頂撞李鴻章。本文則根據今所見劉秉璋之著述文字考察劉秉璋的學術活動情況——學術正是其處理軍政事務的思想方法、智慧之來源,并結合此個案,一窺淮軍文化及精神特征。
一、劉秉璋尚文性格及著述
劉秉璋在淮軍中帶兵打仗雖不及劉銘傳等人,論文化水準卻是淮軍中佼佼者,他和李鴻章是淮軍高級將領中僅有的兩名進士。據劉聲木《萇楚齋隨筆》記載,劉秉璋在戎馬倥傯之際依然手不釋卷,尚學好讀,學有根柢,甚至對煩難的小學亦深感興趣。他還建有藏書樓,名曰“遠碧樓”,藏書頗豐。*《萇楚齋四筆》卷5《遠碧樓藏書》,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下冊,中華書局1998年版,第774頁。劉秉璋不僅喜好讀書,還勤于筆耕,同時代人多有記載。今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有劉秉璋致張鳴珂(1829—1908年)、薛時雨(1818—1885年)函札各一通,亦可見他與同時期著名文士頗有交往,如致薛時雨函云:“道路太遠,送文不便,抽暇自為刪閱而已。”其身故后清廷謚號“文莊”。*《萇楚齋三筆》卷5《先文莊公撰述》,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上冊,第566頁。關于劉秉璋著述情況,劉聲木有如下載錄:
先文莊公亦自少好學,老而不倦,撰有《奏稿》八卷、《未刻稿》□卷、《強恕齋文集》二卷、《詩集》六卷、《方輿輯要》廿卷、《政典》十卷、《禮典》十卷、《讀書筆錄》十二卷、《漢書古字考》一卷、《喻言》二卷、《澹園小品》一卷、《古文鈔》十六卷、《古詩鈔》四卷、《今體詩鈔》四卷、《唐人絕句》一卷、《強恕齋日記》十六卷、《尺牘》八卷、《批牘》二卷、《朋僚函稿》廿卷、《外部函稿》十卷、《三省電稿匯存》十卷、《錦鱗集》十卷、《前集》廿卷、《后集》四卷,都廿四種,共壹百玖拾余卷。遺稿高至數尺,惟《奏議》選刊八卷。刊板及遺稿四笈,某甲攘為己有。宣統辛亥國事之變,更棄之惟恐不速,去之必欲其盡,以致先文莊公生平遺稿只字無存。后雖經聲木竭力搜羅,僅購得《奏議》八卷刊本,復編輯《強恕齋文集》二卷、《詩集》一卷、《澹園尺牘》四卷,擬編為《劉文莊公遺書》,惟尚須商酌,一時未能即付排印,鮮民實深愧怍。”。*《萇楚齋三筆》卷5《先文莊公撰述》,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上冊,第566頁。
另據劉秉璋第四子、劉聲木弟劉體智為劉秉璋《靜軒筆記》所撰序言可知,劉體智曾據劉秉璋讀書日記整理成書有《靜軒筆記》及其他著述“不啻六七種”。不過,目前看來,梓行的只有《劉文莊公奏議》和《靜軒筆記》。幸運的是劉秉璋部分手稿《澹園瑣錄》收藏于今安徽省博物院。
《劉文莊公奏議》由朱孔彰所編,收其同治四年(1865年)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奏議205通,都是日常政府公文,孫殿起《販書偶記》著錄為光緒戊申(1908年)刊本,8卷,流傳甚廣。
安徽省博物院所存劉秉璋手稿本《澹園瑣錄》,考其來源,應是劉體智所捐劉家舊物。此稿卷首載“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十(按:原寫作為“己亥七”,被涂抹修改為“辛丑十”)月既望”“仲良自記”云:
資性素鈍又善忘,每日讀書隨手摘錄,解組后家居無事,戊戌春粗分門類,以便檢查,類之中又有類焉。凡三易稿,皆手自謄寫,都為十二卷,天部一卷為類四,地部一卷為類八,人部五卷為類八,物部二卷為類八,通計四十余萬字,名之曰《澹園瑣錄》。
稿中有大量涂抹批改痕跡,甚至還有紙條夾注,沒有編制目錄,可見是劉秉璋本人對往日隨手記錄的讀書筆記進行了簡單分類謄抄而成。全稿采用類書體例,共計16冊(包括“人部補”與“物部補”各二冊)、40余萬字(據《澹園瑣錄》劉秉璋自撰序言),正文以“天”、“地”、“人”、“物”為題分為12卷28類。手稿內容涵蓋范圍甚廣,主要內容是抄檢已有知識:“天”部1卷4類,內容主要涉及天文歷法、自然現象、陰陽五行;“地”部4卷8類,包括對國內行政區劃、地理沿革、名山大川以及“四夷”風貌的介紹;“人”部5卷8類,此部分內容較為龐雜,然大體不出禮樂人倫儒典、武備政令官職、宗教方技雜談的范圍。經學所占比例不多,但劉秉璋的《詩經》學觀點在此部分也多少有所體現;“物”部2卷8類,分別為“法物”、“珍物”、“用物”、“食物”、“動物”五個方面,旨在釋物。從序言及內容看,《澹園瑣錄》確實屬于家用啟蒙教材或是普及基本知識見聞的“百科全書”。《澹園瑣錄》并未采取逐篇闡釋的形式,也未通過考據的手段深入闡發,而是以獨立著作為單位對章節進行劃分,涵蓋范圍以儒家經典為主,對著作的體例、流傳過程、主旨思想作大體介紹,間或涉及儒家學說的傳承問題,內容駁雜而淺顯。劉秉璋因處理教案不當于光緒二十年(1895年)被免官還鄉,直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病逝,一直鄉居讀書寫作,時間甚長。《澹園瑣錄》序中所提到的“辛丑”是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己亥”是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澹園瑣錄》應是劉秉璋鄉居期間所撰寫或整理,并經過其反復修改、潤飾而成。
劉秉璋勤于筆耕,從劉聲木所述可見其著述文字甚多,內容廣泛,涵蓋學術研究、文學欣賞等,“瑣錄”應該不止于我們今天之所見。遺憾的是,由于他是遭貶身退,又不幸趕上清末民國之交政治與社會動蕩,家族地位下降,其手稿沒有得到及時系統整理、刊刻。據劉聲木《萇楚齋隨筆》所云,散佚甚多,所以,現存清人著述書志中除了《劉文莊公奏議》外并沒有劉秉璋其他著述出版之記載。今發現國家圖書館藏劉秉璋參與撰寫的碑帖《廬郡會館記》,實在屬吉光片羽之珍。*今著名書畫家、《榮寶齋》雜志執行主編徐鼎一先生介紹,其收藏有《劉文莊公文集》部分手稿本,線裝,紙本墨筆,共52頁,104單頁,收有雜著、考論、跋記、奏牘、詩文共78篇。見其2007年10月24日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0a299f01000b67.html 。劉秉璋尚文好學的性格愛好深刻地影響了其后代,其三子劉體信(聲木)、四子劉體智均是近現代不涉政治的著名學者和藏書家。*詳論參見宋路霞:《細說劉秉璋家族》,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另參見鄭玲:《收藏世家:廬江劉氏的藏弆述略》,《大學圖書情報學刊》2011年第6期。特別是劉秉璋和劉體智兩代人的藏書積累對民國時期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鄭振鐸的藏書活動起到了不可或缺之作用,這正體現了詩書傳家古訓的正確性,尤其在改朝換代社會大變動的背景下。
保存完整的《劉文莊公奏議》沒有直接涉及學術問題,亦看不出明顯的學術思想傾向,而《澹園瑣錄》所述也屬于基本常識,內容淺顯,不屬于學術研究,皆可存而不論。劉秉璋的學術思考可依據《靜軒筆記》加以考察。
二、劉秉璋的學術思考及其特點
《靜軒筆記》劉體智序載,劉秉璋“每日讀書,凡有所見及所經之事,悉錄于日記”,此書即是劉體智從劉秉璋日記中整理成相對系統的文章。《澹園瑣錄》是劉秉璋本人的讀書筆記,而從內容上看,《靜軒筆記》不少內容乃至文字與《澹園瑣錄》大致相同,可見劉體智所整理、編輯的《靜軒筆記》內容即來自《澹園瑣錄》以及其他后來散佚的筆記。劉聲木《萇楚齋隨筆》提及劉秉璋的不少著述,估計也是對《澹園瑣錄》內容的分專題編輯。《澹園瑣錄》的著述目的,據劉秉璋自序,是“為子侄輩饋貧糧”,而劉體智《靜軒筆記》序中也提到此書是因“當時科舉未廢,殆為場屋之用”,顯然,劉體智注意到《澹園瑣錄》這一特定性質。粗看起來,雖經劉體智整理、加工,《靜軒筆記》稍顯專深,不過,仍顯駁雜、淺顯。《靜軒筆記》既非劉秉璋手編,亦非專門學術著述,內容只是劉秉璋日常讀書與思考之隨手所記,且是為子侄輩應考之用,主要是對已有經書和先秦兩漢子史著作研究中有關問題的介紹及其擇善而從乃至解讀、發揮,不過,既然是劉體智刻意選定并芟汰,內容比《澹園瑣錄》專深,具有一定的學術性,我們則可據此考察劉秉璋讀書范圍、學術思考及其特點。
《靜軒筆記》準確刊刻時間、過程尚待考察。據劉體智序是由其于民國初年組織刊印,且《靜軒筆記》的刊印非一氣呵成,而是邊輯邊印。由于劉秉璋原筆記比較復雜,整理時劉體智還“間參己意”,因此“每成一冊,即先付印,不容稍緩”。今存民國刻本《靜軒筆記》卷首目錄標為120卷,實存第1至第4冊共19卷,極有可能是僅印刷4冊后即停止。今臺灣文聽閣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晚清四部叢刊》叢書本即據此重印。
從《靜軒筆記》120卷目錄看,涉及72種典籍,經、史、子、集皆有涉獵,其中論經學著作有54卷(其中小學著述18卷),分別是:《周易》3卷,《尚書》2卷,《毛詩》2卷,《周禮》6卷,《儀禮》6卷,《禮記》4卷,《大戴禮記》2卷,《春秋左傳》4卷,《春秋公羊傳》1卷,《春秋谷梁傳》1卷,《論語》3卷,《孟子》2卷,《大學》《中庸》《孝經》1卷,《說文》6卷,《六書音韻表》5卷,《爾雅》2卷,《小爾雅》1卷,《方言》1卷,《釋名》1卷,《廣雅》1卷;史學著述:《史記》5卷,《前漢書》3卷,《后漢書》1卷,《三國志》1卷,《國語》2卷,《戰國策》3卷,《竹書紀年》1卷,《山海經》1卷,《穆天子傳》1卷,《孔子家語》1卷,《晏子春秋》1卷,《越絕書》1卷,《吳越春秋》1卷,《列女傳》1卷,《新序》《說苑》1卷,合計24卷;子部所論包括《荀子》2卷,《孔叢子》1卷,《新語》1卷,《新書》1卷,《鹽鐵論》1卷,《法言》1卷,《太玄》1卷,《潛夫論》1卷,《申鑒》《中論》1卷,《孫子》《吳子》《司馬法》1卷,《管子》3卷,《慎子》《鄧析子》《商子》1卷,《韓非子》4卷,《墨子》2卷,《尹文子》《尸子》1卷,《鬼谷子》《公孫龍子》1卷,《鹖冠子》1卷,《呂氏春秋》3卷,《淮南子》3卷,《白虎通》1卷,《獨斷》1卷,《論衡》1卷,《風俗通》1卷,《老子》《列子》1卷,《莊子》3卷,合計38卷;集部,論《楚辭》4卷。范圍限定于先秦兩漢文獻,不及兩漢以后著述;數量上論經學著作最多,分量最重,而論集部只討論《楚辭》,不及其他詩文。偏重經史,正是科舉考試的范圍,而不論詩文;偏重思想,正是體現政治家尚用的閱讀特點,不同于一般文人學士之興趣。今存4冊,第1冊討論《周易》3卷,第2冊討論《尚書》2卷、《毛詩》2卷,第3冊討論《周禮》6卷,第4冊討論《儀禮》6卷。以下即以其《詩經》學論述為主、兼顧其他內容論述(《澹園瑣錄》對《詩經》問題也有所涉及,只是更為淺顯),以考察劉秉璋學術思考的主要內容。
劉秉璋論《詩經》(《毛詩》)的內容集中于《靜軒筆記》第2冊第6、7卷,計有57篇。前3篇《詩書之別》、《詩本事》、《詩教》,分別闡釋《詩經》與《尚書》之區別、《詩序》的存廢以及孔、孟詩教觀念三個命題。其后54篇討論《詩經》單篇內容,基本還是立足小學,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解說《詩經》中的字詞內涵、名物禮儀、地理民俗、歷史典故等。
劉秉璋重視《詩經》學史的積累,可見他有一定的知識積累,符合清代科舉應考者的知識結構特點。清代《詩經》研究甚熱,有所謂漢學與宋學之別,而劉秉璋的取舍并不清晰,只不過于宋代學者觀點吸收較多,從以下三端可以見出:
第一,論《詩經》與其他經典異同、《詩》今古文經傳承、《詩經》大小序及其作者等問題,劉秉璋主要參考宋代歐陽修、蘇轍、朱熹等人的觀點。
《靜軒筆記》卷6首篇為《詩書之別》,劉秉璋在此文中將“十三經”分為六大類:《詩》、《書》一類,《論語》、《孟子》、《孝經》一類,《易》一類,“三禮”一類,“春秋三傳”一類,《爾雅》一類。又提出“《詩》、《書》同異之處凡十端”,分別是:“《書》無韻文,《詩》有韻文;《書》紀國政,《詩》觀民風;《書》以成周止,《詩》以成周始;《書》無可紀而后《詩》傳,《詩》亡而后《春秋》作;《書》末附有《費誓》、《泰誓》,《詩》末附有《魯頌》、《商頌》。”此論平平無奇,但它透露了劉秉璋對《詩經》地位的評價,亦即劉秉璋之《詩經》學觀念。“《詩》、《書》為一類”、“《詩》觀民風”、“《書》無可紀而后《詩》傳”,在劉秉璋看來,《詩》、《書》并舉意味著《詩經》地位堪與《尚書》并列,皆屬對周朝社會真實面貌之記錄,非《詩大序》中強調的“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朱熹:《詩序辨說》卷上,《四庫全書》第6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頁。之政治功用。這一觀點與朱熹“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朱熹:《詩集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頁。論斷相似,可視作劉秉璋對朱熹《詩經》學說認可之證。
關于《詩序》存廢之爭的理解。《詩本事》一篇,主要就《詩經》學史上有名的《詩序》存廢之爭抒發己見。北宋歐陽修作《詩本義》,辯正《詩序》中記載失當之處多達114則,否定“子夏作序”一說,認為《序》當出自后人之手。蘇轍采取折衷觀點,未像歐陽修一般全盤推翻,但也否定《詩大序》,只承認系于每篇篇末的《詩小序》之首句是孔子所作,其余內容因申說過于詳細有流于瑣碎之嫌,斷非古人所為:“其誠出于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蘇轍:《蘇氏詩集傳》卷1,《四庫全書》第70冊,第315頁。二程針鋒相對,雖然認同孔子的《詩大序》作者身份,但又認定《詩小序》應是史官的作品,學《詩》必先從學《序》起:“問《詩》如何求?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圣人作此以教學者。后人往往不知是圣人作,自仲尼后更無人理會得”*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18,《四庫全書》第698冊,第184頁。;“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程頤:《程氏經說》卷3,《四庫全書》第183冊,第62頁。到南宋,朱熹通過《詩集傳》,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詩經》解釋學體系,他除批評鄭玄“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朱熹:《詩序辨說》卷上,《四庫全書》第6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0頁。的解讀方式外,還徹底否定《詩序》,進而立足《毛詩》本身重新闡發詩旨。劉秉璋稱其“學宗二程子,《詩序》獨不然”。劉秉璋對這樁公案的評判更接近蘇轍的觀點。他認為“《序》首句實與《詩》偕作”,首先肯定蘇轍《詩小序》首句可存的觀點,他的證據有二:一是“《南陔》六詩有義無辭,詩亡,序存”,二是“三十一章大致皆與《毛詩》相類,而但有首句是‘三家詩’遺說不同,而首句之序則一”。若想求得《詩》之本來面貌,僅僅依靠《詩小序》不夠,還要“參之以《尚書》、《左傳》暨古傳記、周秦諸子所述”。這段論述,不盲信古人,不拘泥一家,雖其證明過程難說無懈可擊(亦受筆記體裁因素影響),但治學態度卻堪稱嚴謹。在《澹園瑣錄》第9冊《詩經》篇里,劉秉璋還提到了有些學者認為《詩小序》的作者是衛宏的觀點(此說源出《后漢書·儒林列傳》),但只陳述卻不下斷語,態度曖昧,可視為不棄不取。同時,批評朱熹將《序》全盤推翻的做法,直言“駁之過甚”。《澹園瑣錄》第九冊討論《詩經》,主要是借助前人論述辨析、梳理《詩經》先秦傳承問題以及大、小序作者問題,沒有闡發新見。關于《詩序》存廢問題,劉秉璋旗幟鮮明主張存《詩小序》。
第二,關于傳世《詩經》收詩范圍的認識,也近于宋學。
劉秉璋推崇孔子“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2、208頁。以及《詩》可以“興觀群怨”?”*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52、208頁。的觀點,仍有意拉開《詩經》與政治之間距離。在其看來,所謂“教”即教化,從大處講是教化萬民,從小處講乃人的自我教育,故而《詩經》“涵泳性情,千古不易之理也”。孟子論《詩經》:“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楊伯峻:《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215頁。南宋王應麟有“學《詩》必自孟子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3,《四庫全書》第854冊,第208頁。的感嘆,劉秉璋極為認同,贊美曰“誠哉是言也”。論《溱洧》主旨:“《溱洧》二章描寫男女之情,各盡其致,六朝‘子夜之歌’、唐人‘香奩之集’,于此開其先。”可見,劉秉璋治《詩經》主張就詩論詩,從詩歌本身出發,以文本為本位加以理解,強調《詩經》的情感成分與教化作用,反對過分解讀《詩經》的主旨思想,尤其是夸大《詩經》的政治功能。
第三,劉秉璋論《詩經》學,在方法上重視金石考據與書面文獻的互證、互補關系,亦是繼承宋儒學術傳統。
宋代歐陽修撰《集古錄》,有意識地利用金石原物、拓片作為經學研究的佐證,開金石考據之先聲,后經好友劉敞等人踐行鼓呼,逐漸蔚為大觀,如清郭嵩燾所言:“宋儒考古之勤,信非唐賢所能及也。”*郭嵩燾:《養知書屋詩文集》卷1,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正編)》第16輯,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46頁。清道光年間西周虢季子白盤的出土面世轟動一時,因銘文字詞、句式、史實不乏與《詩經》相類甚至重合之處,有人將其視為《詩經》之補充材料。巧合的是,到了清末,淮軍另一位將領劉銘傳收藏了虢季子白盤,劉秉璋極有可能親見了這份珍貴的文物,他在《詩本事》中稱“詩之原文傳世可供參考者,惟虢季子白盤”,肯定了虢季子白盤銘文對解讀《詩經》原文的重要參考價值。
重視金石考據與書面文獻的互證、互補,這在劉秉璋的“三禮”研究中也有實踐。今存《靜軒筆記》述《周禮》和《儀禮》的各6卷(第8—13卷和第14—19卷)內容里,器文互證、以器釋文者近30處。典型的如:
鄭注:敦盤類,珠玉以為飾。按:傳世銅器敦盤甚多,敦為盛谷食器,盤為承物器,合乎古訓。敦非盤類也。近年玉器出土亦有敦盤之屬,較銅器為小,其為盟會盛牛耳盛血之備,不作他用,明矣。(《靜軒筆記》卷8《珠盤玉敦》)
鄭注: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鄭于鄉射《禮注》云:決,猶闿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闿體也。按:近人金壇段氏、績溪胡氏僉謂決如今之扳指,皆似是而非。決以象骨為之,驗諸古時器物品質,有用象則必有用玉者。今出土玉中有形似扳指而一面高幾及寸一面高不及一寸五分之一者,以之鉤弦良為適用,殆即此物無疑。(《靜軒筆記》卷10《決拾》)
铏即出土之齊侯罍,或曰齊侯壺者是也。本是菜和羹之器,后人誤為酒器,遂生異議。(《靜軒筆記》卷17《铏》)
然而,盡管劉秉璋吸收了宋學《詩經》學的成果,但是,我們又很難將其劃入宋學的陣營里,換言之,漢學傳統在其研究思考中也有明顯表現。
《靜軒筆記》專論《毛詩》的57篇文章里,專門闡發劉秉璋《詩經》學觀點或者發揮詩旨的內容甚少,絕大部分內容都屬于考據的范圍,對《詩經》所蘊含的“微言大義”幾乎沒有發揮,看不出他與晚清今文經學的聯系。清代考據方法相較前代愈加精良,例如桐城學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常常利用古音古義或是雙聲疊韻的原理來訂正前人注疏中的訛誤,這些方法也在劉秉璋的考據中有所反映,劉秉璋有時是直接引用其說法。如,釋《詩經·陳風·月出》:
“舒窈糾兮”,《傳》:“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瑞辰按:“窈糾”猶“窈窕”,皆疊韻,與下“憂受”、“夭紹”同為形容美好之詞,非舒遲之義。(《毛詩傳箋通釋》卷13《月出》)*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17頁。
《毛傳》:“‘窈糾’,舒之姿。”按毛說是也。此類雙聲疊韻形況字,古文無一定意義,觀其用處而已。言女子則用“嬌嬈”,《漢樂府》之“嬌嬈”即《關雎》之“窈窕”也。(《靜軒筆記》卷7《窈糾憂受夭紹》)
馬瑞辰(1777—1853年),桐城人,其著《毛詩傳箋通釋》被視為桐城學術的重要著作,“熟于漢學之門戶,而不囿于漢學之藩籬。”馬瑞辰對出生于與桐城交界的廬江劉秉璋而言屬于鄉黨,劉秉璋多所引用,自是理之必然。此外,劉秉璋釋《周易》、《尚書》、“三禮”,亦綜合采用了古音、古字、通假、雙聲疊韻等多種考據方法:
仁者,人也,取愛之意。從二,從人,則博愛之道也。義者,利也,取利己意。以利為訓,蓋人情趨利避害亦無有不宜焉。古韻義利同音同字。利,和也,亦同韻通用。而臺予余蓋別體也,《易》彖辭中之“元亨利貞”,《彖》傳輒言大亨以正以利通用,而又與我字義字同訓,以字殆即臺字,于此益見古義利二字不分。(《靜軒筆記》卷2《利》)
《注》引鄭司農云:菑讀為不菑畬之菑,栗讀為榛栗之栗。玄謂栗讀為裂繻之裂。按:菑斯聲近,菑栗即撕裂之古字。(《靜軒筆記》卷13《菑栗》)
執假借作謺,《說文》“謺”下云“讘也”,“讘”下云“多言也”,謂鄰國獵取鳥獸便于多言以致討有詞可措,不患無名矣。(《靜軒筆記》卷2《六五田有禽利執言》)
“契”與“怯”同韻,與“需”雙聲,以狀馬行之不倦,古文中形況字也。《詩·鄴風》之《北風》章,其虛其邪,當如是解。若求其字,反失之矣。(《靜軒筆記》卷13《契需》)
劉秉璋《詩經》學考據之范圍,雖以字詞、篇名、主旨為重點(比例約占62%),但并不單單局限于此,還包括禮儀、典制、職官(13%)、名物(11%)、地理(9%)、歷史(5%)等諸多方面,這一點不似馬瑞辰,卻有焦循之風。
顯然,劉秉璋的研究、思考,無涉于漢、宋以及今、古文經學之辯,貌似融通,個人見解不多,其實是其非嚴格學者的表現。這種非專業性還可以從以下兩方面看出來:
第一,劉秉璋治《詩經》不像一般學者那樣追求嚴格的系統性,未采用通行的逐篇逐句釋法,而是隨機選取感興趣的內容加以闡述,篇目主要集中在“風”、“雅”兩部分。涉及《國風》數量最多,有34篇,其次是“雅”17篇(包含《小雅》12篇、《大雅》5篇),“頌”數量最少,僅有4篇,三者在各自整體中所占比例分別為21%、16%和10%,看不出系統性。《國風》中,與《周南》、《召南》有關的篇目數量相對而言更占優勢,比例超過四分之一。可見劉秉璋的《詩經》學趣味比較集中,他不太關注內容更為莊重嚴肅的“雅”、“頌”,而更關注《詩經》中反映西周社會風土人情、內容比較具有民間性的《國風》部分。
第二,《靜軒筆記》引用材料來源較為集中,均以阮元所刊刻的“十三經注疏”本為底本,對版本異文不甚關注;在觀點上兼取前人學說,辨析前說失當之處,所做學術史引用并不全面,有時甚至以個人日常生活感受代替征引文獻的嚴肅、深入考證。《周易》部分引用多出自《困學紀聞》、《周易集解》,《詩經》部分引用來源集中在《說文解字》、《玉篇》、《左傳》、《禮記》、《經傳釋詞》等等。但《周禮》、《儀禮》部分是個例外。清代禮學研究的重要轉折——從推崇敖氏(繼公)到回歸鄭玄,這種學術風氣變化在《靜軒筆記》中的最典型之反映恰在其征引來源的選擇性。劉秉璋不但將鄭注作為研究之底本,而且征引了鄭注推崇者吳廷華(《儀禮章句》)、胡培翚(《儀禮正義》)、黃以周(《禮書通故》)等人的觀點。相比之下,對敖繼公《儀禮集說》一書內容的引用次數明顯要少得多,而且每次出現必伴隨著批評。但需強調的是,對鄭注的認可并不意味著全盤接受無所甄別,劉秉璋對鄭玄及其追隨者觀點的廣泛征引,其前提是對鄭注失誤的體察與糾正:
《天官》之九嬪、世婦、女御數闕,《春官》之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為下文之內宗,即閽人職之內命婦是也。外宗即外命婦是也。內命婦,王后宮官也;外命婦,卿、大夫、士之妻也。九嬪比于天子之三公六卿世婦;每宮卿二人,王后六宮,共十二人,比于天子之小宰、小司徒等十二小卿。內外宗隸于大宗伯之下。《白虎通義》:宗者,尊也。鄭注以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以宗為祖宗之宗,失之。(《靜軒筆記》卷10《內宗外宗》)
鄭注“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于郊”,《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鄭于《月令》注引“司馬職,羅弊致禽以祀祊”。賈疏證彼“祭禽于四郊”與此“馌獸于郊”為一物,其實彼一解以為是仲秋祭禽,以祀祊為一也。按:鄭注此書引《月令》以證為冬狩,“祭四方神”其注《月令》又引此書以證為秋狝祀祊,未免互相矛盾,賈疏糾正是也。拘于鄭學者,雖單詞片義之偶誤,必為之掩飾,彌加尊重。此則兩處互相矛盾無可掩飾者,特表而出之,以見千慮容有一失,未可株守一家之說也。(《靜軒筆記》卷11《致禽狝獸于郊》)
劉秉璋研究思考靈活、通達,往往不做繁瑣考錄,而揆以人之常情進行解釋:
“江汜”、“江渚”必有其地,不必拘于一處,其義乃通。(《靜軒筆記》卷6《戊申戊甫戊許》)
文人之筆,一時興到,何必實有其人,抑何須親其事?(《靜軒筆記》卷6《溱洧》)
其實偏旁同異,無關宏旨,亦不必深考也。(《靜軒筆記》卷7《況瘁》)
九谷之屬,應有盡有,如謂今之所謂黍、稷、粟者,非古之黍、稷、粟,而別求其物以實之,則非所敢知矣。(《靜軒筆記》卷8《九谷》)
總體看來,劉秉璋對《詩經》暨經典文獻的論述,大多著眼于已有爭論或問題,其觀點基本上是從前人所論中擇善而從,論題和考證并不系統、深入,即使稍加辨析,也多是從普通讀者的角度出發對歷史上的公案做出符合日常生活經驗的簡單判斷,沒有特別深刻的見解;所引證文字中,不少沒有標明出處或作者,往往斷章取義,并不是嚴格規范的學術方式;觀點與方法兼采漢、宋,不拘今、古,未有明確的門戶歸依、學說宗仰的傾向,和清代漢學家、今文經學家以及治宋學者強調學有所出、門派歸屬顯然不同。
此書的內容只是劉秉璋為教育子侄應考而作的常識介紹,其性質雖然決定了內容不能太專深,此書自然并不能全面反映劉秉璋的學術思考,不過,從一般意義上,我們仍然可以論定,《靜軒筆記》反映了劉秉璋學術的基本狀況和水準:《靜軒筆記》內容駁雜,基本上是抄檢前人舊說,缺少創見,表明劉秉璋學術水平不高,不是專業的學者,沒有入流于當時學術圈子。
三、劉秉璋與清末社會文化之流變、分野
進士出身的劉秉璋沒有成為學者,談不上學術成就,亦不是著名詩人(流傳下來的詩歌只有數首)、散文家,原因是他生活在清末亂世,身為朝廷倚重的國之棟梁,主要精力并不在治學,學問只是他的閑暇愛好而已。盡管如此,其學術思考中也有一些新的因素乃至特點,尤其是所折射出清末學術發展的態勢以及所屬軍政集團的特點,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一) 學術思潮的分合與起伏
處于封建末世的晚清是各方思想碰撞、社會激烈變革的時期,作為社會鏈條中必不可少的一環,晚清學術自然無法屏居于時代浪潮之外。就劉秉璋學術活動對清末學術演進形態的反映而言,有如下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漢、宋合流。道咸以來,中國傳統學術日趨精良完備開始自我整合與更新:盛極一時的乾嘉漢、宋之爭漸趨消歇,漢學如日中天,以壓倒性姿態取得勝利,考據學“幾成為清代學術的代名詞”*張立文主編,陳其泰、李廷勇著:《中國學術通史(清代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頁。;宋學雖退居其次,然亦未至絕境,賴有倭仁、吳廷棟、羅澤南等人延續學脈;而今文經學在龔自珍、魏源、廖平、康有為等人的手中臻于繁盛。與此同時,多方又明顯呈現出兼采乃至融合的傾向,這一點在重臣曾國藩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詳論參見武道房:《曾國藩學術傳論》,安徽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他主張:“于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致劉蓉》,《曾國藩全集·書信(一)》,岳麓書社1995年版,第168頁。作為深受曾國藩器重的劉秉璋,在學術取向上兼容漢、宋,并非偶然。當然,劉秉璋對今文經學不太關注,這是他和晚清激進的改革派不同之處。
二是西學東漸。伴隨著鴉片戰爭后的國門漸開,來自西方的新學大興,介紹外國政史地科的著作紛紛出版,進化論、新史學先后登上學術舞臺,在“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點的指導下,學術命題、治學方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變革。身處于東西古今交匯點并且直接與洋人打交道的劉秉璋,面對新學與舊學的“兩面夾擊”,他的選擇與態度頗值得玩味,或許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代表晚近普通知識分子群體中守舊一派的觀念與立場。其著述中涉及西方文化、政治、法律乃至舞蹈藝術之議論俯拾即是,如:
歐洲人崇拜英雄,于其本國開創之事尤樂道之。英國大王阿爾夫內得兵敗匿于鄉間,為村婦炊餅,不熟,大受呵責。適軍報至,敵眾大敗,迎歸故都。村婦知為王,自謝乞宥。大王笑曰:“不意壞爾餅,汝亦宥我。”無論史書說部均艷稱之,究竟有無其事不可知,彼時英猶土著,王室族類究竟已否融入條頓血液亦不可知。顧以為國情切重之如此,吾人在先閉關自守,知有己國而已,更無有他國,以與之比,遂不知如何。而始為國猶之乎人居其鄉,則人人皆同鄉,不知如何而顧全鄉誼也。通商以來,相形之下,宜漸有國家思想矣,執干戈,衛社稷,非人人之所能試也,非時時之所能有也。若愛護古跡,則人人能為,隨時所有,姑以此始焉。免疲精神于無用之地,是所望于今之君子耳。(《靜軒筆記》卷4《讀書不可以文法斷定時代》)
歐美各國聽訟之法,先使以口親耶穌而后出言,以明勿欺,猶存古意。(《靜軒筆記》卷12《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西人跳舞中有所謂“狐步”者,庶乎恰合。(《靜軒筆記》卷15《以貍步》)
劉秉璋在其《詩經》學研究中,《朝陽夕陽》一文爬梳“夕”字的字義演化過程,文末指出“宋人解經,尚在萌芽,非其學之淺也,時代進化尚未至也”,已自覺運用時代進化之觀點;《鼒》提到“歐人以掘地考古之學信為有益,但不可束書不觀耳”,雖然對西方考古學的認識過于簡單幼稚,但還是承認考古學在歷史考證中的作用,更難得的是有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方法意識,盡管相比而言在他心目中還是世間已流傳了千百年的書籍更值得信賴。由此可見,劉秉璋視野之開闊,對西方文化了解之漸趨深入、通達。
(二)淮軍與湘軍、淮軍與桐城派的精神疏離
曾國藩率領其建立的湘軍集團成功鎮壓太平天國起義,使本來危在旦夕的滿清政權暫時渡過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不過,內外夾擊之下,從此大清王朝的政治文化生態也逐漸發生改變,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端就是曾國藩對理學和桐城派散文的自覺倡導,在散文創作上出現湘鄉派以及“曾門四大弟子”。在曾國藩及其湘軍退出政治舞臺之后,曾國藩一手栽培的學生且在桐城派故里——桐城以及江淮間成長起來的李鴻章及其淮軍,縱橫晚清政壇近四十年,雖然在軍事、外交、實業等領域除舊布新,功勛卓著,影響深遠,在思想和散文創作上卻竟然沒有傳承老師曾國藩的衣缽。李鴻章和“曾門四大弟子”之一、皖籍同鄉吳汝綸,一開始共同師事曾國藩,后來吳汝綸還長期在李鴻章幕府擔任幕僚,為李鴻章掌機要文翰,二人交往密切,可是,從現存李鴻章與吳汝綸文集中卻看不到二人切磋論文的情況。試想,以李鴻章當時之身份和影響力,如果他介入思想和文化領域,晚清的歷史包括文化和文學史乃至近代史則要完全重新書寫。
對上述現象及問題,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和解釋,最值得注意的是王爾敏先生的研究和分析。王爾敏先生通過大量人員數據分析指出,“淮軍中大軍旅之統將二十六人中有科名者五人、捐職一人,與湘軍領袖多數均有科名不同”*王爾敏:《淮軍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6、285、321頁。,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李鴻章“所注重的幕才,多為通達治體了解洋務的人物和廉正精明的循吏,著重于經世致用。凡有謀略而干練,必受到賞識擢拔。文章道德,尚在其次。是以淮軍軍幕并不護持文人,維系文風。與湘軍幕府相較,自大為遜色。鴻章出身幕僚,并以曾國藩傳人自居,而于幕府規模,則稍不盡師承。此一分歧,亦足顯示兩人政治作風之不同”。*王爾敏:《淮軍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6、285、321頁。正因為文化層次高低不同,“以政治地位而論,僅湘籍分子,任督撫者已二十四人。并時地方權位之盛,無與倫匹。淮軍次于湘軍,戰役則并未參與西北西南。人才則李鴻章之外,重要領袖亦不過十人。政治地位,只有李鴻章一人權勢煊赫。其余任督撫者不過四人,即加上外籍幕府人物,亦不過十余人。”*王爾敏:《淮軍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166、285、321頁。王先生通過大量的統計分析發現,湘軍和淮軍主要人員身份存在明顯差異,一為科舉人物,一為沒有科名的農民、行伍、世職、軍功等,文化程度差異明顯。曾國藩治軍強調價值觀之引導,尤重理學之作用。李鴻章生活的社會環境已不同于曾國藩,曾國藩面對的還主要是國內的太平天國起義,而李鴻章面對的主要來自外來勢力,他看到的是傳統思想的有限性,更關注學習外來先進技術,所以,他不太注重文化建設、學術研究以及文學活動。劉秉璋與潘鼎新進京參加會試即拜李鴻章為師,和李鴻章有師生之誼,進入淮軍也是李鴻章親自奏請朝廷任命之結果,后來在跟隨李鴻章平捻過程中與李鴻章以及淮軍諸將不合,曾于同治八年滅東捻后以父病乞歸隱退。雖然劉、李起初關系密切,劉秉璋也始終受到李鴻章的重用,但是,劉秉璋似乎更受曾國藩賞識,幾乎引為己用,原因就在于劉秉璋的進士身份及他們對文化學術有共同的愛好,志趣相投。
我們循著王爾敏先生的思路進一步觀察,淮軍核心骨干多來自合肥、廬江、舒城、巢縣*根據《淮軍志》“淮軍統將表”統計,432人中,主要是合肥、廬江人,附近的巢縣、舒城也有一些,而安慶地區不多,其中桐城5人(包括周壽昌、程學啟)、懷寧2人、潛山1人、太湖1人。,而桐城派的主要人物所分布的桐城、懷寧、潛山、太湖等地,雖都屬安徽,但二者并不重合。盡管皖、湘之別遠大于合肥、桐城之別,但是,在文化趣味方面,湖湘更接近于桐城。以曾國藩為首的湖湘政治軍事文化群體更自覺地傳承了湖湘區域興盛的理學傳統,同時,桐城派的精神亦符合他的興趣。姚鼐所創建的桐城派,雖標榜“義理考據辭章”兼顧,其實,在乾嘉漢學盛行之時,其批判漢學、捍衛理學的現實性是明顯的,比如方東樹《漢學商兌》,因此,曾國藩繼承桐城派衣缽正是理所必然。劉秉璋雖然文化氣質接近曾國藩,但是,畢竟長期在重視事功的李鴻章集團內活動,他也就沒有進一步像曾國藩那樣偏好理學,也沒像曾國藩那樣熏染桐城派精神氣質和習慣。
綜上所論,劉秉璋的學術活動沒有進入晚清主流學術圈子,而劉秉璋一生的宦途起伏是李鴻章領導的、縱橫晚清政壇逾四十年的淮軍由盛轉衰的縮影。在科舉考試出身主導的清代政壇,偌大的淮軍中像劉秉璋這樣有知識、有文化的骨干居然只是鳳毛麟角,這是一個極為反常的現象。李鴻章重實用謀略,輕視文才,反映了晚清內外交困的時代環境下實用主義思潮的盛行。李鴻章甫一去世,梁啟超《李鴻章傳》即做出了精確的評論:“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明確指出李鴻章識力之不足,影響了其對大勢的判斷,而識力顯然主要來自學術思考與學術積累。輕視科舉為國擢拔棟梁之才重要作用,輕視傳統道德文章,忽視洞察世事的學術文化,無疑嚴重限制了淮軍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并對淮軍乃至晚清最終命運產生了難以忽視的負面影響。李鴻章同時代的張之洞,在事功方面雖然不及李鴻章,但是,他崇尚文教,所提出的“中體西用”之思想方案雖不能紓解當時清廷之困,不過,百年之后在中西文化關系依然待解的今天仍具有重要參考價值。時間充分證明,張之洞好學尚文之高瞻遠矚不能不令人佩服,同時,我們將比梁啟超更加遺憾地“惜李鴻章之識”!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清代文人事跡編年匯考”(13&ZD117)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