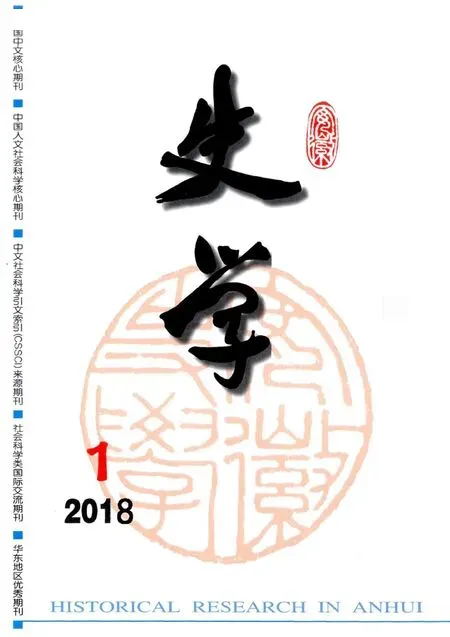李鴻章集外文再補
李永泉
(哈爾濱師范大學 文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晚清重臣李鴻章是影響中國近代歷史的關鍵人物之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顧廷龍、戴逸先生擔任主編的新編《李鴻章全集》,規模宏大、收集完備。雖然如此,亦難免有遺漏,學界陸續有輯佚文章刊出*如張曉《李鴻章對西方近代科學的認識》(《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12期)一文發掘出《李鴻章全集》集外文5篇。徐世中又撰《〈李鴻章全集〉漏收文稿一篇及其文獻價值》(《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13年第6期)、《李鴻章集外文考論》(《安徽史學》2015年第2期)兩文,共挖掘出集外文8篇。,筆者前亦曾輯李鴻章集外文6篇*李永泉:《李鴻章集外文補遺》,《安徽史學》2016年第2期。,今復輯得集外文9篇,特為迻錄,以供相關研究參考。
重修武帝廟碑記*漳鄉位于湖北省當陽縣東北漳水邊上。漢末,關羽被擒殺于此。同治七年重修關帝廟,次年四月告竣。時李鴻章在湖廣總督任上,應所請作此文以記之。
當陽縣之漳鄉,故武帝陵寢在焉。而建廟則始前明成化,入國朝凡再修之,隆規宏基,視他郡邑為最。閱歲既久,舊觀闕如,所司文武吏大懼無以肅成祀典,請加營葺,飭材鳩工,乃備乃固。經始于同治七年八月,畢工于八年四月。鴻章適奉命督軍于楚,所司告成,爰以記請。
竊惟武帝浩然剛大之氣充塞宇宙,其結聚于萬世人心者深固,而光昭國家,崇德報功,肇晉秩祀,與天無極。神明精爽,春秋奔走,將事不戒而虔舉天下,胥同一軌矣。而衣冠出游之地,昭假上下,凜凜乎如在如存,茍周旋承奉有未至焉,匪特愴斯民追慕之誠,曷以征圣代秩宗典禮之隆盛哉?疆理所職,其敬勉之而已。
用書緣起,以告來者。至監理之官,出訥之數,例得附書,具列碑陰,俾后世克考。*李元才修,李葆貞等纂:《當陽縣補續志》卷4《藝文》,光緒十五年鉛印本。
續天津縣志序*《續天津縣志》是清退職在籍道員吳惠元以蔣玉虹私輯的縣志遺稿為基礎,倉猝編纂而成,并請李鴻章為此序。
同治九年,予以湖廣總督奉命督師,剿逆回于陜西。至秦數月,天子以天津邊海重地,番舶往來,華洋雜處,為畿輔守御之要害,非文武重臣不足以勝任。時大學士直隸總督曾公移督兩江,遂命鴻章來津受代,裁三口通商大臣歸并總督,特授為欽差大臣,駐節天津,兢兢焉以招攜懷遠,尊主庇民為要。既蒞任,逾月,邑人吳觀察惠元以其所修《續天津縣志》來質,且請序。
予惟天津去京師二百余里,實畿南之屏蔽也。其地勢下,在古為九河尾閭,凡西北大川咸匯此入海。近者,海運歲行,通商事起,南北中外商賈輻輳,故尤號為難治。顧其人情風俗,輕生赴斗,猶有漁陽、上谷之遺。往歲咸豐癸丑秋,粵逆北竄至城西,知縣謝忠愍公子澄,親率津民劉繼德等數千人大敗之,斬其渠,京畿得無恐。其后捻逆屢犯,津民應募者皆奮起而擊退之,故他郡縣被殘,而天津完善無恙。庚申秋,海疆不靖,時石侍郎贊清守天津,獨抗節不撓,居民千百人衛之,轉危為安。蓋其民之富者多好倡為善義行,其貧者就死不悔,得良吏鎮撫之,則皆能親上死長,勇于赴難而不屈,習使然也。其士大夫仕于他省者,亦多忠義才杰之倫。
往者予奉命團練于鄉,時津人金剛愍公光筯牧壽州,繼守廬州,備兵廬、鳳、潁、六、和、泗,以善擊賊名,忠勇武略為江南北之冠。今考邑志,自昔義烈如金公者固多有之。然則津民之知大義,能為國效力、捍災御患者,豈非官斯土者及其鄉之賢士大夫有以振作于上而致然與?邑志始修于乾隆四年,迨嘉慶間,邑士蔣君玉虹博采旁搜,為續志未成而卒,今吳君復網羅散失,以續成之,體例與凡為志者同,而獨于海道、水利、營田及凡義舉之規條,皆詳載之以為后法,誠善本也。
夫民無常行,惟上所導。率之以好利,則為暴者多;率之以好善,則趨義者眾。是則官茲土者與其鄉公卿大夫皆與有責也夫!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加騎都尉世職合肥李鴻章序。*吳惠元總修:《續天津縣志》,同治九年刻本。
荊州萬城堤志序*倪文蔚,字豹岑,安徽望江人。咸豐二年(1852年)進士,同治十一年(1872年)授湖北荊州知府。在任八年,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輯成《荊州萬城堤志》,是有關荊江大堤的第一部志書。書成,將凡例、目錄寄李鴻章求序,李為作此序。
荊州知府倪君豹岑為《萬城堤志》成,郵致其凡例、目錄,征序于余。志分卷十二,分目三十六。凡述修防之義甚晰,而其所甄采故牘、遺籍,亦廣博以嚴。江自發源西南徼外,由滇入蜀,盤曲六七千里,以與岷江合之,千數百里而出峽。其始束于群山之中,源長流鋪,郁怒無所渫。既出峽,則奔騰橫嚙,甚則逾防稽陲,平野為壑。故湖北濱江郡縣往往多水患,而荊州尤當其沖。自東晉陳遵創建金堤,迄今不廢。我朝乾隆戊申之役,特出重臣,蠲巨帑,增筑石磯。厥后累歲崇修,水患亦以稍弭。夫荊之病澇久矣,而堤之利民亦博矣。
同治己巳,余于楚督任內,持節赴蜀,曾兩過堤上,詳察形勢。審其要術,大抵課工欲堅,籌費欲寬,官事欲核,防護欲勤。得此數者,則災之大者可以減,小者可以消,固人定勝天之理也。君與余相知也久,為人篤雅,劬于著述,尤究心經世之學。守荊州政簡民樂,乃以其暇纂輯是書,于二千年來設堤御水之成績,犁然畢具。務俾有志之士考鏡得失,一旦躬臨巨役,不至以吏為師。后之官斯土者,庶其有所折衷,亦君永庇荊民之一端已。光緒二年正月中澣,合肥李鴻章敘。*倪文蔚纂:《荊州萬城堤志》,光緒二年刻本。
光緒順天府志序*《光緒順天府志》之纂修,緣起于直隸總督李鴻章重修《畿輔通志》時,調取各府州縣志書,獨缺《順天府志》。因而于光緒三年(1877年)商議修纂,至光緒十一年修成,時任順天府尹沈秉成請李鴻章為此序。
光緒十一年,《順天府志》成,府尹沈君書來問序。我朝因明制,順天為京師,而直隸專置總督,則兩漢司隸校尉部三輔河南、唐京畿采訪使領京兆之遺制也,鴻章其敢辭。(謹按:周小史掌邦國之志,鄭司農謂為周志,外史掌四方之志,鄭注謂若晉之乘、魯之春秋,王朝之志先于列國,舊矣。)前代志順天者,僅有謝杰、沈應文之書,草創荒略。皇朝宅京垂三百年,文軌大同,天下郡縣皆有志,而京府尚闕,非所以昭首善也。
今湖北巡撫彭侍郎為尹時,與兼尹德化萬尚書始議創修。侍郎遷去,今通政使周君蒞任,與尚書及鴻章奏明開局,凡八年而書成。一代之舊式,四方之和會,可得而述也。勃碣之間,古為都會;至遼、金而后,正帝王之名;至元、明而后,成一統之志。元有天下之日淺,明則京師已為近邊,故論都者以為有堂皇而無室奧。洪惟我大清之受命也,積功累仁,綿歷奕世,乃光宅乎中夏,遷岐豳作豐鎬,開國之遠,同符于成周。內外蒙古世為臣仆,兩藏通,新疆平,曩代都護、校尉所治,一齊以法,如郡縣吏。幅員之長,過于建元、開元。昔之論形勢者,以河洛為天下之中,今則當以京師為天下之中。
北度大漠,南絕大海,東起龍興之舊都,下臨遼沈而撫屬國,西開玉門、陽關,直達于天山,遠數萬里,近數千里,四維雄張,以環擁京師。京師當南北之中,而近于東。《易·系辭》:“帝出乎震。”太史公《封禪書》:“東方神明之舍。”而中國之山川,皆自西而東,猶朝宗而拱極也。往者多疑四海之說,今則環地數大洲,漢、唐、元所未到者,輶軒之使,冠帶之倫,出自闕廷,如履門閾。而環列大小十數國,或自達,或附屬,皆能通名于上都,以為中國天子之居,仙宸帝所,以必得至為榮異,所謂聲教訖于四海也,所謂天覆地載,莫不尊親也。偉矣哉!三代以來,未有開辟廣遠如斯之盛者也。
若夫考其封域,則《禹貢》冀州之都,而在昔軒轅氏之所宅也。文謨武烈,神圣繼承,制度典則,燦然大備,則《周官》《王制》之精意也。著臺省之故事,采閭里之風俗,則《立政》之篇,二南之詩,固非衛宏《舊儀》、趙岐《決錄》所得而擬也。紫宮朱堂,鈞臺靈囿,神明之觀,事實乎上林,名正乎甘泉,則《三輔黃圖》《洛陽宮殿簿》諸書無所侈其靡麗也。至于問山川之形勝,究土地之所宜,松亭之關,軍都之塞,昔之邊防,久為內地,而水利營田,轉漕海運,磊落數大事昭明乎簡冊,則近代二顧之書,所為紀險要而極利病者,由今觀之,皆陳跡也。
昔之志京府者,獨推有宋乾、咸二志,南渡偏隅,周權具臣,豈若今日際殷武之中興,大堯典之四宅,卿尹登揚,以佐揆文奮武之治!侍郎方帥鄂,為時重臣,通政之為尹也,百廢具舉,比跡于趙張。今沈尹又以特召入尹,而兼總理衙門大臣,于近今為要任,聲施之耀,正未有期。鴻章久忝畿輔,頃監修《通志》畢,復喜見斯志之成,因為述其緣起。至其體例之善,文采之美,則九能三長,授簡綴辭,極天下之選,以成一代之書,信今傳后無疑也。光緒十一年七月,合肥李鴻章。*周家楣修,張之洞、繆荃孫等纂:《光緒順天府志》,光緒十二年刻本。
說文段注訂補序*王紹蘭(1760—1835年),浙江肅山縣人,字畹馨,號南陔,晚年自號思惟居士。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進士,官至福建巡撫。著述甚富,事具《清史稿》卷359。其《說文段注訂補》著于嘉慶時,世不之知,光緒十四年胡燏棻始求得刻之,并請李鴻章為此序。
乾隆以來,為《說文》之學者,推金壇段氏最為顓家。其書主獨斷,有李斯盡罷不同秦文,別黑白以定一尊之意。書成之后,攻者數起。譬之用兵,部分既廣,則虛實不齊;譬之議法,主持太過,則激而思反。入室之戈,亦自召也。往見吳縣馮中允《段注說文考正》,嘆其持論平實,不茍異同,得古人隱略,則表明不同,即議別之旨,異于鈕、徐諸家之昌言排擊者。泗州胡云楣觀察先本蕭山人,得其鄉先達王中丞《說文段注訂補》,刊既成,吳縣潘尚書既序之矣,復來請序,受而盡讀之,有訂有補,體例略同中允書,而所糾正則視鈕、徐為更暢矣。
其證據精確者。如據《公羊傳》,知“例”字不始于當陽;據劉向賦,知“佋”字非造于典午;據《韓子·解老篇》,知體分十三屬之定名;據《春秋繁露》,知“”為水音之正字。泰山之臨樂,是山而非縣,不應執《漢志》之衍文;馮翊之洛,是雍而非冀,不應創許例之曲說。知《漢書》表、志、侯國各異之例,則邛成非泲陰之縣,可辟舊說或有改屬之謬;知崇賢選注援引之疏,則元服之“袗”不應作“袀”,可釋近人校議之惑。汳水義主反入,不應改“至蒙為雝水”之“雝”為“獲”,則持邵氏《爾雅正義》之平;泗水本過臨淮,不應改“卞下過郡三”之“三”為“二”,兼可正錢氏《新斠》注《地理志》之誤。凡所抉摘,并極詳審。
中丞撫閩,以治李藩使獄去官。是獄主之者,實桐城汪制府。制府鄉人姚臬使則稱制府不禮于閩士,是獄起,遂有聯名建祠之舉。今觀左海、茝林之所言,皆歸獄制府,而于中丞有恕詞,知姚言為不誣。李固嘉定錢詹事入室弟子,按是獄者高郵王文簡,陰成是獄者金匱孫文靖。三公同州部,又皆小學家也,而中丞竟坐是累不復出矣。書中多引同時人所著書,而屢稱王伯申說,其宅心和厚,異于大儒戴圣毀何武者。曩在江南,監刻《段氏說文注》成,將并刊《考正》,而中允力辭,故海內通人如潘尚書及南皮張制府皆未見也。中丞此書,晦將百年,得云楣之力以傳。云楣吏治、經術卓然有聲,鄉黨后進有賢達人,是可貴也。光緒十四年十有二月,合肥李鴻章序。*王紹蘭:《說文段注訂補》,光緒十四年胡燏棻刻本。
澄懷園文存序*張廷玉,字衡臣,號硯齋,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大學士張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其六世孫紹文、紹華復刻張廷玉《澄懷園文存》,并請李鴻章為此序。
桐城張文和公以碩學巨材,歷事三朝,為國宗臣,而中更世宗皇帝御政一十三年,輔相德業,冠絕百寮,至于配食大烝,頒請遺詔,蓋千古明良遭際所未嘗有。論者謂漢之蕭、張,唐之房、杜,得公抑云專矣,視公猶其末焉。鴻章往歷史館,征求故事,為欽仰者久之。乃者公來孫紹文、紹華復刊公《澄懷園文存》,乞為一言。
鴻章受而卒讀,以為古今文章之變萬有不齊,要以經世實用為貴。公平生不以文名,而國家政典所關,非公固莫與屬。終明之史纂修數十年矣,至公受命總裁,始有成書,頒之學宮。軍機處政本所出,猶古之中書門下也,公創定其制,上契宸衷,億萬世奉為程法。此其犖犖大者,無知愚知之矣。至其文存一編,上焉宣德紀恩,以匡贊廟謨,開太平無疆之業;下焉抒情述事,以扶翼賢杰,見師濟盈庭之美。沨沨乎盛代之元音,斯文之正軌也。讀者至是,彌以見重熙累洽之世,敦大成裕之俗,庶幾旦暮遇之。彼憔悴專一之士,摛筆騁辭,求為瑋麗巨觀,卒無異榮華飄風,好音悅耳,非所論于公矣。孟子誦詩讀書,終以知人論世,有味乎其言之也。公精力絕人,未爽趨朝,逮暮歸第,舉竟日聞見,細書秘冊無稍遺訛,至耄年猶是。禮親王《嘯亭雜錄》嘗述其概,以為才不可及。圣君賢相一德相孚,豈偶然也哉?鴻章以七十之年,宣力中外,昕夕未遑,讀公之文,思公之遇,蓋有邈然不可及之慕。用徇公來孫所請,粗發其凡,冀與知言君子,共商榷焉。光緒十七年秋九月,合肥后學李鴻章序。*張廷玉:《澄懷園文存》,《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29冊,影印光緒十七年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奉使朝鮮日記序*光緒十六年(1890年)四月十七日,朝鮮國王母妃趙氏薨,右侍郎崇禮以副使身份往朝鮮致祭,自天津出發,至仁川登陸。禮成,循原道返京。是書為崇禮記奉使行程,書成請序于李鴻章,李遂為此序。
光緒十六年秋,朝鮮國王以太妃之喪來吿,用故事遣使賜奠,詔以戶部侍郎續君燕甫,崇君受之為正副使。先是,驛路出奉天東邊,特命改由天津乘北洋輪船直抵仁川,以達漢城,省陸路供億之煩。上念其國新被兇荒,非常制也。兩使以九月望后一日朝辭,十月望日覆命,往返甫一月。今年春,受之侍郎以所編《使韓日記》屬序,記中詳載案牘、儀制,排日編纂,令后之考求故實者有所據依。非如昔人奉使紀行諸書,但敘風土,記程途者比也。
謹案《周禮·小行人》:使適四方,有札喪賻補之禮。《春秋》經傳書天王歸赗會葬皆行于服內諸侯。漢以后始有天子遣使外蕃之儀。朝鮮于我朝歸命最先,被德最渥,莊穆、忠宣以來,臣節亦最純。僖順嗣封五十年,國中大事必奏取進止,特為圣祖仁皇帝所褒嘉,厥后累朝加恩之詔,史不絕書。封賞唁卹,例以三品以上滿洲大臣充使外蕃,而視同服內。殊恩異數,有非他國所敢望者。兩侍郎以豐鎬世臣,位司農,長譯署,譽望華重,聞于中外,持節下臨,虔奉詔書,敬舉典章,海外列邦,環視聳聽,蓋自各國通商之后,始見中朝使命之至也。《春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榖梁傳》:“重天子之禮也。”何休《公羊解詁》以為“書天子之厚”。蘇寬《左氏義疏》云:“外鄉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合觀三傳所述,其義微而顯矣。鴻章久領北洋,于朝鮮之開海禁,實左右之。既又遣兵定其亂,請吏駐其國。凡交涉之事,悉以上聞。使臣之來,復得親候疆除道之役。固樂睹是編之成,以昭示后來也。光緒十九年二月李鴻章。*崇禮:《奉使朝鮮日記》,李德龍、俞冰主編:《歷代日記叢鈔》第135冊,影印光緒間木活字本,學苑出版社2006年版。
重修廣平府志序*吳中彥,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履任廣平府知府,決意重修府志,遂于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正月開局,委郡人胡景桂任總纂,至光緒二十年(1894年)八月修成,請李鴻章為此序。
光緒甲午秋,余督畿疆之二十有五年,廣平吳守中彥,呈進新修府志六十四卷,乃屬余門人胡編修景桂所纂輯。憶自同治壬申,光緒丙子,兩次奉命巡閱營伍,道出洺州,會洺河壩工告成,河道順軌,駐節清流之滸,見夫井田櫛比,風土人情,純樸淵懿,與二三耆老言論,率彬彬知禮讓,識大體。史所稱趙地慷慨悲歌,相聚游戲之習,概所未聞。未嘗不嘆雅化覃敷、首被教澤者之入人尤深也。
方志相沿之通弊,莫大于夸飾,莫濫于攀附。夸飾則古跡人物輾轉牽引,攀附則瑣屑之吏跡,庸沓之詩文,濫羼其中。余嘗修《畿輔通志》,檄各郡縣,采進舊志,纂呈新志,累累然,紛紛然,求其體例謹嚴,考證詳確者,殊不多覯。今閱此志,義例多合古法,復遵依通志,以圖表略傳挈其綱,而每卷必加考訂,不特百四十余年之物曲人官,大端備具,而能志之,誤者正之,支者節之,遺者補之,疑者闕之,不沿訛,不掠美,瞭如秩如。亦尚無夸飾攀附之弊,而風俗物情,昔所聞見者,恍然如在目前焉。余嘉吳守職事之勤,與此書考核之詳且慎也。故樂而為之序。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合肥李鴻章撰。*吳中彥總修、胡景桂總纂:《重修廣平府志》,光緒二十年刻本。
蠶桑萃編敘*《蠶桑萃編》是清末衛杰綜合多種蠶書中的材料,于光緒二十年(1894年)編成的中國古代篇幅最大的一部蠶書,是研究中國近代蠶桑技術發展的珍貴資料。書成,應衛杰之請,李鴻章為此序。
國朝畿輔總制歷年最久、善政最多者,首推桐城方恪敏公,繪《棉花圖》以惠閭閻,厚民生也。余久忝督篆,念畿輔水旱偏災亟思補救,因辦蠶桑一局,命司、道綜理其事。今春衛道以所述《蠶桑圖說淺說》問序于余,戎機之暇,披閱是書,上冊《種桑圖說》有八,中冊《養蠶圖說》十有二,下冊《繅絲紡織圖說》有八,事有本末,語無枝葉。稚童老嫗猶能解曉,以其心體力行,故言之歷歷如繪也。
粵自同治九年移節畿輔,因地瘠民貧,即飭官斯土者興蠶桑利。或政事紛繁,不惶兼顧;或視為不急,未肯深求。間有究心樹藝,一經遷任,柔桑萌蘗多被踐踏斧戕。及綜核名實,咸以北地苦寒,不宜蠶桑對,每聞而疑之。《豳風》農桑并重,觱發栗烈與此地等,且余往年躬履川北各郡,風土氣候略同三輔,歲獲蠶桑重利,是非北地不宜,實樹藝有未講也。迨光緒十八年春,以衛道籍隸蜀郡,深諳樹藝,俾會同長白裕藩司設局提倡,由川揀子種、購蠶子、選工匠,來直試辦,于保定西關擇沃壤為桑田。課晴雨,以審天時;辨旱潦,以廣地利;勤培養,以盡人力。切實講求,冀必有成。十九年得桑百萬有奇,二十年得桑四百萬有奇。各屬紳民領桑蠶者,遣教習導之。民間歲益絲繭以數十萬斤計,而所增土產在十萬金以上矣,此《傳》所謂“務材訓農”者與。局中工匠率聰慧子弟繅絲紡絡,織緞制綢如式并鄉間開機試織。其大宗絲繭派員收買,出洋銷售,以便民商暢行,此《傳》所謂“惠工通商”者與。夫以目前種桑,與恪敏種棉,其為我國家衣被群生者,猶是《豳風圖繪》遺意。
綜計蠶桑一事,經營十余年,尚未就緒。自壬辰迄乙未,閱時未久,種桑、養蠶、織紡三端漸有可觀,司事者其各勉厥職,勿避嫌疑,痌念時艱。集眾思、廣忠益、開誠心、布公道,務期實惠及民,久久行之,藉補水旱偏災之不逮,是則余之厚望也夫。光緒二十有一年夏四月,直隸總督合肥李鴻章撰。*衛杰:《蠶桑萃編》卷12,光緒二十六年浙江書局刻本。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版《李鴻章全集》共收李氏詩文230篇,20多萬字,功不可沒。但以李鴻章事務之多、領域之廣、年壽之長,其失收詩文恐亦不乏,以上拋磚引玉,期同好更為搜輯,以為相關研究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