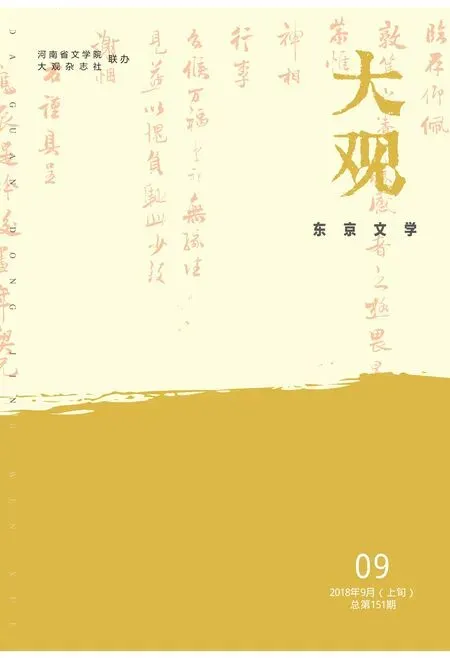不老的風景
楊厚均
這一回,聶鑫森先生向我們展示的仍然是他的短篇,他的三個文字極其節儉的小短篇。三個小說,加起來不過六千余字。
《下午茶》。《別墅院的菜園子》。《比鄰》。正如三篇的總題“凡人俗事”所示,三個小說寫的都是一些瑣碎的人事:《下午茶》寫機電廠廠長勞樂和他的同學茶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言默兩人之間的一次茶聚,名叫“放下”的茶具是小說的“心眼”所在,揭示的是“閑可生靜,靜可生涼”的人生態度;《別墅院的菜園子》把身處城鄉兩地一家三代和睦相處的故事,引入到對一種傳統生活方式的留戀與憂慮之中;《比鄰》講述的是一對老鄰居間友善誠信的往來。
說實在話,僅就小說主題本身而言,似乎并沒有太多可說的。盡管,三個小說,作者還是動了一些心機:通過三種不同生活空間——城市、城市準鄉村(公園式別墅)、原生鄉村——的瑣事來演繹傳統文化永恒的命題。這的確讓我心生感動。但我不得不說,小說讓我保持持久興奮還是它的文體,它的節儉的文字。
在我的閱讀經驗中,今天的小說是越寫越長了,而聶鑫森卻是少數專注于短篇的優秀作家中的一個。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老一輩作家孫犁、汪曾祺等爐火純青的寫作,成為文壇美麗的風景,一些中篇長篇作家,也非常重視短篇寫作,優秀作品迭出,還有一些青年作家,一開始寫短篇就非同凡響,只可惜后來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并不擅長但卻能帶來諸多好處的長篇中去了。那個時期每年一度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含金量非常之高,影響也是非常之大。聶鑫森就是那個時候冒出來的短篇高手,我甚至曾經預言,他的短篇小說極有可能獲全國短篇小說大獎。當然很不幸,這預言沒有成真,這應該不是我的不是,更不是聶鑫森小說的不是,是文學的整體氛圍發生了大的變化的緣故,那個獎不知從哪一年起就沒有了。
可貴的是,在短篇這塊園地,聶鑫森一直堅持了下來,不高產,但從不斷線,細水長流,更其清醇。我曾冒出這樣一個疑問:為什么他就能樂此不疲呢?
我們的確感到了他對于這樣一種節儉文體的偏愛,我們甚至感到,這種節儉文體的背后,是作者一片深切的文化情懷,一種頑強的文化心理,一股巨大的文化力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們談論孫犁、汪曾祺時,常常會言及古代筆記體小說,言及劉義慶,言及傳統文人,我們今天談聶鑫森是否還是可以沿著這樣一條線索?
還是來看這三個小說吧。
小小的篇幅自然是無法容納太多的人物的,《下午茶》只有兩個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好友,《別墅院的菜園子》雖是一家五口,母親、孫女基本上沒有怎么出場,母親只有一句話,孫女也只有被動答話的兩句話,實際在場的也只有父親秋滿倉和兒子秋聲賦兒媳宦靜靜三人,《比鄰》雖然涉及到的人物有兩家兩代同樣五人,但真正的主角則是常惠生一人,全文基本上就只是寫常惠生一人的行為和心理。
人物的多寡,同時也決定了場景轉換的頻率與場景規模的大小,三個小說的空間場景也是極為簡單的,中心場景基本上就是每篇一個:一個茶室,一片菜園,一條通往鄰居家的山路。極簡的人物和極簡的場景,到底是文體本身的規約,還是文體選擇者的內在的文化審美取向?在一個人口高度集中的現代社會,在生活空間因我們對速度的征服和我們不斷擴張的欲望的推動而發生越來越頻繁的轉換,同時被越來越多的物質景觀所充滿的時代,作者的這種選擇是否會變得越來越艱難越來越悲壯?
與此相應的是故事的波瀾不驚。只有微瀾,不見風浪。一次茶聚,就足以平息勞樂滿身心的焦躁;秋家兩代觀念的錯位,因相互的體諒而避免了尖銳的沖突;常惠生與尹德山的善良與誠信輕而易舉就化解了旁人的議論與家人的不滿。在這里,沒有巧合,更沒有博弈,一切就這樣簡單自然,這樣流水般逶迤而安靜。
小說的節儉之處還在于結構布局上的直接與樸實。開局沒有景深,不作鋪墊,直接進入現場;中局不生枝蔓,不弄玄虛,不設樞紐,多以對話、心理活動直接推動演繹“故事”;結局水到渠成,戛然而止,沒有卒章顯志、懸念大白的快意情節設置。如果用攝影術語來形容的話,三篇小說,既不是遠點聚焦,也不是近點聚焦,而是中點聚焦。如果說遠點聚焦與高遠飄逸的審美心理相聯系的話,近點聚焦則更多一份深入現實追尋刺激的精神訴求,而與中點聚焦相伴隨的卻是一份樸實無華的人生趣味。
人物、故事、結構,從某種意義上也就奠定了語言的走向。小說的語言同樣是節儉的。首先表現在心無旁騖的語言流向。如果我們把一個文本的語言形容為一條河流,那聶鑫森小說的語言便是一條平緩的沒有彎道和洄渦的河流,不會在任何一個局部做過多的停留,而以此來宣泄自己的語言快感,行其所行,止其所止,朝既定的目標緩緩而去。其次是簡單明白的陳述句式。小說并不在意句式搖曳多姿的變化,大量的陳述句式運用,雖顯單調,卻也淳樸自然。《下午茶》的開頭:“在這個三伏天酷熱的下午,火辣辣的太陽曬得到處生煙。焦躁的勞樂開車來到湘楚茶文化研究所,然后從車里躥出來,直奔這棟小樓的三樓,敲開了言默工作室的門……”,寥寥數語,時間、地點、人物、環境以及勞樂焦躁的性情盡交代完畢,這樣一種在當下創作中并不討巧的言語方式,在聶鑫森這里依然運用得如此得體、嫻熟。蜻蜓點水式的傳統白描手法的運用,是聶鑫森小說語言的另一特色。與白描相對應的是各種各樣的修辭,烘托、對比、比喻、擬人、排比、反問、頂真等等不一而足,聶鑫森的小說在這些方面似乎顯得異乎尋常的麻木,整個就是一個實心眼,修辭的缺席,導致語言的經濟、實在,內在的是主體情感的深藏不露,因為在我看來,修辭的出現,原是言說者主體強勢介入的結果。
說到情感,這的確是我們理解聶鑫森小說的關鍵。很明顯,三個小說,簡單樸實的背后是一種浪漫情懷,一種對傳統的鐘情與守望。作者曾在他的某個小說的創作談中說自己“還算是個喜歡讀書的人,尤對國學方面的書情有獨鐘”,說他的小說“不著意于故事的編排、營造,都是日常生活的碎片,似乎很散,但籠罩其間的是一種傳統文化的氛圍”。奇怪的是,我們在小說中明明感到這些,卻并不知道作者的這種浪漫到底從哪里流溢出來。我們甚至看不到作者對他筆下某個人物的特別細致的描寫,他似乎是默默地看他們,看他們不緊不慢,看他們獨來獨往。我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聶鑫森的作品中,很少見有年輕美麗的女性主人公的在場。一般來說,作家特別是男性作家,總會把自己的理想符號化為一個女性主人公,這樣更方便他隱晦而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比如前面提到的孫犁、汪曾祺,他們都曾表示要除盡火氣,要把文章寫得散淡,但他們的作品里都有標志性的女性符號,在這樣的符號里,作者盡情地投射自己的情懷。作為聶鑫森同鄉的湖南作家,如沈從文、周立波等同樣以短篇小說著稱的浪漫作家均是如此。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在聶鑫森這里,美麗女性符號的缺席,是他人生態度更為沉潛所致?這樣的一份淡定,莫不正是傳統文化的真諦?
幾個散淡的人物,相對封閉的空間,波瀾不驚的故事,樸素的布局,平淡的語言與深藏的情感,這幾乎就是聶鑫森短小說的全部文體特質。
聶鑫森最近說,上年紀了,總喜歡寫短些。事實上,在我的印象中,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他就把小說寫得很短。他的短小說的文體特質,三十多年就沒有太大的改變,除了越寫越老到以外。大凡一般作家,在寫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總是要另辟蹊徑,尋求自我突破。然而,這種自我突破的意識,在聶鑫森這里似乎并不強烈,幾十年來,他一直就沿著這條路子,不緊不慢,不溫不火。這需要多大的定力,多強的內心?和他作品中所講述的傳統文化相比,我覺得,聶鑫森的這樣一種文體自覺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傳統的精彩而頑強的演繹,他這樣的文體在后現代文體紛亂的時代,將是一道不會褪色的風景。
想起三十多年前的某個夏天和我的表兄胡厚春(株洲作家)去拜訪聶鑫森的場景:瘦高的他穿著寬松的白布大褂,因高大而微曲的身子,顯出幾分天生的低調,搖一把蒲扇,招呼我們坐下,然后津津樂道在北京學習時某老先生講古典詩文意象的故事。那時的他也不過三十多歲吧,而神情卻更像一位純樸的老者。三十多年以后,讀他新近的作品,我得到的還是這個印象。一個老成的作家,也是一個不老的作家。他和他的文體,是老到的,卻是不會老去的。
他是一道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