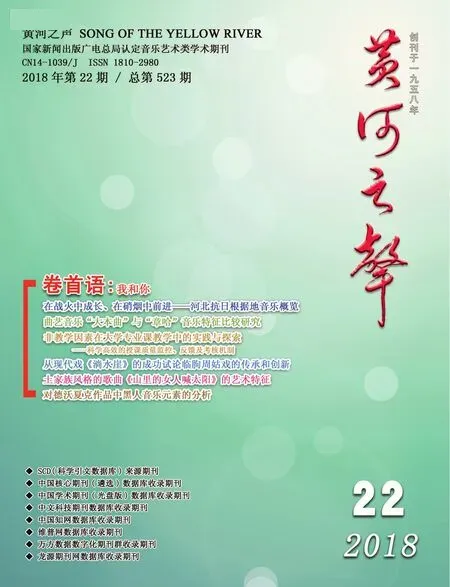《黃水謠》的美學分析
茹 悅
(中北大學藝術學院,山西 太原 030051)
美聲作品《黃水謠》從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美學觀出發,從藝術的特征角度來分析如下:
一、形象性
馬克思認為:“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在《黃水謠》這首美聲作品中,“黃河”其實是個自然力,被藝術家用美學的觀念賦予了形象性的力量,開篇點題地提到“黃水奔流向東方”表現黃河的奔流不息、“水又急,浪又高”黃河的水急浪高、黃河的綿延不絕正是象征著我們中華兒女不畏艱險、不怕困難的高尚情操與高貴品質,借助黃河其實是在為中華民族而發聲,但“奔騰叫嘯,如虎狼”又從反面表現出當時日本對中華民族的摧殘,在人們心中如虎狼一樣可怕,簡直是場噩夢。歌曲中“麥苗兒肥、豆花兒香”更是將自然力加以形象化,表現出抗日戰爭到來前,我們老百姓男耕女織,家家戶戶是一片祥和安逸的生活狀態,沒有壓迫沒有苦難,只有簡單幸福的小日子。
二、情感性
文藝創作依靠于情感,以情感為表現內容和創作目的。結合《黃水謠》這部作品,歌曲的前半段色彩明麗,情緒上采用了明朗的抒情方式,但它是受過苦難的人們對失去家園的美好追思和懷念。后半部分,突然情緒大轉變,與一開始的風和日麗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強烈的對比,這一部分情緒變得沉重而遲緩,使得聽眾在欣賞作品時也會心頭一緊,感覺情感一下子開始壓抑低沉無奈悲涼,情緒也變得悲憤痛苦,作曲家采用了藝術的情感性的處理方式,通過運用藝術中旋律加寬、速度變慢、力度加強的技術手段,孕育出了與先前完全不同的充滿反抗與仇恨的主題情感。同一首作品,運用美學觀念創造出了矛盾與對比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情感表達。
三、個體性
情感悲傷的作品有很多,表現形式也有很多,此時個體性就顯得尤為重要,就像一個事物存在就離不開個體的表現力,《黃水謠》通過“丟掉了爹娘,回不了家鄉”的描寫,細致入微地刻畫出一種國仇家恨,我們不能看出這首作品是一個民族的悲傷,是國之殤!!!這種情感是國家與民族的,并不是男女之間的小情小愛不是花前月下不是可望而不可得。這就是一個作品的個體性,是這種獨特性使得每個作品有了自己的生命與靈活,使得作品擁有了不可替代性,使得一些像《黃水謠》一樣的作品因為它的時代特質被時代與歷史被國家與人民銘記。但是,當環境變化后,個體也會隨著變化,要與之和諧。或個體要隨大局走,要隨潮流走,要與時俱進。所以,通過個體的特色我們可以以此看出它所在的時期的特色及風格。《黃水謠》是一部具有抗日戰爭風格的作品,這是冼星海的代表作,也是中國近代聲樂作品的經典作——《黃河大合唱》中的一首可以獨立存在的混聲合唱或女中音獨唱歌曲。用歌謠式的三段體寫成,它的音調樸素,平易動人。這首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抒情、親切。描寫了奔流不息的黃河之水,同時傾訴著人們在美麗肥沃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景象。第二部分:“自從鬼子來,百姓遭了殃!”以它較低的音區。悲痛的音調、緩慢的速度,寬廣而沉重的節奏,與第一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充分表現了我大好河山被敵寇踐踏,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人們義憤填膺的情緒和燃燒起來的仇恨怒火,這悲憤有力的控訴,深深地打動著人們的心弦。第三部分是第一部分的變化再現,黃河奔騰依舊,而遭到破壞的人民生活,卻呈現出一幅凄慘景象,歌聲在平穩、低沉的情緒中結束,使人久久難忘。這首歌曲長期以來深受人們的喜愛,同時成為一些專業團體和專業歌唱家的必備演出曲目。還曾被其它音樂形式所借用,是一首久唱不衰的聲樂作品。從作品個體本身出發,我們就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作品風格特色,在演唱表演時也會有整體把握。
四、審美性
任何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都不是想到哪里寫到哪里的,而是在創作定稿前,在內心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基本的框架,無論是題材、內容、基本表現力、情感基調、藝術手法還是表達與韻文韻腳都會做到心中有數胸有成竹,這便是人們對藝術審美性的考究。這也是我們與動物的不同,蜜蜂在筑巢的時候一定不會在心中有任何的構思,但任何一個才藝平平技能再蹩腳的建筑師都會在修筑房子前在心中已經有了基本圖紙。在《黃水謠》中,創作者通過“遭殃、凄涼、逃亡、家鄉”這些詞語并不是靈機一動的巧合,這不是一個偶然性,而是藝術家為了使作品擁有藝術性,而特意進行深思熟慮后形成的韻律韻腳。正是美學中的這個理論指導,使藝術家在創作文藝作品時,使藝術作品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本身,作品的素材選自生活,但加入了藝術創作,正是這種藝術構思給予了人們“美”的體驗,而不單單是平淡無奇、庸庸碌碌得去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