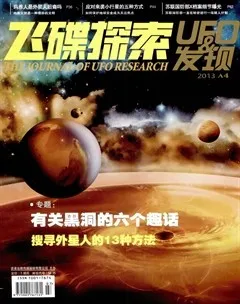之四:黑洞是時空隧道的入口嗎?

真的有“時空隧道”嗎?讀者可否知道,比白洞之說更離奇的還有“蟲洞”之說。蟲洞是連接黑洞與白洞的某種神秘通道,在它里面可以快于光速的速度做宇宙旅行,可以使時光倒流。
此說源于1988年。美國天文學家索恩和他的兩名學生,共同發表文章論述了蟲洞的特性,并認為如果蟲洞開通了黑洞與白洞兩個奇點之間的一條神秘通道(這條通道開在現實的三維空間之外的超空間里),就可以通過這條捷徑從黑洞鉆進奇點,然后從另一個非常遙遠的白洞奇點鉆出。這樣的一種旅行是即時的,等效于超越光速。
然而,一些科學家對此結論難以接受。霍金一開始就持反對態度,認為時間只能向前不能向后的特性是不容破壞的,物理學定律不允許有什么“時間機器”可以使時光倒流。但索恩的回答是:“在物理學深刻認識量子引力理論之前,我們誰也不能下結論。”美國物理學家福特和羅曼也撰文指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并沒有嚴格排除快于光速的旅行或時光旅行。英國牛津大學的理論物理學教授強森也相信,有朝一日,人類將能夠遨游宇宙,縱橫古今。
就在兩種對立的說法相持不下時,霍金改變了態度。他在為美國天文學家勞倫斯·克羅士出版的新書《星旅物理學》所作的序中,大膽推翻了自己過去的假設,公開承認了時光旅行的可能性。他說:“當科學尚未能讓人類登上前所未有的奇妙境地之前,科幻小說早已使我們在各種異想天開的可能性中先行盡游……”他表示,一旦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及量子論結合在一起思考,發覺超光速星際旅行極可能會造成使人們回到過去的結果時,天文物理學已邁向一個嶄新的紀元!
時至今日,相信人類能夠通過所謂的超光速旅行而回到過去的人越來越多。這不只是因為人們對時光倒流的奇妙想法極為熱衷,更關鍵的是它與奇點理論相襯托,甚至有很多真實事件能夠佐證。
1975年,美國國家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37客機正準備在邁阿密國際機場降落。突然,飛機從航管員控制的雷達屏幕上消失,航管員還以為發生了墜機事件。過了10分鐘,該機又從它在雷達屏幕消失的位置上奇跡般出現,令航管員驚訝不已。飛機降落后,有關人員前往調查,機上所有人都說沒有發生任何異常。不過,最使人不解的是,飛機上所有人的手表及機上的航空鐘都離奇地比地面時間慢了10分鐘。這消失的10分鐘到哪里去了?在那奇妙的10分鐘里,飛機又到了哪里?根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只有飛機加速到接近光速時,這種情況才有可能出現。
類似的事件還有數十起,這些傳聞雖然未經官方證實,聽起來“神乎其神”,但按照黑洞理論去對照,這些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在黑洞中,時間和空間的概念截然不同,用“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來描述都不能算是確切的。因為在這個“洞”中連1秒的時間都沒有,沒有時間也就沒有三維空間,完全是即時的。
現今世界上出現的很多不解之謎,只要與時間和空間有關,那就預示著與黑洞有關。不過,有學者持相反意見,認為任何三維物體都不能進入黑洞,只能不相容地“穿”過黑洞。以“穿”過黑洞作為捷徑,能夠節省大量的時間和消耗,這應該是一種比較現實的時空隧道。
究竟有沒有時空隧道?它是人們的科幻作品,還是確有其事?由于它與黑洞緊密相關,所以,隨著黑洞之謎的逐步破解,時空隧道的真實面目也會顯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