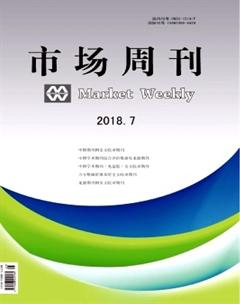上海陸家嘴金融服務業集群研究:基于倫敦歷史經驗的啟示
摘?要:金融業是經濟活動的中心,隨著信息科技的發展,銀行、證券等金融公司在倫敦金融城的聚集程度一直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零售店,因此金融產業集群并不一定是一個正確的方案。本文從金融服務產業區域集群的角度,以倫敦金融城的金融服務產業集群到產業分解為例,分析上海陸家嘴金融服務產業集群從長遠考慮代價高昂,并對陸家嘴金融服務業的未來發展提出幾條建議。
關鍵詞:倫敦金融城;金融服務業;產業集群;陸家嘴
中圖分類號:F83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428(2018)07-0104-02
一、 緒論
金融業是經濟活動的中心。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和商務運營環境能夠有力地吸引全國范圍的銀行、公司到此聚集,吸收巨額的資金流動。近年來我國積極建設金融產業,促使金融服務產業區域集群,以形成影響全球資金流動的金融中心。事實上,在倫敦金融城,金融公司的聚集程度近年來一直在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零售店,因此金融產業集群并不一定是一個正確的方案。
二、 金融服務業集群發展的內在動因
經濟意義上的區域指的是經濟活動相對獨立、內部經濟聯系緊密、體系較為完整、具有特定功能的地域空間,通常分為同質區域、極化區域及計劃區域。產業的區域集群作為一種空間經濟現象,通常是由于歷史、偶然或者政策規劃產生的,集群的增長速度取決于邊際報酬遞增、運輸成本和需求的交互作用,是在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和更新過時的技能和知識之間抉擇以及區域產業之間互相滲透的結果。關于金融服務業,形成其區域集群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信息擴散和非正式信息交換的需要
企業的發展壯大不是一個孤立的過程,而是一個不斷實現信息輸入輸出、與其他企業實現競爭或者合作關系的過程。無論是合作或者競爭的企業之間都需要實時了解市場動態,掌握其他企業的產品或服務信息,同時也必須與其他企業密切聯系,獲取自身生產所需要的產品或信息,在市場導向的經濟大環境下,經濟活動聯系密切的企業各自都不能獨善其身,金融服務更是如此。
(二)降低競爭與合作過程中交易成本的需要
利益最大化的企業要求經濟活動相關聯的企業彼此相互靠近,以分得最大的市場范圍,這為產業集群提供了最初的行動力;而需要合作的企業由于聯系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空間成本)的限制,不得不逐漸集群,降低成本以實現更大效益。金融服務生產鏈是一種關系型的生產系統,這種關系的穩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企業雙方的信任程度,而最初信任的建立以及后期信任的維系都迫切地需要地理上的接近。
(三)與客戶關系營銷的需要
金融服務業產品的生產具有強烈的客戶導向色彩,需要與客戶保持密切聯系以獲得關于客戶意愿的第一手資料,而這種資料的獲取幾乎都需要面對面的交流,只有面對面的洽談才是信息尤其是時效性很強的信息的首要獲取渠道。
三、 金融服務業集群趨勢的反轉——以倫敦金融城為例
倫敦金融城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這里有世界最大的外匯市場,2013年倫敦日均外匯交易約2.5萬億美元,占世界總額的41%。同時,倫敦是世界最大的OTC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市場,2013年倫敦日均外匯交易約1.5萬億美元,占世界總額的50%。倫敦金融城的聲譽價值遠遠超過其區域位置,它已經作為一種金融文化象征深深印刻在人們內心,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范圍內,位于倫敦對于企業來說本身就是一項很有價值的品牌。其次,盡管許多知識是從附近的競爭對手和支撐服務機構中獲取的,但接近客戶、訓練良好的勞動力、專業化團體這三項在倫敦區位優勢中同樣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時,倫敦作為世界著名的大城市,具有寬泛的吸引力和多樣性的文化,四海一家的氛圍和活力四射的環境使得人們樂于在這里工作生活,這是一項重要的商業資產。
盡管在金融服務產業集群方面有眾多優勢,但是2007—2012年以來,銀行、證券等金融公司在倫敦金融城的聚集程度一直在下降,許多金融機構放棄了倫敦地址所帶來的聲譽,在遠離金融城的其他地方尋找價錢更低的辦公場所。無疑,金融服務業比制造業對區域集群的要求更高,但由于信息技術的進步,曾推動倫敦金融城的出現,帶來一種特殊土地使用形式的那種城市密集程度值得人們深刻反思其當下的不合時宜性。
由于金融集群程度下降的數據難以統計,本文用倫敦地區和金絲雀碼頭的金融服務業就業人數的對比來代替說明倫敦金融集群程度的變化。2007—2012年倫敦地區金融服務業就業人數一直處于下降趨勢,金絲雀碼頭的金融服務業就業人數一直呈上升狀態。由此可見,作為世界金融中心的英國逐漸開始放棄金融集群的戰略,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這對中國上海金融產業集群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見圖1)。
四、 上海陸家嘴金融服務業集群分析
作為中國唯一以“金融貿易”命名的國家級開發區的上海陸家嘴金融城,在其蓬勃發展之勢下冠名為“東方曼哈頓”。截至2011年底,上海市金融業創造的GDP達2240億元人民幣,證交所、證券市場以及期貨市場的迅速發展,使陸家嘴金融城的金融中心地位更加穩固。國家和上海市在制度創新和擴大開放方面對浦東的先行試驗給予大力支持,如中外基金和投資銀行的配套政策,吸引各類金融機構,在產業政策導向上則明確要大力發展金融保險業和信息服務業等現代服務產業,這些都是陸家嘴金融業集群發展的制度環境。陸家嘴金融圈就是通過這種制度安排與環境再塑先建立起一個設施完備的空間區域,吸收金融產業進駐圈內,實現金融產業集群。但是,陸家嘴的金融服務業集群絕大部分根源于政策支撐,來自政府的硬軟件并行;而倫敦金融城則市場多一點,計劃少一點。筆者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這種政策色彩濃厚的金融服務業集群的非必要性:
(一)信息技術的發展
信息技術不發達時,金融活動傾向于集中在信息密集和交流便利的中心地。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以及交易限制的放寬,距離已無法阻礙人與人以及公司與公司之間的交流,金融服務業并不像加工制造業一樣需要企業之間的物質要素往來,絕大部分是以信息流的方式進行交流,完全可以通過四通八達的互聯網完成,對于地域集群的需求不大。因此,現代金融產業更傾向于分布在中心地外圍地區,以降低交易成本。
(二)市場全球化
產業集群的原始動力是經濟活動相關聯的企業彼此靠近,以分得最大的市場范圍,金融服務業并不類似于普通服務業以地理坐標為中心,以其市場勢力為半徑分得臨近的市場范圍,而是以全球作為市場范圍,網絡通訊的出現為跨地區、跨國別的金融交易提供了便利。且陸家嘴金融圈的地價高昂,地域上的集群使企業偏離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三)“去工業化”的不利影響
更重要的是,金融服務業在陸家嘴的集群分布意味著中心城市制造業的轉移,即“去工業化”。然而,對于還未真正實現工業化的中國來說,過早的“去工業化”使經濟錯過了從一系列新興工業中獲益的機會,而這些新興工業使用的土地并不比服務業多,技術工人占工人總數的比重也很高,勞動密集程度跟很多服務業相比反而更低,而且先進的控制污染的技術也讓這些新興工業的污染程度極小。制造業是一個城市經濟的主力,過早的“去工業化”會松動上海經濟的根基,對于上海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五、 啟示
金融服務業的比重往往隨著需求和相對價格的變化而有所增加,但理想的狀態并不是金融服務業不斷將制造業擠出城市中心以此實現產業集群,而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服務業成為上海的工業補充。德國和日本的經驗表明,即使服務業擴大了其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這些國家的繁榮程度及其世界地位仍然取決于制造業的先進程度,因而陸家嘴的金融圈在擠出大量技術含量較低的制造業的同時又阻礙了先進制造業的發展,這對一個城市甚至一國未來發展而言是不可持續的。倫敦金融城金融服務業就業人數的變化數據,就可表明金融集群的趨勢正在反轉,可供反思。通過對陸家嘴金融服務業產業集群現象進行以上定性及定量分析,筆者認為效率重于規模,切不可盲目效仿,需尊重市場機制的力量,賦予其自由。
參考文獻:
[1]李西.加強金融業內控管理具體措施分析[J].經營者:學術版(下),2014(8).
[2]王瑛.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集群形成及外部性分析[J].廣西社會科學,2013(10).
[3]凌宏藝.創新能力與企業跨越式發展[J].科技與企業,2014(2).
作者簡介:
曾璐璐,女,安徽人,南京財經大學碩士,研究方向:經濟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