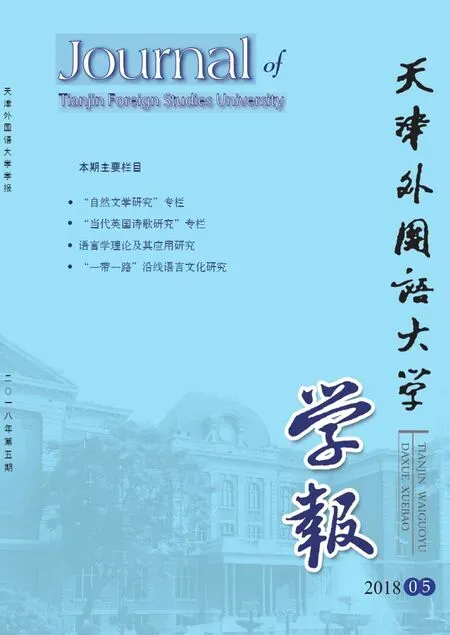達(dá)菲的《世界之妻》:顛覆男性話語塑形的女性想象共同體
梁曉冬
?
達(dá)菲的《世界之妻》:顛覆男性話語塑形的女性想象共同體
梁曉冬
(河南師范大學(xué) 外國語學(xué)院,河南新鄉(xiāng) 453007)
作為西方文學(xué)的源頭,古希臘羅馬神話經(jīng)典作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要么是海倫那樣的紅顏禍水,要么就是像潘多拉那樣的替罪工具,要么是美杜莎那樣的妖魔,要么是赫拉那樣的妒婦。她們都是男性話語中被言說的客體,按照男人的利益、審美價值觀和規(guī)訓(xùn)需要來塑形。當(dāng)代英國桂冠詩人卡羅爾·安·達(dá)菲卻在《世界之妻》詩集中以第一人稱的主體敘事方式,讓神話中英雄的妻子們高調(diào)出場,各自言說自己的追求、情欲和思想,以“我們說”形成了眾女喧嘩的局面,組成了一個女性想象共同體,合力顛覆男性話語權(quán)力下的女性塑形,建構(gòu)女性話語主體地位和女性文學(xué)傳統(tǒng)。
達(dá)菲;《世界之妻》;顛覆男性話語塑形;女性想象共同體
一、引言
女權(quán)運動經(jīng)過三次浪潮,聚勢求變,積漸深入的改革已經(jīng)涉及到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各個方面,聚焦于話語權(quán)力關(guān)系。當(dāng)女性奮力爭取獲得話語權(quán)力,爭取能夠自我表達(dá)并以此來改變被言說的客體地位時,話語主體身份的訴求愈加強烈,原本根深蒂固的父權(quán)話語權(quán)威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歐美當(dāng)代一些女作家①也在文學(xué)源頭尋找改變話語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途徑,她們選擇改寫神話,“寄希望于故事重寫來建構(gòu)自我,重建女性與世界、文化、社會、政治的關(guān)系”(Byatt,2000:124)。
作為深受變革風(fēng)氣浸潤的知識女性和桂冠詩人,達(dá)菲在后現(xiàn)代女性主義語境下也加入神話改寫的行列。在詩集《世界之妻》()中她改寫了一些古希臘羅馬神話和《圣經(jīng)》神話,并采用第一人稱敘事形式,讓神話中英雄們的妻子成為言說主體,表達(dá)各自的追求、欲望和思想,形成了眾妻喧嘩的局面,組成了一個女性想象共同體,以期用合力來顛覆男性話語權(quán)力下的女性塑形,建構(gòu)女性話語主體地位和女性文學(xué)傳統(tǒng)。
二、“我說”:對男性話語塑形的顛覆
所謂話語塑形,是指在話語實踐中話語操縱者對話語對象的客體塑形。它與話語對象的形成、主體位置形成、概念形成以及策略選擇的形成密切相關(guān),是復(fù)雜的話語權(quán)力關(guān)系布展的產(chǎn)物(福柯,2004:128)。簡言之,話語塑形是在特定的話語場域內(nèi)話語權(quán)力者從自身利益出發(fā),按照自己的標(biāo)準(zhǔn)和價值判斷,將被言說的個體進(jìn)行篩選、重組、規(guī)訓(xùn)、命名,塑造成所需要的社會形象。例如,福柯(Michel Foucault)常提到的瘋子形象就是“由一種話語塑形出來的特殊社會客體。瘋子之不正常是相對于正常人的標(biāo)準(zhǔn)而言,瘋子之瘋癲是相對于規(guī)訓(xùn)化的正常生活而言,瘋子作為特殊的社會客體存在是由于心理健康操作中精神病話語場對人進(jìn)行清查、篩選、命名的結(jié)果”(張一兵,2016:258)。在性別話語權(quán)力關(guān)系中,女人如波伏娃所斷言,并非自然天性使然,而是由父權(quán)話語塑造出來的社會客體形象,即第二性。
在傳統(tǒng)文學(xué)話語場域中,“文學(xué)史上的女性形象多半被男性的眼光封鎖在一個十分狹窄的范圍里。女性不可能像男性一樣出將入相,叱咤風(fēng)云。她們只能棲息在歷史的背陰之處,成為家庭舞臺上面的演員,充當(dāng)男性的情欲對象。”(南帆,1996:32)作為西方文學(xué)的源頭,古希臘羅馬神話所頌揚的是男性形象——以宙斯(Zeus)為代表的天神、以阿喀琉斯(Achilles)為代表的英雄、以麥德斯王為代表的國王。神話中的女人要么是海倫那樣的紅顏禍水,要么是潘多拉那樣的替罪工具,要么是美杜莎那樣的妖魔,要么是赫拉那樣的妒婦。男性話語在神話敘事中占據(jù)了主體位置,女性成為男性言說的話語對象,依憑男人的利益、價值觀和規(guī)訓(xùn)需要來打造、塑形。女性要言說自己,首先需要獲得話語權(quán)力。獲得話語權(quán)力的途徑之一便是從文學(xué)的源頭上改寫神話,重新認(rèn)識自己,發(fā)現(xiàn)自己,以自我認(rèn)知和重新界定來重構(gòu)女性形象,借以顛覆男性話語霸權(quán)下的女性塑形。達(dá)菲(Duffy,1999)在詩集《世界之妻》中以第一人稱來重塑神話中的女性形象,忒提斯(Thetis)是其中之一。
忒提斯是古希臘羅馬神話中的海洋女神,神王宙斯曾追求過她。得知忒提斯將來會生下比神王還強大的孩子,宙斯便把她嫁給了密爾彌冬王佩琉斯(Peleus)。婚禮因沒有邀請不合女神厄里斯(Eris),忒提斯遭到報復(fù)。厄里斯暗中把一只金蘋果扔在歡快的客人中間,引發(fā)了“金蘋果事件”,埋下了特洛伊戰(zhàn)爭的隱患,忒提斯和佩琉斯的孩子阿喀琉斯后來也卷入了特洛伊戰(zhàn)爭。忒提斯以色相求助于宙斯,祈求神王幫她兒子阿喀琉斯在戰(zhàn)爭中重獲榮耀。這個海洋女神是用第三人稱視角來描述的,是男性主流話語對她的塑形,即宙斯和海神追逐的情欲對象、被嫁的新娘、遭暗算的受害者、戰(zhàn)禍的替罪羊、有愛的母親。忒提斯沒有言說自己的權(quán)力,只能被動地接受宙斯對她生活的各種安排,唯一主動的是將阿喀琉斯倒提著在天火中歷練,為了兒子的榮耀不惜以色相求助于宙斯。而在達(dá)菲的詩作中忒提斯則是以第一人稱的主體形式來言說自己各種受迫害與遭暗算的經(jīng)歷。
I shrunk myself to a size of a bird in the hand
of a man.
Sweet, sweet, was the small song
that I sang,
till I felt the squeeze of his fist.(1-5)
海洋女神自知在男人手心中不得脫逃,就將自己縮變成一只小鳥,“輕聲唱著甜美的歌”,竭盡全力去取悅于男人,但不能避免被蹂躪的結(jié)局。她扛起“信天翁的十字架”(cross of the Albatross)跟隨船只遠(yuǎn)行,但弓箭手卻在瞄準(zhǔn)她的翅膀(the squint of the crossbow’s eye)。她轉(zhuǎn)而變成一條蛇,蟄伏于巫師的膝頭上(charmer’s lap),卻發(fā)現(xiàn)自己被扼住脖頸幾近窒息(the grasp of the strangler’s claps at my nape)。她憤怒地將自己變成一只食肉的猛禽,下頜里還吞著斑馬的血塊(Zebra’s gore raw in my lower jaw ),但她再有火眼金睛也逃不出獵人的槍口。她把自己變成美人魚、海鰻、海豚、鯊魚,但還是逃不過漁民的鐵叉、漁鏢。她讓自己變成白鼠、鼬鼠、臭鼬、浣熊,也逃不出被制成標(biāo)本的命運(taxidermist)。這位海洋女神無論如何變形取悅都掙脫不掉男人的控制和蹂躪,她終于意識到只有自我足夠強大才能掙脫男人的魔爪。她勇敢地置自己于天地之間,在遼闊宇宙中修煉魔法,超越凡胎肉身。
I was wind, I was gas,
I was all hot air, trailed
clouds for hair.
I scrawled my name with a hurricane,
when out of the blue
roared a fighter plane.(37-42)
女神從大自然中獲取動力和能量,從孱弱的鳥、爬行的蛇、水中的魚、地上的鼠淬變?yōu)轱L(fēng)、火、雷、電和一架怒吼的戰(zhàn)機。她用颶風(fēng)在天空劃出自己的名字,重新界定自我,給自己命名。命名是界定和統(tǒng)轄的權(quán)力。在《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jì)》中上帝賦予了亞當(dāng)為萬物命名的權(quán)力,確立了人統(tǒng)轄萬物的主體地位。亞當(dāng)稱夏娃為女人是因為女人是他的血中之血、骨中之骨,從而也確定了女人被男人統(tǒng)轄的客體地位。詩中忒提斯的自我命名不僅預(yù)示著話語主體位置的改變,更預(yù)示著話語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改變,表明女神要從根本上改變自己被統(tǒng)轄的客體地位。
Then my tongue was flame,
My kisses burned,
but the groom wore asbestos.
So I changed, I learned,
turned inside out—or that’s
how it felt when the child burst out.(43-48)
海洋女神用“烈焰般的舌頭”、“燃燒著的吻”去融化她的新郎,但對方卻身穿石棉瓦衣,水火不融,刀槍不入。她知道不可能借助男性的力量去改變命運,只能調(diào)動自己雌雄同體的原始活力,自力更生,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的生命奇跡,她橫空出世的孩子或許能夠感知母親徹頭徹尾的改變。
從上述文本的解讀中可知詩人用第一人稱主體視角讓女神自述被男性話語控制、規(guī)訓(xùn)、塑形的個體經(jīng)驗,表達(dá)對這些遭遇的憤怒與不滿。女神又從心理、身體和情緒等方面從卑微、孱弱、被動的自我認(rèn)知中扭轉(zhuǎn)過來,與強大、勇猛、獨立等新的自我認(rèn)知進(jìn)行主體對接與認(rèn)同,從而自我重塑成強悍無比、具有雌雄同體原始創(chuàng)造力的新女神形象,來消解男性主流話語對她的社會形象塑造。這也印證了福柯話語理論的核心觀點,即話語的流動性和對抗性。話語可利用權(quán)力將個體塑造成所需要的社會形象,也可顛覆對個體社會形象的塑造。“有真理話語就有挑戰(zhàn)真理的話語;有主流話語也就有邊緣話語。在話語內(nèi)部因為權(quán)力的參與而使這些不同的話語處在流動、對抗?fàn)顟B(tài),話語權(quán)力的交錯移位也因此依賴話語實踐來實現(xiàn)。”(黃華,2005:42)詩人憑借女性話語實踐實現(xiàn)了話語權(quán)力的交錯移位,顛覆并重構(gòu)了忒提斯女神的社會形象。
當(dāng)代女性主義敘事學(xué)家蘇珊·蘭瑟(Susan Lanser,1992:3)在《虛構(gòu)的權(quán)威:女性作家與敘事聲音》一書中說:“聲音,對于這些一直被壓抑而寂然的群體和個體來說,已經(jīng)成為身份和權(quán)力的代稱,有了聲音便有路可走。”達(dá)菲賦予了傳統(tǒng)神話中被噤聲的女神(無論善惡美丑)自己的聲音,進(jìn)而使她們獲得重塑身份的話語權(quán)力和重生之路,美杜莎(Medusa)是又一典型案例。
希臘神話中的美杜莎是戈爾貢(Gorgon)家族三姐妹之一。她曾經(jīng)是個天真美麗的少女,受海神波塞冬(Poseidon)引誘,在神廟里與之野合,失去了貞操。此事激怒了女神雅典娜,她詛咒美杜莎變成丑陋的妖怪,讓她的頭發(fā)變成毒蛇。因嫉妒她的美貌,防止她再與其他男人有染,雅典娜還詛咒凡是與美杜莎眼神相遇的人瞬間都會化為頑石或死亡。為了利用美杜莎眼神的殺傷力,英雄玻耳修斯(Perseus)砍下了美杜莎的頭安插在雅典娜的盾牌上,以化敵為石。
將美杜莎塑造成能量巨大的妖魔是男性主流話語借雅典娜的嫉妒、猜疑之心來懲罰失去貞潔的女性。這種懲罰首先表現(xiàn)在對美杜莎身體的改造和變形上。把這個美麗少女變形為丑陋妖怪,剝奪她美麗的容貌。把她的頭發(fā)變形為蛇,讓她的眼睛具有化男人為頑石的魔力,驅(qū)趕任何試圖接近她的男人,以此來剝奪她做女人和母親的欲望和權(quán)利。他們殘忍地砍下她的頭顱,插在盾牌上以擊退勁敵,毫無人性地把她當(dāng)作御敵工具來使用。正如福柯(1999:26)在《規(guī)訓(xùn)與懲罰》中所闡述的那樣,對人的懲罰與規(guī)訓(xùn)首先是對身體的懲罰與規(guī)訓(xùn),讓身體“直接卷入某種政治領(lǐng)域,權(quán)力關(guān)系直接控制它,干預(yù)它,給它打上標(biāo)記,強迫它完成某些任務(wù),表現(xiàn)某些儀式或發(fā)出某種信號”。從傳統(tǒng)神話中我們看到男性權(quán)力對美杜莎身體的直接控制、干預(yù)和打造,賦予她妖孽的罪名,讓她變形為符合規(guī)訓(xùn)要求的邪惡妖怪形象,強迫她完成退敵的任務(wù),令她成為祭奠貞操的犧牲品。但經(jīng)過達(dá)菲改寫后的美杜莎則是用第一人稱在進(jìn)行主體敘述。
A suspicion, a doubt, a jealousy
grew in my mind,
which turned my hairs on my head to filthy snakes
as though my thoughts
hissed and spat on my scalp.(1-5)
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男性話語塑形使美杜莎仿佛在認(rèn)知上接受了妖魔化的形象,反思是自己心中的猜疑、嫉妒讓頭發(fā)變成了毒蛇,自己的思想也如同毒信一樣拍打著頭皮,發(fā)出咝咝聲響,這個妖魔形象似乎已經(jīng)沉淀在她個體的情感和心理結(jié)構(gòu)中。然而,詩人筆鋒一轉(zhuǎn),讓我們聽到了女神的另一種聲音。
But my bride’s breath soured, stank
in the grey bags of my lungs
I’m foul mouthed, foul tongued
yellow fanged.
There are bullet tears in my eyes
Are you terrified?(6-11)
作為海神波塞冬的新娘,她用“污濁的氣息”、“污穢的嘴”、“腐爛的舌”、“發(fā)黃的獠牙”、“子彈般的眼淚”來嚇退她的新郎。這位曾經(jīng)天真美麗的少女被波塞冬引誘而失去貞操,但受懲罰的并非引誘者,而是被引誘者。她要用被污損的身體器官更加惡毒地來恐嚇和報復(fù)男神的拋棄和背叛,來挑釁男性主流話語對她的侮辱與規(guī)訓(xùn)。
Be terrified.
It’s you I love
perfect man, Greek God, my own;
But I know you’ll go, betray me, stray
from home.
So better by far for me before you were stone.(12-17)
在傳統(tǒng)神話中一貫沉默不語的美杜莎此刻充滿自信地聲稱她一定會讓波塞冬懼怕。她向自己的男神大膽表白,也大膽索要愛的回報。她以自己的話語行為改變了主流男性話語和被壓抑的女性邊緣話語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她用愛的宣言和索取逆轉(zhuǎn)了傳統(tǒng)神話中男女之間主動和被動的關(guān)系,顛覆了用以規(guī)訓(xùn)和懲戒女性的貞潔觀,自我塑造為一個能量強大、邪性十足、敢愛敢恨的新女神形象。
女性主義批評家露絲·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1990:119)曾評論說:“男性話語霸權(quán)下的社會文化結(jié)構(gòu)剝奪了女性欲望和表達(dá)欲望的權(quán)力,結(jié)果女性處于迷茫之中,不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只能歸順于既有的社會話語秩序。”而經(jīng)過達(dá)菲改寫后的美杜莎是一個面帶邪惡微笑的女神。她不甘心歸順既有的社會話語秩序,努力爭取表達(dá)自己欲望的權(quán)利。
I glanced at a buzzing bee,
a dull grey pebble fell
to the ground.
I glanced at a singing bird
a handful dust gravel
spattered down.
I looked at a ginger cat
a house brick
shattered a bowl of milk.
I looked at a snuffling pig
a boulder rolled
in a heap of shit.(13-24)
美杜莎目光的強大殺傷力原本是男性主流話語強加于她的邪惡勢力,這種權(quán)力機制迫使她服從、認(rèn)同和接受這樣的塑形。但是“哪里存在權(quán)力,哪里就有抵抗。抵抗是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另一極,是其不可消除的對立面,是權(quán)力內(nèi)部不可忽視的力量”(福柯,2000:71-72)。人們“在話語權(quán)力關(guān)系內(nèi)部可以對個體重新組合塑造,使個體成為可以表達(dá)話語的主體”(Weedon,1989:112)。達(dá)菲改寫后的美杜莎一方面接受了這種妖魔形象,另一方面順勢將這種邪惡的魔力發(fā)揮到極致,讓生靈萬物統(tǒng)攝在她的目光下,包括“嗡嗡叫的蜜蜂、正歌唱的小鳥、要喝奶的貓、哼哼叫的豬”,讓它們瞬間變成頑石,并以此威懾波塞冬。美杜莎目光的殺傷力是被利用的工具,而改寫后的美杜莎卻發(fā)揮了主觀能動性,主動將目光投向萬物生靈,建構(gòu)自己邪惡強大的主體。
And here you come
With a shield for a heart
and a sword for a tongue
and your girls, your girls.
wasn’t I beautiful?
wasn’t I fragrant and young?
Look at me now.(20-26)
波塞冬背后成群的姑娘觸發(fā)了美杜莎對清純少女時代的回顧和眷戀,展示了她美麗陰柔的一面。她令人心酸的發(fā)問:“我過去不也很美?不也年輕,散發(fā)著少女的芬芳?”是對美的向往、對愛情的追求和渴望。而波塞冬手里的護(hù)心盾、割舌劍和身后成群的新歡令她感到絕望,她再次硬起心腸,喝令他“你現(xiàn)在看著我”,要將他化為頑石。
美杜莎走出了傳統(tǒng)神話,成為有血有肉、敢愛敢恨的新形象。她掌握了話語權(quán)力,從身體、心理、情緒、意識等層面不斷修正、打造自己,從被動的、妖魔化的、邪惡的客體位置逐漸走向主動示愛、強勢、祛魅化的主體位置,并在這樣一個打造過程中消解、對抗傳統(tǒng)神話對自己的塑形,爭取自己的社會地位。詩人試圖再次印證女性形象是被權(quán)力話語塑造出來的,反過來也能夠抵制和反抗話語權(quán)力。話語權(quán)力更替給了傳統(tǒng)神話中被抑制的女性發(fā)聲的機會,她們用“我說”顛覆既有的男性話語塑造,進(jìn)而創(chuàng)造出有時代印記的女性話語和女性主體。
三、“我們說”:女性想象共同體的建構(gòu)
在這部詩集中達(dá)菲采用“我說”的第一人稱敘事手法來顛覆男性話語霸權(quán),重塑女性主體形象。這些獨白者并不孤單,各路英雄的妻子翩然現(xiàn)世,高調(diào)出場,眾聲喧嘩,組成一個女性放歌的盛會,形成了曲調(diào)一致、追求相同的女性想象共同體(community)。所謂共同體,在這里并非指地理意義上的界限或疆域,而是一種烏托邦形式,是人們所尋求的以價值趨同為基礎(chǔ)的共享家園和精神歸屬(Rink,2008:207)。想象共同體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看來終是共同體成員所產(chǎn)生的一種集體歸屬感、一種內(nèi)在的凝聚力或向心力。盡管這些成員或許未曾謀面,但他們懷有對共同體的共同想象,能夠感覺到自己是共同體的一員(Anderson,2004:6-7)。國內(nèi)著名學(xué)者殷企平先生(2016:79)也斷言:“大凡優(yōu)秀的文學(xué)家和批評家都有一種共同體沖動,即憧憬未來的美好社會,一種超越親緣和地域、有機生成、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體形式。”
達(dá)菲在《世界之妻》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越發(fā)傾向重構(gòu)堅強的女性形象,越發(fā)從個體情感的構(gòu)建向群體情感構(gòu)建方向發(fā)展”(Rowland,2003:56)。詩集中的“我說”逐漸匯聚成“我們說”,女性想象共同體也在“我們說”中建構(gòu)起來。我們聽見黛利拉(Delilah)在敘述自己如何幫助大力士參孫(Samson)學(xué)會去愛。黛利拉本是希伯來神話中誘惑大力士參孫的妖女。參孫憑借神賜威力可以徒手擊殺雄獅,可只身與外敵非利士人征戰(zhàn)周旋。非利士人讓參孫的女人黛利拉引誘他說出神力的秘密(即頭發(fā)的力量)。黛利拉趁他熟睡時剪斷了他的頭發(fā),致使他喪失神力而受制于敵人。非利士人挖掉他的雙眼,并將其囚于監(jiān)獄中,讓他受盡折磨,黛利拉也因此成為靠色相引誘并最終毀滅英雄的禍水形象。而在達(dá)菲改寫的詩中大力士卻在求教于她如何去愛。
Teach me, he said—
how to care.
...
I can rip out the roar
from the throat of a tiger;
or gargle with fire
or sleep the whole night in the Minotaur’s lair
There’s nothing I fear.
but I cannot be gentle, loving or tender.
I have to be strong
What is the cure?(1-2,6-13)
面對參孫的困惑,黛利拉用自己“果敢堅定的雙手充滿激情地剪斷他每一縷發(fā)絲”(Then with deliberate, passionate hands/I cut every lock of his hair.),幫助他認(rèn)識自己柔情的一面,教會他如何去愛。傳統(tǒng)神話中的妖女形象在該詩中被反轉(zhuǎn)為充滿溫情的人生導(dǎo)師形象。她剪斷孫參的頭發(fā)并非出自陰謀,而是出自愛。她要在參孫的神力中增添愛的柔情,使他具有神的威力和人的性情,在男女相愛的共同體中學(xué)會分享溫柔和親情。傳統(tǒng)希伯來神話以妖魔化的女性形象讓黛利拉在場缺席,強加于她輕浮陰險的蕩婦特性,不給她自我言說的機會與權(quán)利,而改寫后的黛利拉卻是一個果敢的教母形象,她高調(diào)出場,用愛和柔情來訓(xùn)導(dǎo)感化英雄,彰顯出自信強大的女性主體。黛利拉的形象反轉(zhuǎn)是女性權(quán)力話語對男性權(quán)力話語的有力挑戰(zhàn)。
我們還會聽到奧德修斯(Odysseus)的妻子珀涅羅珀(Penelope)的聲音。奧德修斯曾遠(yuǎn)征特洛伊城,十年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歸途坎坷,在海上多漂泊了十年。人們盛傳他已葬身魚腹,客死他鄉(xiāng)。堅貞不渝的珀涅羅珀為了擺脫求婚者的糾纏,宣稱等她為丈夫織完一匹做壽衣的布料后再改嫁。她白天織布,夜晚又把它拆掉,拖延時間,等待丈夫歸來。后來奧德修斯回到家園,趕走了求婚者,夫妻得以團(tuán)圓。珀涅羅珀是貞潔的化身,是男性教育女性的模范樣本。但在詩中等待不再是珀涅羅珀生活的全部,編織也并非是她打發(fā)光陰的工具,而是通過編織自娛自樂,開發(fā)自身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
I sorted cloth and scissors, needle, thread,
thinking to amuse myself,
but found a life-long industry instead.
I sew a girl
under a single star-cross-stitch, silver silk—
running after childhood’s bouncing ball.
...
I was picking out
the smile of a woman at the centre
of this world, self-contained, absorbed, content
most certainly not waiting,
when I heard a far-too-late familiar tread outside
the door.
I licked my scarlet thread
and aimed it at the middle of the needle’s eyes
once more.(9-14,39-47)
經(jīng)過達(dá)菲改寫后的珀涅羅珀成為一位發(fā)揮女性創(chuàng)造力和主觀能動性的女神。她在編織中建構(gòu)出一個女性成長的烏托邦以及一個筑成女性夢想的圣地。星空下奔跑的女孩和站在世界中央心滿意足微笑著的女人是她的自畫像。她沉浸在自己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中,自得其樂,完全忘記了編織的初衷。門外熟悉的腳步聲也未能喚起她盼望丈夫歸來的激情,她對此充耳不聞,“舔濕了猩紅色的絲線”,繼續(xù)編織著。她以這樣的形象重塑來抵制男性話語對女性的規(guī)訓(xùn),走進(jìn)并占據(jù)世界的中心。她是在女性想象共同體中自我塑形的又一位踐行者。正如法國的激進(jìn)女性主義者西蘇(Helene Cixous,1976:880)所言:“女性必須行動起來,抓住一切機會言說自己,書寫自己。為了自己的權(quán)利,女性應(yīng)該懷有強烈的意愿,在每個政治環(huán)節(jié)、每個象征機制中做行動者和主動參與者。”
在詩集中還有皮格馬利翁(Pygmalion)的妻子加拉泰亞(Galatea)的聲音。皮格馬利翁是塞浦路斯國王,他不喜歡凡間女子,發(fā)誓永不結(jié)婚。他用神奇的技藝雕刻了一座美麗的少女像,他把全部的精力、熱情、愛戀都賦予了這座雕像。他像對待戀人那樣撫愛她,裝扮她,給她起名為加拉泰亞,并向神乞求讓她成為自己的妻子。愛神阿芙洛狄忒被他打動,賜予雕像生命,并讓他們結(jié)為夫妻。加拉泰亞是男性塑造的一個被動形象,是一個沒有生命、欲望、情趣的石雕少女。在《皮格馬利翁的新娘》中加拉泰亞卻演化為主動表達(dá)情欲的女人。
So I changed tack,
grew warm, like candle wax
kissed back,
was soft, was pliable,
began to moan,
got hot, got wild
arched, coiled, writhed
begged for his child
and at the climax
screamed my head off—
all an act.(39-49)
如果說珀涅羅珀在塑造一個藝術(shù)的自我,加拉泰亞則是在塑造一個情欲的自我。在傳統(tǒng)男性話語體制內(nèi)莫要說女性大膽表達(dá)自己的身體經(jīng)驗,她們連自我表白的機會都沒有。如同幾千年來女性的身體被驅(qū)逐一樣,女人也被驅(qū)逐于話語權(quán)力之外,女性情欲的表達(dá)也必定是傳統(tǒng)話語的禁忌。達(dá)菲筆下的加拉泰亞卻主動放開自己,享受性高潮帶來的快感,直白地表達(dá)性感受。她由一個沒有任何知覺的石雕女轉(zhuǎn)變?yōu)檠庵|,讓身體的感受進(jìn)入女性話語,展現(xiàn)生命潮汐的涌動與原始活力。她無疑又是一名男性統(tǒng)治話語的有力挑戰(zhàn)者,她的性獨白是對壓抑女性肉體和情欲的文化秩序的顛覆。這讓人再次想起西蘇(ibid.:876-880)對女性書寫的召喚:“書寫你自己,你的身體之音一定要傳遍世界!只有這樣,你無意識的生命之泉才會涌動,生命的能量才能在世界上發(fā)散。你不可估量的價值才能體現(xiàn),舊的游戲規(guī)則才會改變。”書寫讓女性重新認(rèn)識自己的身體,糾正男性知識話語對女性身體的歪曲,擺脫男性話語霸權(quán)的禁錮,釋放出女性生命能量的力比多(libido),建構(gòu)起以靈肉一體的女性世界。
《世界之妻》的最后一首寫的是大地豐饒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豐饒女神是一個悲情的母親,她的女兒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被冥王哈迪斯(Hades)擄到冥府成婚。悲傷的母親沉浸在失去愛女的悲痛中,大地也因此進(jìn)入嚴(yán)冬,荒蕪一片,寸草不生。后經(jīng)宙斯與冥王商定,珀耳塞福涅可與母親相守六個月,才有了豐茂的春夏與枯萎的秋冬。作為《世界之妻》的壓軸作品,達(dá)菲改寫的豐饒女神得墨忒耳,卻是另一番景致。
Where I lived—winter and hard earth.
I sat in my cold stone room
Choosing tough words, granite, flint
to break the ice. My broken heart—
I tried that, but it skimmed
flat, over the frozen lake.(1-6)
改寫后的豐饒女神選用“粗糲的、如同花崗巖一樣尖利的詞語”來“破除心頭的堅冰”,修復(fù)她破碎的心,改變自己悲傷的心境。她失去愛女的傷痛只能靠自己來表達(dá)、修復(fù),毋需他人來描述和言說。當(dāng)女兒回歸故里時,得墨忒耳興奮地發(fā)誓,讓空氣變得和煦溫暖,讓月亮張開嬌羞的嘴,讓藍(lán)天綻放笑靨,讓春風(fēng)撲面,迎接她的女兒。這位在傳統(tǒng)神話中聲音被遮蔽的女神此刻卻擁有上帝般的內(nèi)在智慧和外在語言,用女性話語和想象力為女兒建構(gòu)出一個充滿溫暖親情的空間,一個令人神往的女性烏托邦。
I swear
the air softened and warmed as she moved,
the blue sky smiling, none too soon
with the small shy mouth of the moon.(11-14)
我們可以看出達(dá)菲滿懷“共同體沖動”,用“我們說”來抗拒男性話語對眾神之妻的塑形,以期建構(gòu)一個“超越親緣和地域、有機生成、具有活力和凝聚力”(殷企平,2016:79)的女性想象共同體。她以詩歌的和聲召喚世界對女性的關(guān)注,以文學(xué)力量介入,并試圖改變性別不平等的社會問題。她實踐了西蘇的女性書寫理念,即女人必須寫自己。女人必須通過寫作把自己帶到文本中去,如同把自己帶進(jìn)世界和歷史之中。一個人的將來再也不可能由過去決定,雖然我們不能否認(rèn)歷史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著我們。但我們決不會一遍遍重復(fù)過去來強化歷史,絕不認(rèn)同過去是我們不可消解的宿命,也絕不會把女性的生物學(xué)意義和文化意義混為一談。這個時代是辭舊迎新的時代,更確切地說是由女性書寫打破舊的男性書寫傳統(tǒng)的時代(Cixous,1976:875)。達(dá)菲通過詩作把遮蔽在眾神身后的女人帶進(jìn)了世界、歷史和未來,帶進(jìn)了女人自建的想象共同體,也帶進(jìn)了女性“我說故我在”的澄明世界。
四、結(jié)語
薩拉·布魯姆(Sarah Broom,2006:69)曾評論說:“達(dá)菲對于古典希臘羅馬神話的重新挖掘,并非單純從敘事的角度來進(jìn)行的,而是以此證明,每個故事和話語都能夠通過自己的聲音,或多或少地得到社會層面的理解和關(guān)注。透過字里行間,人們從(改寫的)神話中讀到了歷史、政治和科學(xué)。這部詩集燭照了女性的無意識領(lǐng)域,從藝術(shù)創(chuàng)作到政治領(lǐng)域都推翻了傳統(tǒng)神話中所涵蓋的既定真理。”換言之,達(dá)菲詩歌中神話人物的重新塑造表面是敘事層面的活動,但深層意義在于敘事中性別話語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較量。《世界之妻》以女性的話語狂歡逆襲上位,以虛構(gòu)的權(quán)威顛覆男性話語塑形,建構(gòu)出一個女性想象共同體,一個具有美好愿景的女性烏托邦。
注釋:
①善于改寫神話作品的有當(dāng)代英國女作家A. S. 拜厄特(A. S. Byatt)、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丹麥女作家卡倫·布力圣(Karen Blixen)、美國女詩人伊麗莎白·都德(Elizabeth Dodd)、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等。
[1] Anderson, B. 2004.[M]. London: Verso.
[2] Broom, S. 2006. Gender, Sex and Embodiment: Simon Armitage, Carol Ann Duffy, Grace Nichole[A]. Contemporary[C].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3] Byatt, A. 2000.[M]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4] Cixous, H. 1976. The Laugh of Medusa[J]., (4): 875-893.
[5] Duffy, C. 1999.[M]London: Anvil Press Poetry.
[6] Irigaray, L. 1990. Women’s Exile[A]. In D. Cameron (ed.)[C]. New York: Routledge.
[7] Lanser, S. 1992.[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8] Rink, B. 2008. Community as Utopia: Reflections on De Waterkant[J]., (2): 205-220.
[9] Rowland, A. 2003. Love and Masculinity in the Poetry of Carol Ann Duffy[A]. In M. Angelica & A. Rowland (eds.)[C].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0] Weedon, C. 1989.[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
[11] 福柯. 1999. 規(guī)訓(xùn)與懲罰:監(jiān)獄的誕生[M]. 劉北成, 楊遠(yuǎn)嬰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12] 福柯. 2000. 性經(jīng)驗史[M]. 佘碧平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3] 福柯. 2004. 知識考古學(xué)[M]. 謝強, 馬月譯.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14] 黃華. 2005. 權(quán)力、身體與自我:福柯與女性主義文學(xué)批評[M]. 北京: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15] 南帆. 1996. 軀體修辭學(xué):肖像與性[J]. 文藝爭鳴, (4): 30-39.
[16] 殷企平. 2016. 關(guān)鍵詞:共同體[J]. 外國文學(xué), (2): 70-79.
[17] 張一兵. 2016. 回到福柯——暴力性序和生命治安的話語構(gòu)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 Imagined Female Community to Subvert the Patriarchal Discursive Characterization in Duffy’s
LIANG Xiao-dong
As the source of the Western literature, the ancient Greek and Roman and mythology maliciously depicts female characters either as Helen, a dangerous beauty or Pandora, a scapegoat, or Medusa, a monster and Hera, a jealous wife, who are shaped in accordance with man’s interests, norms and aesthetical values. Carol Ann Duffy, however, rewrites these mythic stories in her collectionby means of first-person narrators to let the female characters walk out of the male shadow of power, speaking for themselves, letting out their desires, feelings and thoughts. They build up an imagined female community to subvert the stereotypes of the female figures depicted by the patriarchal discursive power. Duffy tries to make female subjectivity in literary discourse and set up the female literary tradition.
Duffy;; subversion of the patriarchal female characterization; imagined female community
2018-07-08;
2018-08-15
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目“當(dāng)代英國詩歌的底層敘事研究”(14BWW053);河南省教育廳高校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優(yōu)秀學(xué)者資助項目“當(dāng)代英國詩歌的底層敘事研究”(2015-YXXZ-13)
梁曉冬,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xué)、西方文論
I106.2
A
1008-665X(2018)5-003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