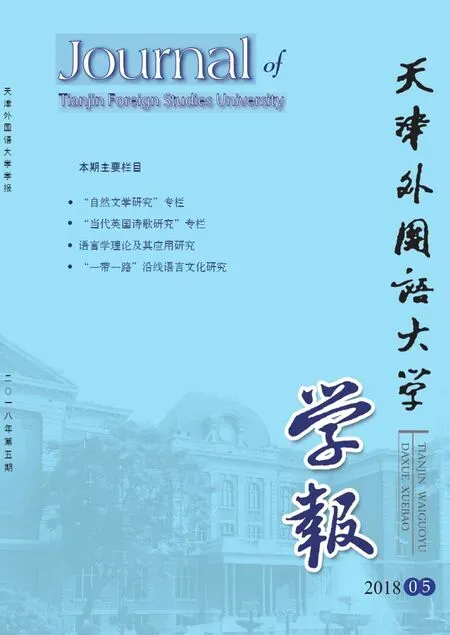伯恩斯坦語碼理論的社會符號學研究
胡安奇
?
伯恩斯坦語碼理論的社會符號學研究
胡安奇
(廣州大學 外國語學院,廣東廣州 510006)
巴茲爾·伯恩斯坦的社會學理論植根于語碼這一核心概念,試圖在語言相對主義視野下探究社會分工、權力與控制、教育話語和文化傳遞等社會學課題,從語言使用切入教育話語,構建自己的結構主義社會學。語碼具備語言學和社會學雙重屬性。從社會符號學視角來看,語碼發揮著符號中介的功能,存在于社會系統之中,一方面體現為社會關系對言語行為的規制力,另一方面在教育話語體系中通過對教育知識的分類和架構,實現社會關系的控制和調節功能。
伯恩斯坦;語碼;社會符號學;符號中介
一、引言
巴茲爾·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是20世紀英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在語言學社會學、教育學社會學以及教育話語理論等方面建樹卓越,其主要成果收錄于四卷本論文集《階級、語碼與控制》和《教育、符號控制與身份:理論、研究、批評》一書。伯恩斯坦的社會學理論植根于語碼(code)這一核心概念,試圖在語言相對主義視野下探究社會分工、權力與控制、教育話語、文化傳遞等社會學課題,從語言研究切入社會問題,逐步回歸涂爾干(Durkheim)的功能主義傳統并最終走上歐洲結構主義社會學的道路(Atkinson,1985:136)。語碼孕育于早期社會學調查活動,成形于六七十年代的語言研究,而后在教育話語研究中被系統提出,可以說貫穿于伯恩斯坦社會學思想的全過程,因而具備語言學和社會學的雙重屬性。韓禮德(Halliday,1975/2007:153)曾明確指出,伯恩斯坦的語碼理論“既是一種語言理論也是一種社會理論”。故而,對于語碼的研究不能僅僅從語言學或者社會學的單一視角出發,而應該從語言-社會的二重維度審視語言在社會系統中的運作機制。就此而言,把語言使用者和社會結構系統均納入符號意義的賦予和識解的社會符號學無疑為語碼的闡釋提供一個較為理想的理論框架。本文正是在社會符號學(Halliday,1978/2001;Hodge & Kress,1979/1993,1988;van Leeuwen,2005;田海龍,2015)的理論視角下梳理伯恩斯坦社會學思想中語碼的概念演進和內部邏輯,探討它的社會符號特征,并對它在整個伯恩斯坦社會學思想中的地位和理論價值作嘗試性解讀。
二、從符號二元論到社會符號學
社會符號學的解釋力來自于言語的意識形態性和社會性,它發端于索緒爾(Saussure)的符號二元論和語言社會觀,經由葉爾姆斯列夫(Hjelmslev)的語符學(Glosssematics)以及奧格登和理查德(Ogden & Richards)的“意義三角”理論,把符號的指稱意義和情感意義以及符號的生產、接受及其符號-語境(sign-situation)納入符號的意義圈,符號的意義不再局限于社會團體的集體意識,它還突出了符號使用者的主體地位,符號在傳播過程中的增益和虧損同樣也納入符號的意義循環之中,意義的研究從符號的內部運作走向意義的功能性和社會性。然而,奧格登和理查茲對語言語境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交際的情景語境,而沒有涉及到語言使用者的文化語境;盡管注意到了語言的多功能性,但是他們對語言功能的劃分過分依賴情景語境的作用,不僅繁雜且不全面;另外,他們對語言的語境以及它與語言的意義之間的關系沒有作系統、深入的討論。韓禮德(Halliday,1978/2001)辯證吸收了巴赫金(Bakhtin)的符號意識形態性以及言語體裁的概念(胡壯麟,1994)和伯恩斯坦的語言社會學思想,構建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社會意義理論(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來闡釋語言在社會中的運行機制,以考察語言的生產、傳播、接受、交換等過程,強調從社會維度解釋語言的變異和變革。韓禮德認為,符號學研究的對象不應該是抽象、孤立的符號,而是符號系統,是對意義的研究。他(Halliday,1978/2001:108)提出了社會意義理論的六個成分:語篇、語境、語篇變體或者語域、語碼(伯恩斯坦意義上的語碼)、語言系統(包含語義系統)和社會結構,并把社會結構看作是構成“文化現實”的一個意義系統,經由文化語境、家庭關系系統、社會等級系統介入語言交際之中,從而影響著意義的生產與傳遞過程。通過這六個成分,語言意義的生產就不僅僅是結構主義符號學所倡導的封閉的、自治的過程,相反,意義從符號體內部和符號的組合關系擴展至小句及語篇并延伸至社會系統,符號具備了意識形態性。依據巴赫金/沃羅希洛夫(Bakhtin/Volosinov)的符號觀,符號和意識形態之間是辯證統一的,“符號所到之處,都有意識形態的身影,反之,任何意識形態的事物都具有符號價值”(Volosinov,1986:9-10)。即是說,言語符號作為交際的媒介,產生于被社會建構的個體之間(而非自然人),因而被意識形態化,從而使得韓禮德的語言思想具有了一定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性,二者都“堅持把話語作為真實的語言-言語(language-speech)現象和社會意識形態結構”(Volosinov,1986:97;胡安奇、曾蕾,2014)。由此可見,韓禮德(Halliday,2003:2)的社會符號學對言語意義的解讀是多維度的:“意義系統是一個四維復合體,它包含意義性、社會性、生物性、物理性:意義在社會中建構,經由生物學方式激活,通過物理途徑而被交換。”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韓禮德的社會意義學并沒有構建一個概念化的符號體系,這一任務是由霍奇和克雷斯來完成的,他們(Hodge & Kress,1979/1993,1988)依據巴赫金的話語的意識形態論和對話理論、本維尼斯特(Benveniste,1966/1971)的主體間性思想和韓禮德的社會意義學等思想,對結構主義符號學進行社會符號化的建構,提出了一個較為完善的社會符號學模型。
霍奇和克雷斯的社會符號學的出發點是承認個體意識(consciousness)的物質基礎和意識形態性。但是,這里的意識形態指的是社會意義在特定社會階層或者群體所呈現出的不同的功能、取向和內涵,那么,控制著不同階層對社會意義的差異取向的控制機制被稱為話語控制系統①(logonomic system),它是一套社會符號行為控制原則,對意義的生產和接受的條件和過程起到限定作用。另外,話語控制系統本身也屬于意識形態復合體的一部分,它要么服務于統治階層的權威和要么代表著被統治階層的抗爭,因而實現的是社會權力關系,反映的是社會階層內部和階層之間的權勢關系(power)和聯結(solidarity)功能。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伯恩斯坦的語碼也屬于話語控制系統的一部分,它們都是話語在社會實踐中的規制原則。對于社會符號學研究來說,符號的這種社會意指功能屬于符號的符指層(semiosic plane),也即語言作為社會過程在社會中的建構和交換,顯然,符號的符指層所指涉的是意義的社會生成系統。另一方面,符號的所指意義在社會符號學中屬于它的模因層(mimetic plane),指涉符號系統的外部世界。在社會符號學研究中,人們較多關注符指層,也即符號意義的社會功能,在具體的話語實踐中,它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元符號(meta-sign)來表達,比如,口音、詞匯、句法、語體風格、文化等來實現社會關系中的差異性和同一性,也即話語的權勢和聯結功能。簡而言之,社會符號學堅持以意義的社會性為基礎,突顯的是語言的社會符號性和社會建構性。
三、作為社會符號的語碼
依據社會符號學的基本觀點,語言是社會符號系統的一部分,言語行為屬于社會過程,語言的意義不僅產生于“形而上”的內部規則系統,它還具有一個“形而下”的“器”——社會階層關系(class relation),因為社會勞動分工下的階層分化必然導致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和社會控制系統,而語言則成為權力的生產與再制系統中最為有效的符號形態(Bourdieu,1991:164)。伯恩斯坦畢生致力于探索知識、話語在不同社會階層中的差異呈現和使用,從而塑造和建構不同的知識結構并維系社會關系的再生產,語碼的概念貫穿于他的社會語言學理論和教育話語理論的始終。通過語碼的社會符號化,伯恩斯坦把話語、意義、語境、社會階層、家庭角色、教育控制、社會變革、文化傳遞這些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的基本思想有機聯系起來,并最終把它們歸結為“社會關系”系統網絡下的權力分配和社會控制體系。從社會符號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在“符指層”,也即語碼的語義系統,還是在“模因層”,也即語碼所指涉的社會關系維度,語碼均被賦予社會符號意義,發揮著不同的社會化功能。
1 語碼作為規制原則
歷時的來看,語碼的概念和涵義呈現出一個動態演進的過程。起初,伯恩斯坦根據不同社會階層的語言使用模式區分出兩種語言變體:公共語言(public language)和正式語言(formal language),前者為工人階級兒童所熟悉,后者經常出現在中產階級家庭,二者的區別主要在詞匯和語法表層。為了挖掘不同語言使用模式背后的社會根源,伯恩斯坦使用語碼這個概念探索語言的編碼取向、言語變體跟語境及說話人的社會地位之間的關系,進而把前者抽象為局限碼(restricted code),后者為曲闡碼(elaborated code),語碼進而被看作“是在不同社會語境下控制話語實現的規制性原則”(Bernstein,1971/2003:9)。但是伯恩斯坦注意到,工人家庭的孩子盡管比較熟悉局限碼,他們完全可能在特定語境下使用語法結構復雜的曲闡式語言變體,那么,語碼跟特定情景下的言語變體關系如何,二者如何區別?伯恩斯坦在語言學家韓禮德和哈桑的研究中找到了答案。首先,哈桑對語篇銜接與連貫的研究把傳統的意義研究從小句內部提升到語篇層面,意義從詞匯、小句走向小句復合體及語篇本身,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上下文語境和語言的使用環境,語言的意義和語境緊密結合在一起,這也就克服了伯恩斯坦早先試圖僅通過對特定言語使用的微觀描寫推導出語言變體的宏觀特征的研究困境和誤區。對此,伯恩斯坦(Bernstein,1971/2003:10)毫不掩飾他對哈桑的感激之情:“實際上,如果我早點意識到她(哈桑)早期著作的社會學意義,我也不會作出一些讓我們的研究陷入死胡同的決定了(而這些都是我個人的責任)。”語境思想的引入對后期語碼理論的發展具有決定性 作用。基于此,伯恩斯坦劃分出兩種意義序列:語境依附型意義(context dependent meaning)和語境獨立型意義(context independent meaning),前者具有個別性,后者具有普遍性。對于個別性的語境依附型意義,語碼的規制原則相對隱晦,而對于普遍性的語境獨立型意義,語碼的規制原則較為明確。其次,伯恩斯坦借鑒韓禮德有關語言功能的研究成果,把語碼跟語碼變體的社會功能和意義挖掘出來。韓禮德認為,兒童使用語言實現七大功能:工具功能、控制功能、個體功能、互動功能、啟發功能、想象功能和信息功能,伯恩斯坦則根據兒童社會化過程中的基本社會化情景把它概括為四大功能:控制功能、教導功能、人際功能和想象功能。語碼在具體語境中體現為不同的言語變體,實現的是語義功能,語碼的涵義同語言的社會功能和價值結合在了一起,成為“控制四大基本社會化情景中的語言實現形式的規制性原則”(Bernstein,1971/2003:11),它在語言表層句法實現形式的規制力表現在兩個方面:限制性(restriction)和闡釋性(elaboration),前者通過限制性的語碼變體實現,后者通過曲闡性的語碼變體來表達,語碼是潛在于語言變體背后的制約性規則,相當于語言的深層結構,位于語言的語義層。
那么,語碼的規制力何來?伯恩斯坦的實證研究表明,個體社會化過程中的家庭和學校以及他們所在的社會階層和社會關系都對話語的實現形式產生重要影響,個體通過社會交際過程塑造社會角色,因而,在伯恩斯坦看來,角色(role)是一個復雜的編碼過程,它不僅控制著意義的創造和組織方式,還制約著意義的傳遞和接受。社會關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言語的詞匯和句法的選擇,因此,語碼或者語言形式本身就是社會關系的映射。伯恩斯坦(Bernstein,1971/2003:104)用下圖來闡述社會關系、語碼和語言實現之間的交互關系:

圖1 語碼、語言形式、社會結構關系
如圖所示,社會結構在言語活動中居于決定性地位,它通過社會關系形態決定著語碼的語言形式,同時它還在心理層面制約著交際的走向,進而創造出不同的意義秩序,并通過不同的言語事件呈現出來。由此可見,伯恩斯坦對語言的社會學研究雖然受到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薩丕爾(Sapir)和沃爾夫(Whorf)等文化人類學家的影響,但是他絕不是一位語言決定論者,相反,對于他來說,社會關系決定著語言的使用,社會關系模式或者說社會結構形成不同的語言形態,也即語碼;反過來,這些語碼“本質上傳遞文化并且制約人的行為”(Bernstein,1971/2003:96;丁建新,2016)。語碼對言語行為的規制力的根源就在于社會階級及其背后的社會關系,對于此,伯恩斯坦(轉引自Hasan,2009:143)直言不諱:“毫無疑問,從社會學角度來說,對社會化過程具有決定影響力的是社會階級。”至此,伯恩斯坦的語言學社會學中的語碼初具雛形,作為語言語碼,它更多地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對不同社會階層所呈現出的語言模式的差異具備實證主義社會學的一般解釋力,但是它還不具備符號的內部結構形態和意義生成機制。同時,社會關系的規制力絕不只限于一般言語活動之中,它存在于語言社會化過程的各個階段。伯恩斯坦創造性地把社會學研究中的家庭結構、社會控制與人類學研究中的交際過程、符號結構跟語言語碼結合起來,語碼的規制力通過語言結構轉化為選擇(selection)和整合(integration)功能,在特定的語境下體現權力和社會關系,通過家庭和學校教育等形式,塑造心理結構并傳遞文化,這就為語言語碼到教育語碼的過渡作好了理論準備,同時也為賦予語碼這個抽象概念一個具體的符號結構和成分關系奠定了語言學、社會學和符號學基礎。
2 語碼作為符號控制
伯恩斯坦借鑒涂爾干的《社會分工論》,尤其是他的社會團結理論,把教育作為“社會事實”和獨立的系統,從制度性和結構性方面對教育話語和教育傳遞作結構主義社會學的分析,推導出教育話語的規制原則(也即語碼)的內部結構。可以說,分類和架構構成了伯恩斯坦教育語碼理論和教育話語理論的核心,同時也為語碼的符號化提供可能。簡而言之,分類指的是社會分工下的不同范疇之間的關系,分類的強弱反映不同程度的社會分工以及社會階層關系;架構反映的是社會關系對交際規則的控制。就學校教育來說,分類和架構是用來區分不同教學內容之間的隔離(insulation)和邊界(boundary)的程度。相應地,分類就是“內容之間的邊界維持程度”,它不指代具體的教學內容,而是內容之間的關系和內容之間的差異程度(Bernstein,1975/2003:80)。分類可以理解為對教育知識分工的程度,反映教育信息系統中大綱的基本結構。架構用來描述教師和教授內容之間的特定教學關系,體現的是“教師和學生對教授和習得的知識的選擇、組織、進度以及時間的控制程度”,它反映教學內容和非教學內容之間的邊界(Bernstein,1990/2003:85),架構則決定著教育信息系統中教學的基本結構。分類和架構的強弱整體反映著社會控制的程度。在強勢分類和架構下,學科內容之間彼此獨立、邊界明晰,教學內容結構穩定,選擇單一。反之亦然。因此,語碼在一般意義上可以理解為分類和架構之間的張力。據此,伯恩斯坦(Bernstein,1996:29)把教育語碼的這一機制用符號的結構形式描寫如下:

圖2 語碼的符號結構
公式中的E代表占主導地位的曲闡語碼取向(elaborated orientation),+和-代表分類和架構的強度,i指對內部關系的分類或者架構,e指對外部關系的分類或者架構。隨著C和F的強度變化,我們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教育實踐模式。教育語碼反映的是教育話語及其各種實踐形式在社會建構中的潛在規則,通過它我們可以理解知識系統如何成為人們意識的一部分,從而揭示不同的教育話語模式所隱含的符號控制過程。伯恩斯坦根據分類和架構的強弱劃分出兩大類教育知識語碼變體:集合語碼(collection)和整合語碼(integrated),前者分類和架構強勢,后者相反。在此基礎之上,伯恩斯坦劃分出兩種教育傳遞模式:顯性教育實踐(visible)和隱性教育實踐(invisible)。教育語碼對教育實踐產生不同的規制力,塑造不同的教育話語體系并創造出特定的知識結構和社會秩序。也即是說:“分類與架構根據不同的規則建立編碼程序,塑造心靈結構。但是,特定的分類和架構背后是權力關系和基本的社會控制原則。因而從這個角度來說,分類和架構具現權力與控制,因而形成特定的社會關系模式并繼而產生不同的交際形式。這些交際形式必定但不一定最終塑造心理結構。雖然權力維持分類(也即物體間的隔離、邊界,無論是個體的內部關系亦或是外部聯系),它也可以通過不同程度的架構來實現。架構管控互動,且經常處于在場……架構力度規制社會化的模態。”(Bernstein,1975/2003:10-11)
作為符號化的語碼,它所蘊含的符號權力體現在對范疇的分類上,是一種范疇間的關系,比如,性別、群體、階級、種族、概念等,體現的是各范疇分類之間邊界的強弱程度及合法性,其目的是建立合理的關系秩序。語碼的控制力用于維系不同范疇內合理的交際形式。因而可以說,分類和架構為語碼賦予了穩定的內部成分關系和符號結構,借此,權力和控制這兩個社會學要素自然地進入教育知識話語體系,語碼完成了從語言語碼到教育語碼的轉變,同時具備了社會符號的基本特征。
四、語碼的社會符號學意義及其理論價值
從語言語碼到教育語碼,語碼不斷被抽象化、概念化、結構化并最終符號化。然而,語碼的符號化是以個體意識的物質性和集體意識的意向性為基礎,建立在一個基于社會分工的社會語義系統之上,因而也就避免落入索緒爾結構主義符號學的意義孤島,使其具備豐富的社會符號學價值和意義。如此一來,伯恩斯坦語碼理論的核心關懷可以歸結為社會關系結構在符號交際中是如何被差異表征的。顯然,這里的差異不在于語言系統的區別,也不是韓禮德語言學所說的語義潛勢的不同,而是不同社會關系在話語中的投射,其本質為符號的中介功能。語碼的這一社會符號學屬性對于伯恩斯坦的整個社會學理論來說至關重要,它直接開啟了伯恩斯坦與系統功能語言學長達半個世紀的對話與合作,語言學和社會學以最自然、貼切、深入的方式走到了一起,英國的社會學研究因而變得熠熠生輝,韓禮德的系統功能語言學也因獲取了充分的社會學營養而光彩奪目(胡安奇、王清霞,2014)。對于此,美國社會語言學家庫爾瑪斯(Coulmas,1975:5)曾評價道,盡管言語(speech)創造不同的群體,并在各個亞群成員之間起到中介調和(mediation)的作用,但是社會學理論卻極少關注語言,哪怕是涂爾干(Durkheim),韋伯(Weber)和帕森斯(Parsons)也只不過是把語言作為社會的基本現實;即便是舒茨(Schütz,1965)從人種學研究的角度提出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的概念亦或是哈貝馬斯(Habermas,1985)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他們也只是從高度抽象的層面探尋社會交往得以可能的條件,唯有伯恩斯坦和格雷姆肖(Grimshaw)等極少數社會學家的研究是建立在現實言語材料之上,語言被賦予符號中介的社會建構功能。在這一點上,伯恩斯坦深受符號互動社會學家米德(Mead)和社會-文化心理學家維果斯基(Vygotsky)的影響,把話語方式同民族心理和社會結構聯系起來,語言成為調和思維、現實、文化的中介。誠如哈桑(Hasan,2005:150)所言,“語言的中介能力是語碼理論的關鍵……盡管伯恩斯坦沒有使用符號中介這個術語,但是符號中介的思想的確是他社會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在伯恩斯坦的著述中,動詞中介(mediate)出現了至少40次,尤其是在第一卷他對語言社會學的論述中出現頻次高達25次。伯恩斯坦(Bernstein,1971/2003:19)認為:“詞語在情感表達及其所認可的社會認同之間起到中介(mediate)作用,也就是說,價值觀被賦予在情感的言語表達之中。它存在于所有社會,但關鍵的決定因素不一定在于詞匯量的大小,而在于詞語的性質和語言使用的類型,在于語言結構對思維和情感產生多大的中介效果。……語言的結構模式,也即詞語與句子的關聯方式,反映了情感結構的特定形式,繼而反映出交往的途徑和對環境作出的反應。”
伯恩斯坦因而借用歷史-文化心理學中話語作為取向和規制系統的概念用于他的語碼研究,進而把語言同意識發展有機聯系在一起,語碼成為心理發展的社會之線上最光彩奪目的一環,因為“在所有符號形態中,唯有語言藐視時間,具備反思能力,為現實分類,解析可傳達的經驗,協同發出一個文化的不同聲音”(Hasan,2005:134)。由此可見,語碼并非一個抽象的實體,而是一個意義系統,是一個關系的系統網絡,作為社會意義的符號實質上應該是一個包括文化系統和社會結構在內的整個意義系統,社會性凸顯的是符號意義的社會價值,關注的語言與社會結構二者作為社會系統的互動與共變關系。因而,韓禮德(Halliday,1978/2001:88)曾評價道:“伯恩斯坦的社會學是一個關于社會學習和文化傳遞的理論,同時也是一個有關社會維持和社會變革的理論。”
至此可以看出,在伯恩斯坦的整個社會學體系中,語言就像圓心,把言語使用、權力與控制、文化傳遞、社會分工等要素組成一個社會學的圓。對于他的社會學思想來說,語言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它揭示了因勞動分工帶來的階級差異引發的教育不平等,而更在于它打破了傳統的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互相對立的研究模式,相反,語碼理論成功地把語言、意識、社會這三大人類關切有機串聯在一起,進而把教育問題跟家庭、學校、權力分布、社會階層等緊密結合起來,從微觀到宏觀,將語言問題推向符號控制和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的理論高度,使其具備廣闊的應用空間,因而被廣泛使用于教育話語分析及資本主義文化批判。
五、結語
從言語使用到語碼再到話語,伯恩斯坦試圖把語言、傳遞、教學等微觀過程同宏觀形式結合起來,探究教育語碼、教育內容與過程、文化傳遞如何跟社會階級和權力關系聯系在一起的,他“一直致力于發展一個系統的結構主義理論用于描述教育系統與社會分工的關系”(Sadovnik,1991)。確切地說,伯恩斯坦最終是要建構一個涂爾干式的結構主義理論分析勞動分工的改變如何創造不同的意義系統和語碼系統以及這些系統如何分類,并把權力關系的不平等同結構主義路徑整合在一起。從社會符號學的觀點來看,語碼不僅僅是一套言語交際的規制原則,它還是“教育實踐信息系統的規制原則”(Atkinson,1985:136),發揮著符號中介的功能,存在于社會系統之中,實現社會關系的控制和調節功能。正是通過語碼這一社會符號屬性的概念,伯恩斯坦搭建了一座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對話與溝通的橋梁,為我們探究語言、心理、現實三者之間的關系提供新的途徑。
注釋:
①Logonomic是logonomos的派生形式,是Hodge和Kress自創的一個合成詞,由logos和nomos構成。希臘詞logos就是文中提到的邏各斯,含有規則、思想、語言等意義,nomos是指控制機制(a control or ordering mechanism)(Hodge & Kress,1988:4)。
[1] Atkinson, P. 1985.[M]. London: Methuen.
[2] Benveniste, E. 1966/1971.[M]. Florida: University of Miami Press.
[3] Bernstein,B1971/2003.[C]
[4] Bernstein, B. 1975/2003.[C]. London: Routledge.
[5] Bernstein, B. 1990/2003.[C]. London: Routledge.
[6] Bernstein, B. 1996.[C]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7] Bourdieu, P. 1991.[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8] Coulmas, F. 1975.[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9] Habermas, J. 1985.[M]New York: Beacon Press.
[10] Halliday, M. 1975/2007.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Semantic Change[A]. In J. Webster (ed.)[C].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1] Halliday, M. 1978/2001.[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2] Halliday, M. 2003. On the “Architecture” of Human Language[A]. In J. Webster (eds.)[C]. London: Continuum.
[13] Hasan, R. 2005. Semiotic Mediation and Three Exotropic Theories: Vygotsky, Halliday and Bernstein[A]. In J. Webster (eds.)[C]. London: Equinox.
[14] Hasan, R. 2009. Language in the Processes of Socialization: Home and School[A]. In J. Webster (eds.)[C]. London: Equinox.
[15] Hodge, R. & G. Kress. 1979/1993.[M]. London: Routledge.
[16] Hodge, R. & G. Kress. 1988.[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7] Sadovnik, A. 1991. Basil Bernstein’s Theory of Pedagogic Practice: A Structuralist Approach[J]., (1): 48-63.
[18] Schütz, A. 1965.[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 van Leeuwen, T. 2005.[M]. London: Routledge.
[20] Volosinov, V. 1986.[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1] 丁建新.2016.作為文化的語法-功能語言學的人類學解釋[J]. 現代外語, (4): 459-469.
[22] 胡安奇, 王清霞. 2014. 伯恩斯坦語碼理論研究的系統功能語言學途徑述評:以韓禮德和哈桑的研究為例[J]. 北京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 26-31.
[23] 胡安奇, 曾蕾. 2014.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哲學性研究[J]. 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 56-59.
[24] 胡壯麟. 1994. 巴赫金與社會符號學[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 49-57.
[25] 田海龍. 2015. 符號意義的賦予與解讀——社會符號學視角[J]. 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 (6): 1-7.
A Social Semiotic Study of Bernstein’s Code Theory
HU An-qi
Basil Bernstein’s structural sociology theory is built on the notion of code, attempting to explore the main sociological issues within the scope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in terms of social labor division, power and control, pedagogic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etc. Accordingly, code is endowed with both a linguistic and sociological attributes. From a social semiotic perspective, code plays a semiotic mediation role in the social system to regulate the specific social relations in speech activities and realize the regulating and mediating func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and framing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
Basil Bernstein; code; social semiotics; semiotic mediation
2018-03-18
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項目“社會-認知視域下的伯恩斯坦話語理論研究”(GD17XWW09)
胡安奇,講師,博士,研究方向:社會符號學、批評話語分析、認知語言學
H0
A
1008-665X(2018)5-008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