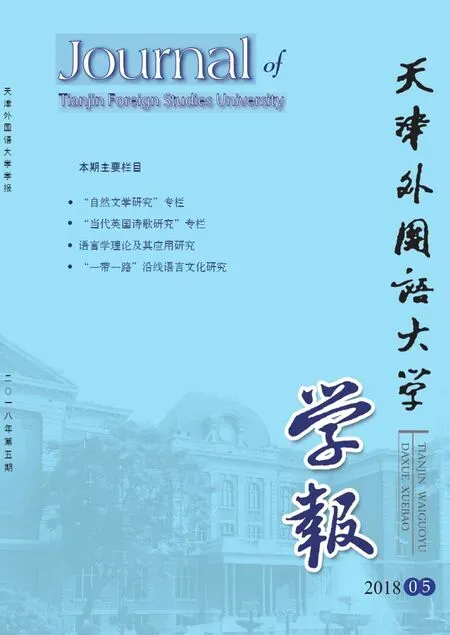學術思想與研究路徑:新修辭學與批評話語分析的異與同
田海龍
?
學術思想與研究路徑:新修辭學與批評話語分析的異與同
田海龍
天津外國語大學語言符號應用傳播研究中心
將新修辭學與批評話語分析相提并論,本身就預示著二者之間存在某種聯系。但這并不等于認為二者相互影響,互為存在的條件,也不是說二者各自的領軍學者彼此有著很通暢的學術溝通。相反,不論是在兩個領域的學者溝通方面,還是在文獻的相互引用方面,新修辭學和批評話語分析各自的生成和發展都沒有留下足夠的痕跡證明它們之間存在過實質性的聯系。然而,當我們跳出這兩個學科的領地審視它們的主要觀點和操作方法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雖然它們產生的地理位置相隔萬里,它們賴以生存的人文環境卻都具有后現代的特征。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我們這些“局外人”看到二者之間存在的聯系。
準確來講,新修辭學在20世紀40到50年代,甚至是更晚一點的60年代(溫科學,2006:35)產生在美國,而批評話語分析則是在20世紀70到80年代產生于英國(田海龍,2006)。地理位置不同,但所處的人文環境正是后現代主義思潮在西方學術界盛行的時期。后現代主義的思想體現在語言學研究領域,突出表現在對結構主義語言學思想的反動,在將研究對象由孤立、靜止和封閉的語言系統轉向活生生的實際運用的語言的同時,語言思想也產生了深刻的變革,其中就包括認為意義不是由語言系統內部各成份之間的相互關系確定,而是由社會主體通過話語事件之間的聯系建構,在這個過程中始終貫穿著權力關系的影響,貫穿著社會活動者的興趣對事實進行的不同程度的折射(田海龍,2014)。非常明顯,語言已不再像一個客觀存在的物體那樣供研究者客觀地審視,相反,研究者更感興趣的是社會活動者如何運用語言這一資源來實現其構建身份、實施影響和參與活動的目的。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新修辭學提出“人類是修辭動物”的觀點,認為修辭不再是演說和寫作的附加物,它的功能也不再僅僅是勸說;修辭是所有人類交往中生來具有的東西,它制約著人的思想和行為,進而影響人們對現實的認識。這種“修辭即認識”的觀點將交際與修辭的過程看作是一個主體互聯的過程,交際的主體通過修辭過程完成身份的話語建構(田海龍,2015)。同樣也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批評話語分析提出話語是一種社會實踐(Fairclough,1992),語言的運用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糾纏在一起,二者不是相關,也不是相互聯系,而是社會就存在語言運用之中(Kress,2011),因而,語言運用建構著語言使用者的社會身份,并幫助語言使用者實現其社會活動的目的。
可見,新修辭學和批評話語分析在后現代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對語言研究的基本問題實現了認識的一致。然而,正像批評話語分析的不同學派在話語與社會的關系由“媒介”建構這一點上達成共識但在這個“媒介”到底是什么這個問題上認識不一一樣,新修辭學和批評話語分析也在主要觀點一致的同時各自有著迥異的操作方式。例如,鄧志勇和胡敏對《時代周刊》和《經濟學人》2008年3月14日發生在我國拉薩的一系列打、砸、搶、燒等嚴重犯罪事件的報道進行對比分析時,運用的方法是新修辭學代表人物伯克(Burke)創始的戲劇主義修辭批評的戲劇五要素分析法(鄧志勇,2011:165-179),而對類似社會問題的研究,批評話語分析的學者則采用其他的研究方法。例如,辛斌對中美主流媒體對南海仲裁案報道的分析就分別采用議程設置的方法(辛斌,2017)和框架分析的方法(辛斌,2018)。
以上研究案例雖然可以說明新修辭學和批評話語分析在具體的研究路徑方面有所不同,但是,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種不同的研究路徑恰好可以佐證上文提到的二者在學術思想上的契合。或許可以說正是這種路徑和方法的多樣才使得新修辭學和批評話語分析有種殊途同歸的默契,使得二者匯合在條條道路都可通達的羅馬。
例如,新修辭學關于交際的主體通過修辭過程完成身份的話語建構的觀點與批評話語分析關于身份通過社會認知的方法被認識的觀點,就有異曲同工之效。在批評話語分析看來,講話者通過對交際語境的主觀判斷,才可選擇適合的修辭策略和方式;而只有講話者使用的修辭手段和方式通過共同享有的理念被認可時,講話者的身份才可完成在聽者方面的建構(van Dijk,2012)。在這里保留,語境是一個關鍵的概念。它不再是事先客觀存在的東西,而是話語活動參與者依據其社會身份實時主觀建構的東西。依據這個觀點,政治家的強勢不是因為他使用了強勢語言,而是因為他使用的強勢語言在聽者那里被認為是具有強勢的意義。換言之,政治家的強勢不是存在于他使用的強勢語言之中,而是通過聽者的語境模式(context model)這類的社會認知主觀構建出來。在這個意義上,新修辭學和批評話語分析采取了相同的認識真理的路徑,達到了學術思想的一致。
綜上所述,有理由認為新修辭學和批評話語分析在學術思想上有高度的契合,其各自熱衷的研究路徑也促成了這些共同的學術思想。
[1] Fairclough, N. 1992.[M]. London: Polity Press.
[2] Kress, G. 2001. From Saussure to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The Turn towards a Social View of Language[A]. In W. Margarte, S. Taylor & S. Yates (eds.)[C].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3] van Dijk, T. 2012. Critical Context Studies[A]. In Hailong Tian & Peng Zhao (eds.)[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4] 鄧志勇. 2011. 修辭理論與修辭哲學[M]. 上海: 學林出版社.
[5] 田海龍. 2006. 語篇研究的批評視角——從批評語言學到批評話語分析[J]. 山東外語教學, (2): 40-47.
[6] 田海龍. 2014. 話語理論與語言符號學——福柯與巴赫金對后現代語言研究的啟示[J]. 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 (5): 14-20.
[7] 田海龍. 2015. 新修辭學的落地與批評話語分析的興起[J]. 當代修辭學, (4): 32-40.
[8] 溫科學. 2006. 二十世紀西方修辭學理論研究[M].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9] 辛斌. 2017. 從議程設置看中美主要媒體關于南海爭端的報道[J]. 當代修辭學, (5): 45-53.
[10] 辛斌. 2018. 中美媒體關于南海爭端報道的框架分析[J]. 外語學刊, (3):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