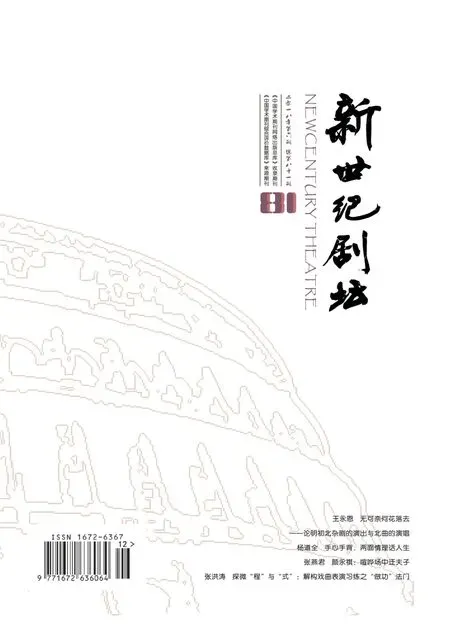默然都不語,應識舞臺情(下)
三、從入行到懂行,從專業到擅長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代表著中國各族人民和各民主黨派人士,高呼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這個時候,不僅是中華民族抗擊外來侵略和民族壓迫的勝利,同樣也是全民族革命的勝利!與此同時,戲劇能夠帶給人民的意義,也在這一時刻產生了更加革命性的體現。
新中國的話劇大量排演了蘇聯的經典名劇。而李默然所在的東北文協文工團,也在1951年10月2日,改名東北人民藝術劇院。此時的李默然,被分配到了東北人民藝術劇院話劇團,成為一名專業話劇演員。
從在郵政局的業余話劇團第一次登上舞臺,到現在成為專業話劇演員,在外人眼中,都會認為這時候的李默然已經是一個十分懂行的表演者。甚至在那個時候的李默然眼中,十幾臺戲近一百多場的演出經歷,也應該是自己已經達到高水平話劇演員的榮譽勛章。可是正如前文說過的,上天為你準備的安排,除了是在幫助你之外,某些時候也許同樣會變成一種阻礙。日后發生的一件重要事件,才讓李默然真正看清,此時的自己只是一個入行的話劇演員,離真正的懂行,還有一定的距離。“真正的坎坷”,才剛剛開始。
當時的劇團,不僅大量地引進并排演蘇聯的優秀劇作,同時也把蘇聯的演劇體系引入到國內,供文藝人員研究學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就這樣被全面介紹到中國來,對當時的國內話劇表演產生了深遠的觸動,至今依舊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伴隨這股熱潮,李默然所在的東北人藝話劇團專門抽出一段時間,組織劇團全體人員認真學習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的理論知識。并在這之后,把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組織排演了一出蘇聯的話劇——《曙光照耀莫斯科》。
《曙光照耀莫斯科》的導演是東北人藝話劇團的嚴正。出生于江蘇南京的嚴正曾在西安的西北電影制片廠工作,后來投身革命,去了延安,在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工作、學習。在延安時期,嚴正就早已在多部話劇演出中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最為出名的就是在話劇《帶槍的人》中成功塑造了斯大林這一舞臺藝術形象。后來,當解放的泱泱大潮席卷東北地區的時候,嚴正也隨著當時東北人藝的前身東北文協文工團,一起來到了這片富饒的黑土地上。起初作為副院長的他主管歌劇團,后來轉而指導話劇團的工作。此時的嚴正,可以說是劇團中少有的在早期就接觸并學習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的人。因為除了李默然等后期加入的工作者以外,早期的老文工團的成員們,在延安工作學習的時候,都跟曾在莫斯科系統學習過戲劇的新中國才女孫維世學習過,而孫維世在莫斯科學習的正是最為正宗和純正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因此,運用斯氏體系排演《曙光照耀莫斯科》,是嚴正并不陌生的一次實踐。
在嚴正的指揮、領導下,包括主演李默然(飾演庫烈聘)在內的所有演職人員,運用嚴格、正規、科學的排演方法,認真進行了劇本分析、角色分析、生活體驗、臺詞研究等步驟后,于1951年3月進行正式排練。
興致勃勃又雄心壯志的李默然跟隨集體開始排練,但是他絕對沒有想到,后面的他將會迎來自己演劇歷史上的第一次磨難!
最初,一切都很順利,在前幾幕幾場的排練中,李默然的表現甚至多次受到嚴正的表揚。被表揚的李默然也堅信自己多年積累的表演經驗是絕對正確的,甚至覺得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的理論學習中學到的知識已經可以充分熟練地運用到排練實踐中。然而有一天,在場上排練的李默然按照以往的經驗,做出了這樣的一件事情:他將劇中的人物“卡碧特麗娜”的名字斷音,自作主張地讀成了“卡碧特·麗娜”。而李默然這樣做的理由,也是他按照以往的舞臺演出經歷,為了達到某種習慣性的戲劇效果而做出的改動。因為他從小接觸到的舞臺演出,包括大量的戲曲舞臺演出,可以追求腔調的改動而達到的美感,往往會引起觀眾的強烈興趣和好評。正當李默然為自己這次改動而“沾沾自喜”的時候,以往總是表揚李默然的嚴正,突然打斷了排練,并冷冷地指正道:“你這就是腔調式形式主義!”
一言既出,舉座皆驚!誰也沒有想到,此時已經是劇團中的“臺柱子”的李默然,這個被稱為“天才”的李默然,那個以往只會被觀眾認可和領導表揚的李默然,會在這個時候出這樣一個“丑”。大家更沒想到,從來都是表揚李默然的嚴正,會突然在這個大家看似都沒有問題的改動上如此較真。
可能是意識到自己的話語對自己的同志重了一些的嚴正,隨后緩和了語氣,認真地從自己打斷排練的理由,以及默然同志這樣做是如何不符合斯氏體系的原因娓娓道來。說得包括李默然在內的所有演員心服口服。從這時起,一直在表演上“順風順水”的李默然,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吃“天才”的老本到頭了,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演員甚至表演藝術家,從小接觸過的戲曲表演模式以及陳舊舞臺、電影的模式應該被置換和修改了。這個曾經“上天的安排”在多年“幫助”自己后,終于還是成為了一種“阻礙”。
那個時候的李默然無疑是痛苦的,因為任何天才都很難接受自己在擅長的領域被突然否定。但是,“傷仲永”真正的“殤”,是在仲永的一生中,沒有一個可以對其進行階段性否定并指導鼓勵的人。一個在日后被時代認可的偉大的人,其初期的奮斗實踐一定是痛苦的,這種人更為厲害的地方在于,從痛苦中解脫并再次向前的速度又是常人無法企及的。李默然就是這樣的人,這樣被時代認可的人。
很快,李默然就從暫時的痛苦和彷徨中走了出來,他再次反思自己的過去,反思自己的表演,反思自己對斯氏體系的理論學習,最終在反復研習劇中人物之后,最終成功甚至可以說是完美地塑造了庫烈聘這個人物。《曙光照耀莫斯科》的演出大獲成功,導演嚴正也因此在演出后,奉調至中央文藝系統任職,后來,又調到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任系主任。
從這次“失意”中,李默然可謂是有了一次脫胎換骨的變化:他不再“迷信”自己過去的演出經驗,不再照搬雖然優秀但并不完全適合話劇表演的傳統戲曲表演模式;而是真正進入到學習和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劇體系的工作中,并讓其作為指導思想在日后的演出實踐中繼續發光發熱。
《曙光照耀莫斯科》的排練,可以說是李默然表演生涯的一個轉折點,這也是先生在日后回憶中承認的自己從入行到真正懂行的重要轉折。而之后的兩部戲——《第二個春天》(1962年)和《報春花》(1979年),對他而言,又讓表演這門藝術,從一個“工作專業”,真正變成了自己“擅長”的一種藝術形式,并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劇理論,形成了真正的自我理解。用先生的總結就是——《曙光照耀莫斯科》讓其克服了“強調式的形式主義”;《第二個春天》讓他明白了什么是演員的“最高任務”;《報春花》則讓他明白了,一個演員在塑造人物的過程中,“對真實生活進行體驗”是多么重要的要求。這三部戲之后,李默然成為了表演上真正的“大師”,無論是《李爾王》中的“李爾”,還是《夕照》中的“父親”,此時的他,可真正地稱之為對于角色達到駕輕就熟的程度。
總結李默然的表演藝術特色,可以用“三化四品”來進行簡單地概括。
“三化”,是指演員的三種最起碼的基本功。第一是“消化”,是指在導演的幫助下,對于劇本的認真消化,真正地吃透劇本;第二是“變化”,是指演員在第一步“消化”之后,要把自己變成角色的同時,讓劇中的角色也變成你,達到自我與角色的真正融合;第三是“融化”,是指在“消化、變化”后,讓觀眾看到舞臺上你的表演后,承認你就是人物,并且承認,這個人物就是你塑造和演出的。
李默然認為,在“三化”的基本功之后,就應該升華為“四品”了,是演員更高一層進步的重要質變。
“四品”,第一是“大江東去”,是指“三化”后的演員應該在表演中擁有自己獨特的符合劇中人物的豪邁的“激情”;第二是“潺潺流水”,是指演員在表演的激情中,不會失去符合劇本和人物性格的細節上的“細膩”;第三是“曲徑通幽”,是指在前兩步的基礎上,達到的一種表演上的“意境美”;第四是“異風突起”,是指完成了前三步并不是重點,應該在細膩又激情的意境美中,凸顯自己的個人風格,這種個人風格,一定要使觀眾產生某種程度上的“驚艷”!
“三化四品”,是李默然整個表演藝術的總結。同時,也讓李默然從對于經典的模仿變為擁有了自成一派的表演理論,甚至后來有人總結默然先生的表演風格用了“李派”來稱呼。雖然在先生自己看來,這套理論特別是對于“旦角”也就是女性角色的塑造上有一定的缺憾,但是正是在這樣的表演方法教育指導下,后來改為遼寧人民藝術劇院的老東北人藝,相繼培養出了大批優秀演員。先生“李派”的表演風格,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沒!
四、急流勇退:陰差陽錯又實至名歸的英雄
默然先生的整個職業生涯,基本都是在舞臺上度過的。這不僅是時代賦予他的偉大使命,同樣也是李默然自己遵從內心的信仰而做出的主動選擇。但是,就連默然先生自己都承認,自己的名字真正被全國人民所熟知,繼而成為一種民族符號和文化符號被宣揚,并不是通過自己的舞臺作品,而是通過《甲午風云》這部電影來實現的。可以說,先生的名氣是靠電影打向全國的。
說起先生與這部電影、與電影中“鄧世昌”這個角色的淵源,真的可以用陰差陽錯來形容。甚至先生在許多場合都會這么說,鄧世昌這個角色,是他“撿”來的。
1959年5月,一部由葉楠編劇的名叫《甲午風云》的文學劇本在雜志《電影文學》上面刊出,引起了眾多讀者的強烈反響。同年8月,在各方領導的努力下,長春電影制片廠擔起了拍攝電影《甲午風云》的重任。隨后,組織決定導演林農擔任《甲午風云》的總導演。拍攝很快進入籌備階段,導演林農也很快決定,請著名的表演藝術家金山來塑造電影中“鄧世昌”這一角色。然而,就在林農的邀請函遞到金山手中后,眾人才得知,金山另有工作安排,無法按時出演鄧世昌這一角色。這下眾人措手不及,最有“資格”的演員在關鍵時刻被工作纏身無法到來,如何是好?就在眾人為此感到一籌莫展之際,林農想起了自己早早在遼寧“人藝”“預定”下來的李鴻章的扮演者——李默然。
林農是很欣賞李默然的,在之前一次拜訪遼寧人民藝術劇院的活動中,遼寧“人藝”作為招待活動之一,就是邀請他觀看了正在演出的話劇《漁人之家》,其中扮演姚努茲·布魯格的演員“給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后來經過多方打聽,林農得知那個演員就是遼寧“人藝”的臺柱子之一,時任遼寧“人藝”副院長的李默然。于是,林農很快找到當時的遼寧“人藝”院長洛汀,希望借用李默然去自己的《甲午風云》劇組,扮演其中的一個重要角色——李鴻章。
本來林農沒有料到自己會成功,因為當時作為副院長的李默然,不僅要負責院中的相關行政工作,同時還要擔負主要演出的責任,因此可謂是劇院中少有的幾個支撐大局的人之一。經常參與選角的林農,自然知道這樣的重要人才資源,無論在哪個劇團都不會輕易放手。但是讓所有人都沒想到的是,沒費多大功夫,洛汀就答應了林農的請求。林農不知道的是,這其中也有另一段淵源。
時任院長的洛汀,曾經在電影演員身上吃過一次“虧”。有一次,遼寧“人藝”在青島演出,計劃本來早已安排就緒。只是沒想到,臨到演出時據說上海將要來一支演出隊伍,遼寧“人藝”當時租用的場地要臨時借調給上海的隊伍。這讓洛汀很生氣,也很不解,雖然作為組織的決定洛汀不得不服從,但是心中泛起嘀咕的他,決定一探究竟。終于,派人打聽了之后的他,得知上海帶來的話劇雖然不比遼寧“人藝”的話劇出色,但是上海帶來的這部戲中的演員,有當時的電影“大明星”康泰。聞訊而來的觀眾當然更希望一睹大明星的風采,主辦單位也只能為了民意而讓步,用“委屈”遼寧“人藝”來實現民眾的愿望。
這件事之后,洛汀很受觸動。當時的他在心中就決定,日后一定在自己的演出隊伍中,培養出像康泰那樣的電影明星,那樣,就不會有人再以此為名“擠兌”掉自己院團的演出了。
沒想到這么快,機會就從天而降。
答應了林農的洛汀,很快就派遣李默然以工作的名義,前往長影出了個“長差”。接受了上級指派的李默然,也背著自己的行囊來到了長春,但此時的他卻還不知道主演金山遺憾缺席的消息。
當身材高大、面貌俊朗的李默然出現在導演林農、攝影師王啟民的面前時,日后被稱為慧眼識英的王啟民立馬起身指著李默然說道:“老林,還找什么鄧世昌,這不就在你眼前嗎?”接著,經過簡單的介紹和了解,李默然這才得知原本定下的主演金山無法來了,而本來被作為李鴻章扮演者的自己,成了新任主演的“繼承者”。
就這樣,李默然成為了鄧世昌的扮演者,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拍攝與制作,電影于1962年上映。而后面先生在影片中的表現,筆者就不用在這里過多贅述了,因為到現在,《甲午風云》中的鄧世昌,都是整整幾代人心中的文化符號。那個時候,觀看李默然出演鄧世昌,已經成為了萬人空巷的情狀。其火爆程度,也許只有22年后的《少林寺》可以與之媲美。但是《少林寺》征服觀眾的,更多的是其動作性的無比優美以及對少林武術的破天荒的展示與宣傳,而《甲午風云》征服那個時代觀眾的,是中國人民在解放二十多年后,心中依舊存在的屈辱感和使命感。他們從鄧世昌身上再次看到了民族的脊梁,從宏觀的角度堅定了民族振興的信仰,從微觀角度明白了人民英雄的偉大與不屈。
此時的李默然,靠著鄧世昌這一角色名揚天下,成為了萬眾矚目的“英雄”。但是先生卻在這個時候,在英雄鄧世昌的光環下,做出了另一個令人“匪夷所思”但卻比他成功完美地塑造了民族英雄這一舉動更加“英雄”的決定。
靠著《甲午風云》紅極一時的李默然,并沒有像很多其他的演員一樣,就此留在了熒幕之上。相反,他卻在眾人驚詫的眼光中急流勇退,像以前一樣,重新將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到了舞臺演出上來。這在當時很多人的眼中是不可思議的事情。現在回想一下,之所以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是因為大多數的人做不到像先生那樣面對名利而不為所動的境界。但是了解李默然的人都會知道,這樣的境界,并不是李默然在一朝一夕中培養出來的。
五、激流勇進:只要信仰真,名利如浮云
在此不想過多地贅述先生在《甲午風云》中的成就,關捷先生所著的《人民藝術家李默然》一書,已經將默然先生參加《甲午風云》的前因后果以及如何塑造鄧世昌講得十分詳細;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筆者想通過描述先生參加電影演出前后的表現,來讓大家看到一個在藝術上真正能夠做到“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園、完善自己的道德操守、永不舍棄戲劇情結”的大丈夫、大演員的形象。
前面說到了默然先生在演出《甲午風云》后,選擇了急流勇退。其實了解李默然的人都明白,這樣的選擇看似偶然,其實是一種必然。
現在的戲劇界,不乏有許多身兼編、導、演數職的“大家”。他們有的只是初出茅廬的“新青年”,有的則已經在戲劇演出圈子中有了一定名氣。在演出《甲午風云》前的李默然同樣也曾嘗試過表演以外的工作——1953年嘗試導演話劇《婦女代表》、1959年嘗試編劇話劇《海邊青松》。而其中的《海邊青松》,還曾經獲得過當年文化部的編劇大獎。誠然,無論以現在還是當時的眼光,在外人看來李默然的這兩次改行應該算是很成功的。但跟現在不同的是,李默然并沒有因為這兩次在外人眼中成功的“轉行”,就此走上了身兼“數職”的道路。反而是在每一次的轉行后,都會在思考一段時間后,對自己的同事和朋友們公開表示,自己再也不會做這一行當的嘗試了。
是李默然“妄自菲薄”嗎?在筆者看來不是,這恰恰是先生有著強烈的“自知之明”。他真正明白“術業有專攻”這一亙古格言的深切含義,同時也能真正認清、明白自己的天賦之才應當用在什么地方。
如此說來,這兩次的“轉行”及其結局,在先生的一生中,應當被認為是兩件比先生成功塑造了鄧世昌這一角色還要偉大、還要重要、還要值得載入史冊的事情。因為自古以來,能有自知之明已經是十分難的事情,而作為一個表演天才,一個在那個年代就是大家眼中公認的優秀表演藝術家,擁有自知之明更是難上加難。比難上加難更難的則是,出演鄧世昌讓先生真正名揚天下、“火”得“一塌糊涂”后,先生依舊信守著當初心中的信仰和默默許下的誓言,真的在自己去世前,沒有再擔任過任何除了演員身份以外的戲劇職能。
當然,李默然能夠做到如此放平自己對待熒幕的心態,也跟他在嘗試了電影之后,做出的對舞臺和熒幕的總結有著很大的關聯。他認為,相對于熒幕表演,自己之所以對舞臺表演更加難以割舍,是因為在他眼中,雖然兩種藝術門類都是無法消除“遺憾”的表演藝術,但是,把演員和觀眾用一道熒幕隔開的影視演出,呈現在觀眾面前時是非現場性、非直觀性的,讓這樣的呈現跟擁有著連貫性、現場性、直觀性的舞臺藝術相比,演員能夠將“遺憾”降到最小的能力微乎其微——當影視通過熒幕或者電視機播放后,演員在劇中的表演就此定型,無法再進行改動——而對于舞臺表演藝術,由于其不同于影視的呈現特性,演員則可以在不斷地重復演出中修正表演中的“遺憾”,盡可能地將這種“遺憾”降到最低程度,盡可能地把每一次與觀眾的相見都做到比上一次更“完美”。可見,表演藝術在先生心中,是一種應該盡可能追求完美的藝術形式。而先生自己,也是一個力求在表演上盡可能完美的、擁有崇高職業信仰的偉大藝術家。
如果說上述兩件事情,可以體現出本節開頭對先生“固守自己的精神家園、完善自己的道德操守”的總結,那么在“永不舍棄戲劇情結”這一定位上,先生的所作所為依舊值得我們后人深思。
在幾年前很長的一段時間中,中國的戲劇市場,是不斷走著下坡路的。而就在那個時候,比李默然輩分年長的前輩紛紛去世。和自己同齡的戰友也紛紛由于年老體衰,不再擔任或者顧及跟戲劇有關的事情。就連比李默然晚上幾輩的年輕演員,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也紛紛放棄戲劇舞臺——要么轉行,要么走上影視道路。甚至有段時間,“戲劇工作者”被看做是一種沒有什么“出息”的職業。
看著周圍的人紛紛“急流勇退”,看著當下的話劇市場如此破敗,當年在“鄧世昌”之后選擇急流勇退的李默然,卻在這個時候、在自己的晚年,再次做出了一個和周圍不一樣的決定——激流勇進。
功成名就后的李默然,成為了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看著當時日益萎靡的中國話劇市場,年逾古稀的李默然,開始為中國戲劇(話劇)的復興而奔走呼告。他首先為了給協會籌錢而接了自己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影響全國”的電視廣告,讓廣告商把代言的所有收入,全部打入了戲劇家協會的賬戶。緊接著,鑒于西方有著完善的表演理論體系,為了讓中國人有著自己真正成系統的表演理論體系,他親自聯系各大一流戲劇院校和專業院團,聯合徐曉鐘等知名表導演準備開展一場旨在研討中國自己的表導演理論體系的大型研討會。由于種種原因,這次研討會無疾而終,沒有達到先生組織這場研討會的初衷。而當不久后,李默然再次想要重新組織中國戲劇戲曲表導演理論體系的研討會時,先生卻在北京的家中駕鶴西去。可以這樣說,直到默然先生去世前一天,他都沒有脫離研究和進行與自己相伴一生的戲劇舞臺工作。
先生這一生,一次急流勇退,彰顯了其作為一名真誠的戲劇人不計名利堅守信仰的高尚情操;一次激流勇進,展示了先生不為了戲劇一時的頹喪而放棄自己畢生信仰的堅貞情懷。其信仰之真,該令當下許多以戲劇混日子的人汗顏。
六、后記
“默默離去,黃鐘大呂蕩回聲。”(李龍躍詞)任何人的肉體都是暫時的,無人例外。但是偉大的人去世后,他的肉體雖然消失,但是他最寶貴的財富——偉大的精神,對后人的影響卻是永存的。默然先生雖然離我們而去,但是他的經歷和他的精神,就像一曲回蕩在戲劇人耳邊發人警醒又無比神圣的黃鐘大呂,直到現在都可以作為我們戲劇人研究的實際范例和瞻仰的行為標范。
愿先生在天之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