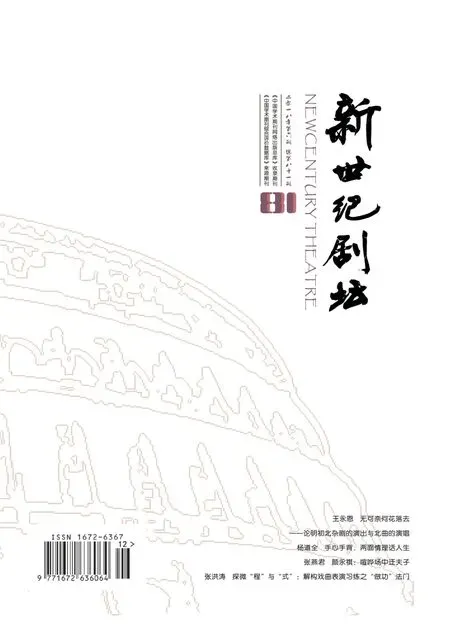從敘事學角度淺析話劇《暗戀桃花源》
《暗戀桃花源》是賴聲川1986年導演的話劇作品,在臺灣首映后大獲追捧,成為中國話劇史經典之一,已經在海內外巡演數場,也曾被各劇種改編,每一種都十分受歡迎。《暗戀桃花源》的成功并非建立在營銷或是“明星噱頭”之上,而是用獨特的戲劇敘事話語對整部話劇進行現代重塑,利用戲中戲結構融合現代與傳統,利用優秀的場面調度進行多時空敘事,憑借獨特的敘事風格征服海內外觀眾。
《暗戀桃花源》(本文根據話劇《暗戀桃花源》1999年的重塑版本進行文本分析)講述兩個毫不相干的劇組(“暗戀”和“桃花源”)因為誤會用了同一個彩排場地,演出在即,只能共用一個舞臺排練。《暗戀》是一出現代愛情悲劇:男主人公江濱柳和女主人公云之凡因戰亂分別,后雙赴臺灣卻彼此不知,四十年后,江濱柳彌留之際,通過登報方式尋找云之凡,最終二人相見,卻已是人顏老去,物是人非。《桃花源》則是一出古裝喜劇,背景是古代武陵,漁夫老陶發現妻子春花與房東袁老板有私情,被逼無奈出海打魚,歷經千險,誤入桃花源,遇到長相酷似春花和袁老板的夫妻,三人度過美好時光后,老陶回到武陵,發現老婆與袁老板認為老陶已死,二人再婚生子,生活充滿矛盾。除了以上兩條故事線索,還有另外一條游離在兩個劇組故事之外,源于現實生活之中的線索:一個衣著怪異的年輕女人亂入全場,尋找她的情人劉子驥。導演利用三條毫不相干的線索彼此打斷,重新解構,創造出新穎的戲劇結構,碰撞出大創作,從故事的整體來看,兩個劇組一邊相互打岔,一邊因臺詞意外洽和,彼此串場,導演用不同時空中人物豐富的戲劇語言,創造不一樣的矛盾沖突,現代與傳統、夢境與實際、悲情與歡喜、理想與現實、幻覺與真實的碰撞,看似復雜卻又清晰地印證導演苦戀、思鄉、尋找的主題。
一、“找尋”主題下的多線索悲喜結構
從整部劇作來看,《暗戀桃花源》是一部融合多主題、多線索的套層結構,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戲中戲”結構。但與普通的戲中戲不同,該劇戲中含兩戲,并且是毫無瓜葛的兩個劇目,導演巧用同一舞臺排戲這一“癥結”設置矛盾沖突,運用道具、臺詞、演員表演將兩戲串在一起,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全劇共有三條線,一條是“暗戀”劇組內部線索,一條是“桃花源”劇組內部線索,一條是現實的外部線索(包含瘋女人、舞臺爭端、導演講戲等情節)。整部劇又是以演戲-搶舞臺-各自拍戲-一起拍戲-劇終順序時間進行,所以從敘事結構來講,還可看作開放式結構。
《暗戀桃花源》(1999年版)共15幕,由現實情節線索打斷兩個戲中戲進程,為了實現間離,也為實現連接,為故事時空跳脫埋下伏筆,這種“打岔”是一個承上啟下作用,可將兩個劇情毫無關聯的戲劇文本拼貼在一起,創造出宏大敘事結構,因此,該劇廣闊的結構枝椏可被分為:1.劇組外部矛盾;2.劇組內部矛盾;3.戲中戲《暗戀》;4.戲中戲《桃花源》;5.怪女生尋找劉子驥五部分,表達近似的主題:找尋。找尋合理的解釋,找尋丟失的愛情,找尋遺忘的回憶,找尋人們心中的極樂之地和理想追求。
布萊希特特別強調話劇的抽離感,他認為,演員應當時刻保持自身感情獨立,演角色但不完全成為角色,同時,觀眾也應從沉浸式觀影習慣中解放,有充分的審美自由。《暗戀桃花源》現實情節部分即是創造這種間離感,不單是演員與角色,演員與演員之間,也存在于角色與觀眾之間。導演利用復調結構,將雙方劇組相互打岔制造出的虛實迅速切換,將劇本、演員、觀眾以異態割裂,創造觀眾與演員、觀眾與角色、演員與角色的多層互動,打破觀眾被動接受的傳統效果,讓觀眾從兩條戲中戲線索中抽身,不斷提醒觀眾正在排戲,形成間離感,引發觀眾對舞臺呈現的思考。這是一種弱化戲劇沖突的方式,與開放式結構淡化戲劇沖突的特點相一致。這樣,觀眾不至于在觀影過程中有疲憊感,不會因線索繁復感到顧此失彼,可以將注意力有效分解至戲中戲上。
作為戲中戲,兩個故事則雙雙采用強調明顯、有力戲劇沖突的閉鎖式結構,從故事接近高潮的部分開端,構成情節線,情節沖突集中發展。賴聲川認為,悲喜劇并不是反義詞,而是一體兩面。《暗戀桃花源》便是對悲喜劇融合的最好例子。《暗戀》和《桃花源》一個是凄美、安靜的愛情悲劇,一個是粗俗、鬧騰的夸張喜劇,二者截然不同卻又強弱互補、平衡,彼此不喧賓奪主又相得益彰。這種一體兩面貫穿話劇始終:戰亂上海和和平臺北,下游的武陵和上游的桃花源,云之凡與江濱柳的關系疏遠對比,老陶前后性格和心境變化等等,這種對照結構在兩劇最后仍然存在,江濱柳終見云之凡,不失為一種告慰,而老陶看到現實中的春花和袁老板的態度,留下一聲嘆息,黯然離場,兩條河流異源終融,悲喜劇在最后一刻相互轉化。
二、時空交錯下的戲劇互動
與小說相比,話劇在時空表達方面極具特點。戲劇空間包括現實劇場空間和戲劇表演空間,戲劇表演空間又包含直接環境空間和間接心理空間。
《暗戀桃花源》在時空方面跨度大,有人稱“暗戀”是一出“時間悲劇”,“桃花源”則是一出“空間喜劇”。兩個多小時時間,“暗戀”講述了橫跨五十年的愛情,中間穿插各種夢境、想象,“桃花源”利用各類道具、象征手段來助攻空間變換,導演用很多巧妙的辦法實現了異時空事件出現在同一舞臺的想法。
(一)戲劇表演環境空間自由轉換
戲劇表演環境空間即舞臺。由于管理人員安排失誤,兩個劇組只得共用一個舞臺排演話劇,兩劇組由此產生了現實生活矛盾,促發了整體話劇進程,也正是這個失誤,讓“戲”與“戲中戲”可以在同一舞臺實現,也為第十一幕舞臺一分兩半,兩劇組同時使用做鋪墊,整部戲的高潮部分由此產生。導演利用第三條現實線索,營造真實的排練環境,演員入臺下臺隨意,與現實的排演現場相一致,也與“搶舞臺”這一爭端相符合。第三幕云之凡和江濱柳在深情告別時,“桃花源”劇組從幕后走進前臺,讓原本離別的傷感帶上了搞笑的氣氛。還有一次經典打岔,出現在老陶在桃花源與長相酷似春花和袁老板的夫妻二人共度歡樂時光之時,導演利用燈光的明暗來暗示時間的流逝,在燈光一亮一暗時,“暗戀”劇組成員依次出現在后臺,打破了整個戲劇平衡,歡樂時光結束,所有人回歸現實。導演用“強制性”手段來實現表演環境空間虛(戲中戲)和實(現實的排戲過程)的自由轉換。
(二)細節處理塑造心理空間
在第六幕,江濱柳生病不能曬太陽,江太太想將其扶回室內,江濱柳拒絕,而在最后,江濱柳與云之凡最終相見卻又相顧無言,云之凡離開后,江濱柳終于明白,他一直尋找的那份感情只能永遠留在五十年前了,等待五十年卻發現物是人非的悲痛,導演用一盞聚光燈強打在江濱柳身上,把江濱柳照回現實。
作為一出愛情悲劇,“暗戀”整部劇渲染的都是江濱柳對于初戀的思念,戲里的現實生活中與跟他結發多年的妻子江太太始終有難以逾越的心理鴻溝,卻又難以割舍。為了突出這一情感狀態,導演利用夢境實現了對江濱柳心理空間的表現。江太太向護士輕聲抱怨江濱柳與她交流甚少,放起了江濱柳喜歡的音樂,燈光暗,年輕的云之凡上臺,護士和江太太在前排左下和中下位置,以采訪形式回憶二人相識、相知,后排燈光暗,前后形成兩個異域空間,江濱柳隨之凡潛入陰影,一邊是江太太的的現實生活,一邊是江濱柳的夢境。兩個空間是現實與理想的對比,形成2∶2對話模式。一個電話打來,江太太接起電話,江濱柳即將醒來,他站在陰影與明亮的交界處,似乎在愧疚,似乎在猶豫,似乎又不舍,那種躊躇的模樣讓矛盾的心理躍然舞臺。
“桃花源”作為古裝喜劇,在武陵、桃花源兩個時空切換,導演巧妙運用戲曲的綜合性、虛擬性、程式性表演特點:演員有相應的武打動作,音樂有戲曲鼓點,老陶在捕魚過程中有高亢的船歌,有虛擬的劃船、走路等程式化動作來突出情節。一間房,房里有不和的夫妻;一床被,被里有微妙的鄰里;一條江,江里有驚濤駭浪,激流漩渦;一片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這些空間、地域變化都是靠幕布、畫板、被子等道具及演員表演協助完成。同時,空間變化反向影響演員表演。老陶從武陵來到桃花源,被環境同化,當他再返回武陵時是一年以后,儒雅謙卑的他想把春花帶回世外桃源,武陵卻早已不是他離開時的武陵,春花和袁老板再婚生子,本是武陵人的老陶卻被認作從陰曹地府來的異端,來索命的神經病,武陵再也回不去了。桃花源里的烏托邦和“暗戀”里江濱柳的愛情理想有些相似,春花和袁老板對于世外桃源的不理解,就如同江太太他們對江濱柳的心事不理解,最終,所有人都得回歸現實。
三、多元修辭助攻戲劇敘事
整體來講,該劇主要用了借代、雙關、跳脫等敘事修辭手法,尤其是在戲劇沖突明顯,對白多笑點集中的“桃花源”部分中體現最為明顯,以第四幕舉例。
以借代彰顯老陶人性懦弱。在第四幕,“武陵三角”開場,老陶用兩張餅代指春花和袁老板,用刀代指自己。通過對話我們可以看出老陶早就知曉老婆偷情這一現實,為什么買藥買一天?其實就是去幽會。可見內心對于這件事是痛恨的清楚的,但是他對妻子偷情卻無能為力,只能在家沒事找事,把兩張餅代做春花和袁老板,拿餅出氣,這就格外彰顯了老陶的懦弱。
劇中使用雙關豐富劇情。袁老板到春花和老陶家送被子,三人攤開被子,以被為幕,借著欣賞被子的理由,袁老板和春花二人情不自禁在被子里依偎,兩人眼睛望著被子,手上動作豐富,一段雙關語就此展開。在之后,袁老板拿打魚的大小來表達對老陶身體的鄙夷,老陶鼓勵老陶:做人要努力,要有理想,想要得到什么,你就闖進去,把他硬搶過來,你懂我這話的意思嗎。此處實際仍是一語雙關,是在說他自己,要把春花搶過來。
跳脫是戲中人物說話時由于事件發展特點,把話說了一半而不往下說了。第二幕中,老陶和春花鼓動老陶去上游打魚的一段對話運用了明顯跳脫。從中可以體現出二人明顯的棄老陶于生死之外的意思,一唱一和的默契程度更加印證二人出軌關系,老陶個人蒙上了悲情色彩。
《暗戀桃花源》是一部在不斷打岔中完成的經典劇目,他讓觀眾認識到,悲喜劇可以做到渾然一體,兩個戲看似毫無瓜葛,實則殊途同歸,他用戲劇化手法告訴觀眾,人的一生就是喜憂參半的一生,你無法參透別人的內心,就像你內心深處那無人傾訴的孤獨,我們從江濱柳的年輕時代走來,幻想著可以生活在桃花源,遇見江濱柳和云之凡的美好愛情,卻在歲月的浪濤中被各種意外打岔,逐漸放手走散,最終成為生活中的春花和袁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