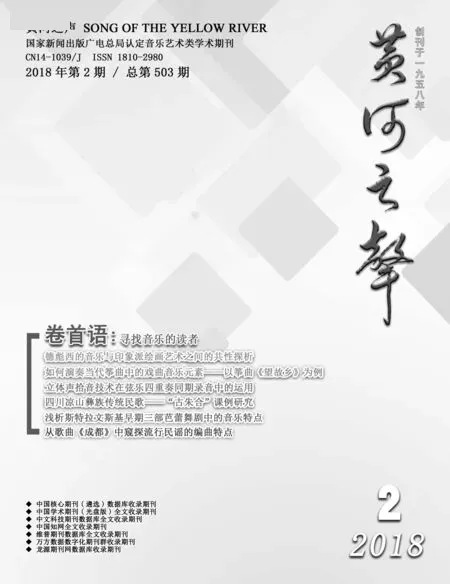淺析抗戰時期上海革命進步音樂積極的影響
張翼飛
(上海大學文學院,上海 200444)
一、抗戰時期上海紅色音樂的產生背景與原因
繼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上海被侵、“七七事變”以來,國家持續處在戰爭與動亂的時局中,上海社會各階層對于戰爭與經濟動蕩,反響巨大,為革命者創造了發展的空間。而在上海的其他戰線,來自文藝界的諸多著名作家夏衍、潘漢年、魯迅等人,積極采用文學的力量展開“對抗”,呼吁并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這是在中共領導下的一個文藝先鋒的組織。“‘左聯’積極介紹馬克思文藝理論和蘇聯作品,宣傳黨的文藝路線和主張,推進革命文藝作品的創作。”[1]以“左聯”發展為契機,一大批在上海的音樂文化工作者,先后成立了“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以及在“左聯劇聯”內成立音樂小組,這些音樂家們,通過自己的才華以及滿懷“同仇敵愾,保家衛國”的激情,投入到革命的音樂創作中去。創作了一大批真正服務于革命實際需要的優秀作品。
二、上海紅色音樂(運動)的現實作用
在抗震時期的上海,隨著“左翼音樂運動”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左翼作家聯盟”在文藝宣傳上的單調性與不足,讓文化與文藝相結合,通過音樂讓老百姓“接觸”革命文學作品,同時,借助文學作品的先鋒性結合音樂充分的表現力,來團結國人反抗侵略的信心。在上海成立的“左翼音樂運動”雖然沒有波及全國,但它在抗戰的大后方得到了長足地發展。為適應革命運動的需要,以任光、麥新、張寒暉、呂驥等一大批革命的作曲家,創作出了一大批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富有斗爭性質的歌曲,為百姓所傳唱‘除此之外,他們還為那些為滿足革命戰爭需要而被創作出來的以革命為題材的電影配樂,使電影情節表達更加符合大眾的需求。
整體來看,以上海社會為基礎產生的“左翼音樂運動”,不僅表達了廣大音樂工作者的愛國情懷,更表現了人民文藝運動的高潮。隨著戰爭的結束與時局的轉變,這一類作家聯盟與音樂運動雖然早已成為歷史,但它們所孕育的一代人、一代作品至今仍然影響著今天的中國。“左翼音樂運動”是在戰爭的催生下產生的革命性質的產物,立足戰爭,為革命服務。在和平時期,革命紅色音樂仍然是教育廣大人民的載體。所不同的是,沒有了硝煙與動亂,然而不變的是,愛國的情懷得到了進一步地延續與發展。
三、黃自《旗正飄飄》、江定仙《新中華進行曲》對于革命的影響
《旗正飄飄》由近代愛國音樂家黃自所創作,這首帶有進行曲風格、四部混聲合唱性質的革命歌曲誕生在“一二八”事變之后。在那個嚴峻的背景下,愛國音樂家黃自繼《抗日歌》之后,又創作出了這一首混聲四部合唱。
這首樂曲是回旋曲曲式風格,基本以4/4拍的節奏,突出每個音節四個時值的強弱關系,增加了樂曲演奏時強弱的對比感;樂曲采用b小調,凸顯樂曲所要表現的對于上海淪陷以及抗日志士浴血奮戰犧牲的悲壯場景。歌詞中的“旗正飄飄,馬正蕭蕭”作為主旋律音節重復出現了三次,將慷慨激昂的主題表現力提高了,雖然歌詞在重復,但是對應的歌曲旋律線條則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三次出現的主部,織體寫法均有變化。六次出現的”旗正飄飄”,寫法不盡相同,力度逐漸增強,使再現部富有動力性。”[2]插部的寫作,分為兩個層次進行發展,第一部分采取領唱為主旋律調性,而在合唱部分為了變現強烈音樂表現了的對比,先后使用了D大調與A大調,大調的音樂表現力較小調來講給人更加高亢的感覺,這種轉調式的寫作手法,不僅體現了黃自對于不同調性旋律協調的把握,而且對第一插部所要表現的人文情懷進行了渲染,無不都凸顯了他精湛的作曲技術。在第二插部,為了與第一插部進行區分,表現多重情懷,采用與之前相對的小調來發展旋律,此部分以e小調為主,來表現國破家亡的慘敗局面以及對于上海淪陷的悲憤情懷。“在插部與再現部之間,齊唱與聲部之間的對話方式體現了由分散到統一的過程,準備了主部的再現,全曲結束時情緒更為激昂、熱烈”[3]。
這首混聲四部曲式,是協奏鮮明革命歌曲,其立足于上海淪陷的緊要關頭,向廣大愛國志士發出的救亡圖存的“呼聲”。歌曲中使用了領唱、合唱、對話等多種唱法,樂曲風格貼近底層老百姓,樸實而又不乏革命上進性。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蠶食上海的危急情況下,這首歌曲的唱響,無意在心理上,鼓舞了我方廣大的人民與抗敵軍,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了日本侵略軍。它謳歌了民族的堅韌不拔,突出了救亡圖存的正面影響。
江定仙——愛國作曲家,學生時代,師從偉大的愛國作曲家黃自先生。電影《生死同心》的主題曲《新中華進行曲》就出自江定仙之手,歌曲中催人奮進的旋律和斗志昂揚的歌詞,不僅表現了“四萬萬”中國人民寧死不屈的節操,還進一步堅定了革命必勝的信心。
這首樂曲從題目上就可以獲知這是一首進行曲風格的樂曲,是一首二部合唱,通過合唱的方式相比獨唱在樂曲的表現力上就有很大差別,作為革命題材的進行曲音樂,只有用過合唱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呼應大眾,激起民族團結的的作用。“全曲旋律分為三個樂段,第一樂段包括兩個相同但結尾不同的樂句,表現“覺醒的大眾”奮勇而起;第二樂段以半音上行級進,表現了人們熱血沸騰”[4],第三樂段的作用是起到主旋律“再現”的作用,呼應主題,重申立場,為全曲收尾。這首樂曲作為一部群眾合唱的作品,歌詞深入人心,歌曲旋律巧妙地展現出人民大眾不懼革命犧牲、奮勇向前的。
通過這兩首作品,不難看出,在中國陷入到戰爭的摧殘中時,那些手無寸鐵的音樂家們依然在為革命“奔走呼號”,雖然沒有直接打擊侵略軍的武器,但是透過大量的愛國革命題材的音樂作品,將“四萬萬”中國人的氣概凸顯出來,表現了我們民族可歌可泣的風貌。
江定仙先生的《新中華進行曲》和黃自先生的《旗正飄飄》都是群眾合唱性的音樂歌曲,所不同的是黃自先生的作品使用了大量不同的音樂歌唱形式,將領唱、問答式唱法以及合唱融為一體;而江先生的作品這幾乎是通篇合唱。雖然表現手段是不同,但是歌曲的表現效果不可小覷,兩首樂曲的題材與呈現的內容,都是以具有革命、愛國為主要特點,同時,兩首歌曲都選用了進行曲式的題材編配,在節奏上更加亢進,突出表現革命志士氣概、國家生死存亡、民族團結同仇敵愾的豪邁場景。所不同的是,這兩首樂曲的寫作時間、背景以及寫作載體也是不相同的,黃自先生的《旗正飄飄》作于日軍進犯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伊始,而《新中華進行曲》是電影《生死與共》所編配的主題曲,盡管所表現的效果與主題都是彰顯號召人民奮勇殺敵,保家衛國。但是,從寫作風格上來說,《旗正飄飄》作為一首混聲四部合唱,其寫作更加自由,旋律線條可以更多地根據曲作者的心緒變化而進行發展,不受限制;而在《新中華進行曲》中,由于該曲是為電影所創作,從而限制了旋律線條發展的自由度,使樂曲的發展緊扣電影情節主題發展的需要,一定程度上削減了該樂曲表現效果。總體來看,這兩部作品都積極地、正面地謳歌了革命志士的光輝事業以及彰顯了民族的尊嚴。
四、結語
在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斗爭中,身居上海或游走于其他戰線的音樂工作者譜寫了大量的謳歌愛國情懷的革命歌曲,極大地團結了中國最底層的勞動人民,鼓舞了在前線奮勇殺敵將士們的士氣,重振國民對于抗戰必勝的信心。同時,激昂奮進的革命歌曲作品也向敵人表現了我們革命志士們的高昂士氣與決心,對敵人的侵略的行徑進行了有力的心里威懾,歌曲的表現大長國人的骨氣與威風,在精神程度上很好地滿足并配合了我軍將士的抗敵、人民團結需求。
此外,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音樂運動”的成功組建與發展,有力的呼應了其他社會團體的革命斗爭需要,相互配合與協作,承擔起抗戰音樂作品創作的重任。“左翼音樂運動”以及其他音樂團體的誕生與發展不僅在戰爭中發揮了在人民精神上的鼓舞作用,更為上海以及國家留下了大量充滿正義、自強不息的“正能量”歌曲。時至今日,這一類作品仍然在發揮著鼓舞大家建設祖國、增強民族自尊心和團結一致的巨大作用。其間接地為中國抗戰勝利、新時期國家社會的發展目標順利實現做出了巨大貢獻。
[參考文獻]
[1]居其宏.百年中國音樂史1900-2000[M].湖南美術出版社,2014,5.
[2]陳志昂.抗戰音樂史[M].黃河出版社,2005,6.
[3]同[2]
[4]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