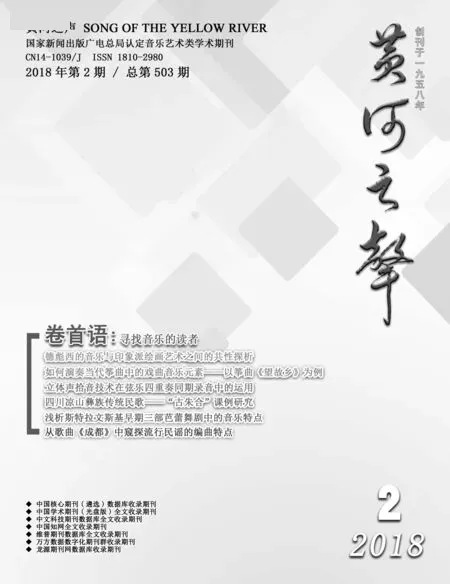草原民歌交響化
——以崔炳元第一管弦樂組曲《內蒙古民歌六首》中《土爾扈特的故鄉》為例
楊 雪
(內蒙古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位于內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額濟納旗蘊藏著土爾扈特蒙古族悠久的民間藝術,這是一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這里是土爾扈特蒙古族歷史文化的搖籃。世代相傳的土爾扈特民歌被民歌專家贊美為“天籟音,空靈曲,旋律美妙……”
一、土爾扈特民歌的藝術特征
由于歷史條件、地理環境、風俗習慣等方面原因,土爾扈特人民在長期的游牧生活中創造出來的獨特的藝術形式。土爾扈特民歌主要是由土爾扈特祖先傳承的古老、原生態的民歌,這些民歌主要以民歌藝人口傳心授的方式傳承。土爾扈特民歌也是土爾扈特長調民歌,長調民歌結構相對自由,其特點表現為歌詞多用兩句式、旋律優美舒展、高低音轉化幅度大等,與其他蒙古民歌的不同之處是在每首歌末尾都有祝辭,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吉祥如意等。土爾扈特民歌反映了土爾扈特蒙古族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有描繪駿馬、親人和草原的,也有抒發思念、祝愿、贊美等情感的。民歌曲調較完整的保留著蒙古民歌五聲調式風格,其調式多用宮(即12356)、微(即56123)、羽(即61235),也有少量的六音、七音調式。
二、土爾扈特民歌《土爾扈特的故鄉》的“交響化”
土爾扈特民歌《土爾扈特的故鄉》描繪的是著名的土爾扈特東歸故事。土爾扈特部作為中國蒙古族一個古老的部落,為尋找新的生存環境于明朝末年離開故土來到伏爾加河下游生活。140年后,由于俄帝國的擴張,其生活受到嚴重威脅,土爾扈特部首領沃巴錫率17萬族人踏上東歸祖國的漫長征程……
崔炳元先在了解這首民歌的歷史背景后,采用新穎的配器手法,使得樂曲在這里變得更為具象。作者在音樂發展中依據音樂情緒的需要,再配器上采用了遞增的手法,使得音響逐步加深加濃加厚。從樂器分布的層次看,由單層次的純音色的功能分組的配器手法逐步過渡到多層次的混合音色的復合功能的配器手法。
樂曲先是由大提琴solo引入主題,深沉的音色、深情的旋律凸顯了土爾扈特部首領率領族人東歸的英雄人物形象,第4小節加入和聲織體以起到襯托的作用,由單簧管、低音單簧管、巴松、圓號、長號、大號和低音貝斯同時進行切分式的節奏型。第14-16小節以樂隊全奏的配器形式結束該段主題,主題旋律由大提琴轉至第一、二小提琴和中提琴的雙八度演奏,木管組與銅管組加強和聲效果,織體厚重、層次分明,深化了東歸主題誓死如歸的情感意境,這里音響上的擴張使人感受到土爾扈特人民堅定的東歸信念。
接著加入音色較為個性的特色樂器英國管來演奏主題旋律,由弦樂組增加和聲以襯托加強旋律的發展,木管組交替式演奏在和聲色彩上作出一定變化,為轉調做準備。第33小節加入小軍鼓演奏,速度發生了變化,木管組和弦樂組用復合音色的方式演奏主題旋律強調了土爾扈特民族長途跋涉中的坎坷和磨難,急促的鼓點則加劇了該民族勇敢、強悍的陽剛品質。第41小節弦樂組開始對之前主題旋律進行補充演奏,第二小提琴連續奏出8個四十六分音符的節奏型以推動全曲高潮的到來。第48小節開始樂隊全體演奏,銅管組開始了主題旋律的演奏,木管組和弦樂組分別在高音區承擔裝飾性的固定音型,裝飾性材料采用和聲式配器手法,在和聲配置上運用了上置法和包置法,某些地方還運用了音色的重疊。這樣濃厚的音色使得音響效果變得強大輝煌,讓人可以浮想到氣勢磅礴的東歸隊伍行走在茫茫的草原中。
東歸的路途歷盡艱辛萬苦,面對嚴峻的環境和氣候,土爾扈特人民并沒有畏懼并堅持到達新的家園。從第63小節開始全曲速度變得稍慢,一段抒情的演奏開始了,先由低沉的大提琴solo引入,圓號和小號演奏八分和四十六分兩種固定的音型來突出旋律。第一小提琴與大提琴交替式的演奏主題變奏材料,采用主題中較有特點的音列進行二度創作的變奏材料表達了土爾扈特人民向往新家園的美好心情。第76小節樂隊再次全體演奏,主題旋律轉由木管組和弦樂組復合音色演奏,銅管組采用和聲式手法來襯托旋律,最后在全體樂隊的和弦長音中結束了全曲。樂曲兩次重復主題之后,迎來一種較為溫暖的結局——回歸祖國的土爾扈特蒙古族在水草豐美的草原上安居下來。從全曲看,作者采取樂器種類和樂器數量增加的手段把一個固定不變的主題旋律由最微弱的音響發展到了全樂隊的強力音響,賦予了這首民歌新的內涵。
三、結語
民歌是民族文化的精華,也是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象征,傳承、發展和創新傳統民間音樂是音樂人的職責所在。崔炳元先生的這首作品把土爾扈特蒙古族傳統民歌與交響樂相交融,對民歌《土爾扈特的故鄉》進行二度創作,提升了歌曲的內涵,增強了藝術感染力,使用西方的配器手法譜寫出土爾扈特蒙古族音樂的民族色彩,達到了傳承和創新草原民歌的目的。所以,在文化產業高速發展的今天,保留原生態的民間音樂資料,遵循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出草原民歌新的音樂面貌,是我們年輕音樂人義不容辭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