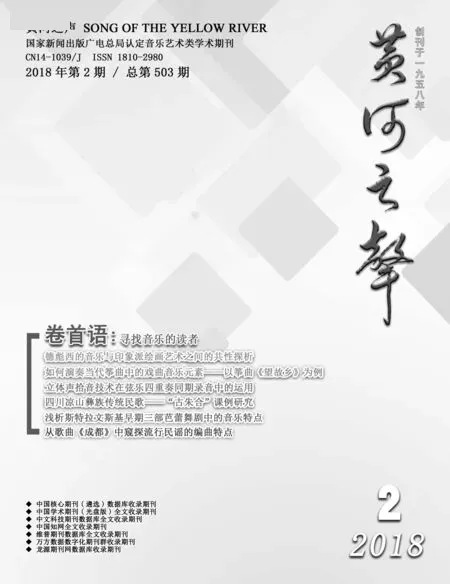由《踏著硝煙的男兒女兒》之于當(dāng)代舞淺思索
龍 敏
(延安大學(xué)魯迅藝術(shù)學(xué)院,陜西 延安 716000)
《踏著硝煙的男兒女兒》就是這種軍事題材的舞蹈創(chuàng)作作品,是在特定的戰(zhàn)爭年代中誕生與形成的,當(dāng)時“英雄主義”的歷史情愫和美學(xué)品格普遍存在于藝術(shù)乃至普通人生活情感之中,這時期所創(chuàng)造的舞蹈充分的展示了大家所熟悉的歷史、革命和護衛(wèi)家園的傳統(tǒng)題材,在這種觀念下創(chuàng)作出來的舞臺呈現(xiàn)出了紅色的記憶,革命的過往。這種以舞蹈的形式去表現(xiàn)特定的社會生活內(nèi)容和塑造具體的人物形象的作品,其內(nèi)容以現(xiàn)實或歷史的、真實或想像的人物和事件作為依據(jù)。在舞蹈的創(chuàng)造過程中客觀現(xiàn)實生活的題材是十分重要的,舞蹈作品《踏著硝煙的男兒女兒》就是反映戰(zhàn)爭素材的優(yōu)秀作品,以對越的自衛(wèi)反擊為開端開始了這個作品的創(chuàng)作。
舞蹈開場,是槍聲四射的激戰(zhàn),戰(zhàn)場上硝煙彌布,負傷的戰(zhàn)士遍地掙扎,救護兵不停地在四處搜索負傷的隊員,一旦發(fā)現(xiàn)了受傷的同志即刻飛奔過去,不管身后的槍炮離自己多近,救人的信念可以讓他忽視掉眼前的一切,穿越彈雨去幫助受傷的戰(zhàn)士轉(zhuǎn)移至安全區(qū)。盡管很艱難,但是她堅持不放棄,身負重傷的戰(zhàn)士不想連累到她而試圖掙脫,卻突然暈倒在地。一朵小花搖曳在了陣地上,只見救護兵歡喜的跑過去摘下了它并送給了戰(zhàn)友,希望以此可以減輕他的疼痛,編導(dǎo)的這一細巧安排,給令人沉重的殘酷戰(zhàn)爭下的低郁環(huán)境增添了些許浪漫主義情感色彩。戰(zhàn)爭還在繼續(xù),戰(zhàn)況不容絲毫放松,受傷戰(zhàn)士經(jīng)過救護兵簡單地包扎,真誠地對救護兵表達了感激與告別,隨后又毅然返身于戰(zhàn)場繼續(xù)戰(zhàn)斗……
從作品的編創(chuàng)技法看來,該作品《踏著硝煙的男兒女兒》中,既用到了西方現(xiàn)代舞的編舞技法又用到了民族傳統(tǒng)藝術(shù)的虛擬寫意手法,并巧妙的將二者進行了揉合。如通過不同肢體動作和空間的轉(zhuǎn)換來營造時空的變化,在同一個舞臺布景中去敘述救護兵對傷員不停歇的搜救過程。在雙人舞中,救護兵與負傷戰(zhàn)士似是而非的“背負”與艱難的前行,火花在女性舍命相救與男性的英雄氣概中摩擦而出,編導(dǎo)將戰(zhàn)士抬手和“輕吻”化作嚴肅的敬禮,將戰(zhàn)士男兒的柔情與鐵漢的堅韌揉合,塑造出一個有取舍有擔(dān)當(dāng)?shù)能娙诵蜗蟆?/p>
藝術(shù)源于生活,許多舞蹈動作的構(gòu)思都是從生活中得到啟示的,如前面提到的“吻別”,就是從生活中得到的細節(jié)。在某戰(zhàn)地醫(yī)院,護士尋問一位傷勢十分嚴重的小戰(zhàn)士最后還有什么要求,小戰(zhàn)士靦腆地說:“長大到現(xiàn)在還沒有女孩子吻過我……”于是,年輕的護士毫不猶豫地上前親吻了他,就這樣,戰(zhàn)士安詳?shù)刈吡耍]有一點點遺憾!生活中的戰(zhàn)士可愛,護士可敬,藝術(sh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
文藝界領(lǐng)域近年來積極倡導(dǎo)尊重個性創(chuàng)作、解放思想、百花齊放的藝術(shù)氛圍,“回歸本體”的舞蹈思潮成為深層的社會主流。這種“回歸本體”的觀念直面?zhèn)鬟_了作品對舞蹈本身藝術(shù)創(chuàng)作、藝術(shù)規(guī)律的一種尊重和推崇,以及對時代過去式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于程式化、僵硬化的有力批判,使自身在該領(lǐng)域業(yè)界占有了一定的“話語權(quán)”優(yōu)勢。這趨勢勢必會引發(fā)整個舞蹈屆內(nèi)從事舞蹈編導(dǎo)創(chuàng)作的人們在題材內(nèi)容的選擇上,重新做一個“意義”的定位和思考。在這樣的大創(chuàng)作環(huán)境氛圍里,如果有誰還照常延續(xù)以往“超寫實”的風(fēng)格方式去反映再現(xiàn)特定的生活場景和人物故事形象,可能就會被大家認作(甚至?xí)行┰S的揶揄)是沒創(chuàng)新、沒想法和過于守舊;再或者有的受眾在觀賞中確實是沒能理解作品的主旨思想,作品到底要表達什么?自己在做一個二度創(chuàng)作的猜測和擴展時,對這些作品“無情節(jié)、無人物、無始無終的舞段”提出內(nèi)容上的疑問,對作品原創(chuàng)編導(dǎo)的用意完全無從追思,可能會使觀者對自身的水平跟不上時尚、藝術(shù)深度不夠等方面產(chǎn)生自卑和自我懷疑。隨著歷史的滾動向前,各個時代的藝術(shù)審美、風(fēng)格、思維模式都發(fā)生相應(yīng)轉(zhuǎn)變。社會群體的心態(tài)和接納度越來越開放和包容,不再呈現(xiàn)對單一特定題材和人物形象的特別青睞,另一方面看來,社會群體審美提高了,其對藝術(shù)作品的創(chuàng)作水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論是何種風(fēng)格、何種流派的藝術(shù)作品編創(chuàng)者,在新的時期里都需重新為自己的選材方向、核心以及外延做一個考量,找到能夠與時代特征和時代風(fēng)貌相接軌的思維情感。咱們之前賞析過的軍事題材舞蹈作品也同樣如此。也許這類題材作品現(xiàn)在所要面對的是一個繁復(fù)紛榮的時代大舞臺,在這個時代舞臺上,審美觀念和社會群體意識的多樣發(fā)展讓“軍事題材”本身已經(jīng)不再獨占特別的優(yōu)勢,舞蹈編創(chuàng)者不能像以往一樣僅僅依靠選材的分量和人們“情感審美”的偏向去出彩和讓大眾接納這樣的作品。可以猜測的是,在當(dāng)代背景下的中國大舞臺,軍事題材的舞蹈繼續(xù)下去的生命力和競爭點只能是來自于“題材”本身的與眾不同了。
但是,當(dāng)下我們務(wù)必要認識到的一點是:當(dāng)代舞想要延續(xù)發(fā)展的話僅僅只是依靠改一個名稱是完全辦不到的。這只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泡沫,哪里能經(jīng)得住藝術(shù)舞臺的考驗?所以,要想當(dāng)代舞能真實扎穩(wěn)根基的發(fā)展,務(wù)必是要經(jīng)歷多種舞蹈思潮的碰撞和提煉,找準自己的價值特征與風(fēng)格定位,讓當(dāng)代舞也形成自己的教學(xué)研究系統(tǒng)和編創(chuàng)技法體系,如此,當(dāng)代舞才會有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