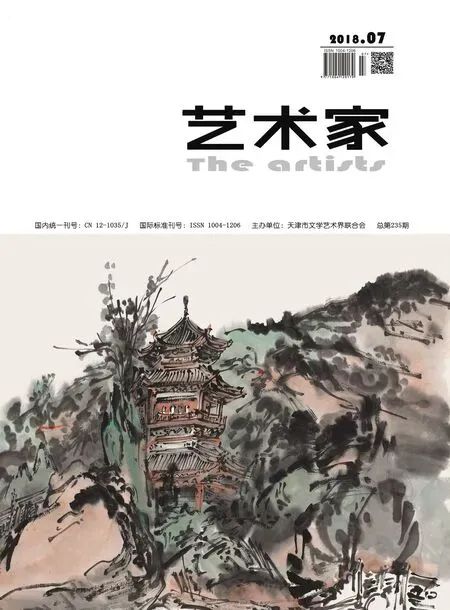文學與影視的差異化表現
□李佳席 浙江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
近幾年,暢銷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幾乎成了一種潮流,IP電影的超高票房,讓不少人認為作家的走紅有絕大一部分原因是其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文學作品與當今電影的高科技聯姻,為文學作品的影視化提供了大量的受眾群體,同時也碰撞出新的色彩。電影中聲效、色彩、畫面鏡頭的剪接與組合,通過計算機處理產出的特殊視覺效果,獨異和優越于其他藝術門類。不可否認的是,影視擁有強大的表現手段和表現空間,但文學和影視終究是含有各自藝術特質的存在形式,當文學作品被局限的影視篇幅而限制時,兩者還是存在差異的。
一、文學細節的表現差異
電影再現小說濃厚的文學性時表現得力不從心,最具體的就體現在細節的表現上。細節是文學作品或影視作品在描寫人物性格、敘述事件發展、展示重要社會環境和自然景物的最小單位[1]。在整個文學或影視作品中,細節描寫屬于情節的基本構成單位,雖然屬于“枝葉”,但占有重要地位。一個好的細節處理,可以在表現作品主題和文字或影視風格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可以升華人物形象。細節描寫的特點是對所描寫對象作逼真、細膩、生動的描繪,它是對重要信息的具體描寫。因此,細節的審美功能是通過具有細節參與的具體描寫和刻畫,真正體現“以小見大”、從細節看整體的重要意義。精彩的細節會讓人眼前一亮,甚至發現其中包含的特別含義,讓人回味長久,給人以驚喜[2]。文學以抽象性的語言文字作為敘事的承載,而影視以具象的動作性決定了運動畫面為敘事載體,電影的具象性決定了它對文學作品的改編只能從看得見的角度出發,再現物質現實。
例如,文學作品《阿Q正傳》中阿Q畫押、陳奐生住店等細節描寫,既有利于情節的發展,又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主題的表達,準確而細膩地表現出社會生活本質的某些方面,而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文學語言注重的是傳神,這是影視表現手段所無法企及的,尤其是對神態及心理活動的描寫。文學作品總能帶領讀者迅速了解人物性格,給予讀者更大的想象空間,這都是影視表現所欠缺的。但從另一方面講,文學中的細節描寫是平面的,而影視中的細節描寫是立體的;文學中的細節描寫,可以進行細致的細節刻畫,但有些諸如道具或場景的細節刻畫就需要花費一定的篇幅,這樣就會暫時中斷情節敘述,可能會導致讀者瞬間的情節抽離,影響情節發展。這一問題對于立體化和畫面感非常強的影視手段來說是不需要考慮的。它可以通過鏡頭的變化(如使用特寫、快慢鏡頭及反復鏡頭呈現等方)直觀地描繪細節,引起觀眾的注意。因此,影視作品中的細節表現往往和影視敘事相結合,所以相對來說比文學作品的描寫更加流暢[3]。
此外,文學作品中的細節表現是單一手段,只能使用語言的線形表現;而影視作品則可以采用多種元素的綜合使用來構成細節。因此,影視作品相對文學作品來說,在構成細節的手段和元素上要豐富得多。
二、人物形象的表現差異
我們所熟知的一個個鮮活的形象,往往都是來自經典的文學著作中,從古至今依然綻放光芒,如《紅樓夢》中的王熙鳳一角,現在想起來似乎還能感受到她潑辣和爽朗的笑聲,海明威的《老人與海》中那個堅毅的漢子桑提亞哥,《巴黎圣母院》中有由善良熱心變得自私虛偽的副教主弗羅洛等。這些形象都隨著文字得到升華,變成世界文學寶庫中的瑰寶。作為傳統文字文學,對于人物形象的刻畫有許多細致的表現方法,最普遍的就是心理描寫。通過對人物心理的細致描寫,將人物形象多方位地塑造出來,使讀者能夠更好地感受書中鮮明的人物形象[4]。
而在影視作品中,心理描寫在熒幕上直觀表現給觀眾的較少。心理描寫大多體現在劇本上,而這種心理變化要通過演員的表演得到體現就很難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通關眼神、動作來表現各種思想狀態,人物形象與主題要形成高度統一,而影視作品的核心也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只是表現手段比較單一。在人物形象的身上,常常集中體現著創作者自身的思想與情感好惡。在影視作品中也一樣,如果只是憑借大段獨白讓觀眾理解每一位人物的內心感受,這對于鏡頭的表現力來說會大大減弱作品的說服力,并且使影視的表現形式顯得很不和諧,難以讓觀眾很好地融入情節的發展中去。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影視作品中就顯得尤為重要了,也成為吸引觀眾的首要看點。以《大話西游》為例,主要人物還是沿用了名著《西游記》中的形象,但卻加上了周星馳所特有的表現方法,讓整個形象生動幽默起來,塑造出一個特殊的人物形象,這樣的表演也得到了觀眾的喜愛。在人物塑造方面,動作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個人物是什么形象,在影視作品中是用動作表現傳遞給觀眾的,也可以說人物的實質是動作。例如,在影片中,有位老人需要過馬路,這時人物形象就很容易通過人物的動作表現出來,如果只是視而不見,那么這個人物可能是冷酷的;如果趕忙上前攙扶,那他極可能是一個熱情而善良的人。這樣一來,人物形象就變得十分鮮活了。
在影視作品中,動作是塑造形象的主要途徑。這相比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塑造顯得十分有難度。有些深層次的內心思想是很難用動作表現出來的,所以很多改編文學的影視作品都不是那么成功,有很大原因是不能滿足讀者對于人物的想象。但這不會影響影視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獨特角度。
三、象征手法的表現差異
所謂象征,從象征實體出發,到象征寓意的感悟,在心理上經過了一次由此及彼的依次聯想的動態過程,并且在審美感受上得到了超越形象、超越本體的效果,使觀眾得到了“言外之意”。在影視手段的表現上,主要體現在鏡頭的拉近,給予象征物體特寫。影視作品作為大眾的視聽藝術,所產生的造型感染力與視覺沖擊力也遠遠比靜態描述性的文字來得直接。而象征在文學作品中的表現則是通過鋪墊和陳述描寫來表現的[5]。
在影視作品的象征表現中,每位影視導演其實都有自己慣用的方法,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張藝謀、姜文的作品。張藝謀在其影片中充分運用影像來創造形之外的意,善于利用宏大的場面表現。例如,在《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大片菊花的道具背景,以及菊花袍,因為“黃菊花”在影片中充當的是反叛的象征符號,最終滿地殘菊,用直接且震撼的畫面表現了大眾起義及反抗皇權的慘敗后果。張藝謀對農村傳統題材的掌握,具有雙重的象征意義:一方面是對原始生命力的探索與贊美,另一方面又是對蒼涼、貧困、落后、愚昧的反思和批判。在他拍攝的影片中,有很多極具象征意義的鏡頭,如電影《紅高粱》中的“酒歌”“顛轎”這兩種場景的描繪,是對生命的肆意張揚與敬仰,突出的是主人公九兒與于占鰲之間熾熱的感情發展,以及對侵略者的抵抗。姜文的電影中對象征手法的運用更加多元化,主要通過對色彩的掌控,反映出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時代特色。以《陽光燦爛的日子》為例,全片都是在陽光燦爛的夏日白天完成的,黃色的暖色調為基調,像看一段老時光,在紀念青春的同時也暗含著對現實悲劇的諷刺。
與細節表現一樣,影視作品的象征也是通過多種元素來綜合使用的。例如,電視劇《來來往往》中林珠的身影和金絲鳥籠交錯的鏡頭,構成了人物命運與身份的象征;色彩可以構成象征,如《紅高粱》中紅色象征著生命和愛情。在電影《重慶森林》和《墮落天使》中,對畫面語言大多采用慢速攝影,因而畫面的節奏很快,這無疑體現了現代人的生活節奏之快,以及內心的騷動與不安。可見,在影視作品中,象征手法的體現是直觀的、生動的,帶有鮮明的造型性,給人的視覺沖擊力更大。但另一方面,影視作品在使用象征手段時,采用聲畫結合的方法,在畫面的體現上雖然豐富,但相比文字的靈活生動來說就,顯得生硬刻板很多,失去了文字特有的隱性含義和更多的想象空間。
結 語
綜上所述,本文從三個角度分析了文學與影視的表現差異,雖然如今因為快節奏的生活,以及信息傳播途徑空前發達,大眾娛樂、審美趨向空前多元,影視藝術在大眾生活中越來越不可或缺,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忽視文學的不可替代地位,兩者應相輔相成,也必將始終保持各自的獨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