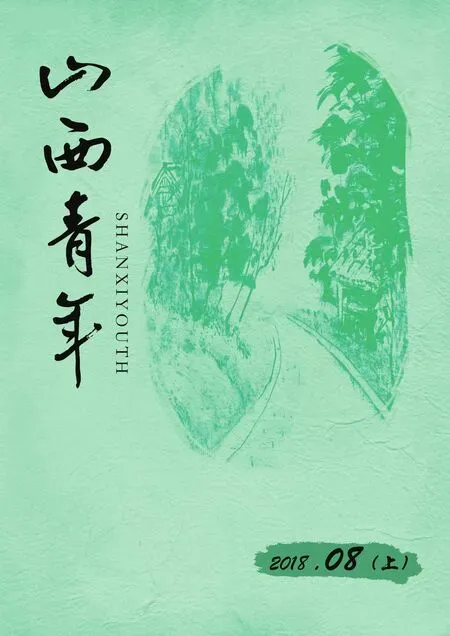中心化與邊緣化:國家、市場視角下的鄉村變遷*
——基于內地農村四村的調查
譚曉慶 閆紫微 趙竹漪 馬蘇日娜 馬雅琪
(江南大學,江蘇 無錫 214122)
一、引言
在城市中心化、農村邊緣化的背景下,城市該怎樣解決過度的負荷,農村又該如何應對落后于時代的問題?農村的選擇會是什么,是離開還是留守,他們各自又該怎樣應對時代的洪流?農村新的發展道路究竟在哪里,它又會走向何方?農村傳統是該舍棄還是保留?如何動用國家、市場的力量加速農村產業發展,縮小城鄉差距?這些都是亟需討論和解決的問題。經濟的長足持續發展、社會的和諧穩定、整個國家的進步和民族的復興與農村相關,也注定落腳于農村。
二、鄉村變遷現狀描述
(一)人口與經濟
基于四村人口狀況調查,農村人口外流的特點突出,雖然村內留守兒童現象依然存在,但越來越多的父母在融入城市后,選擇將孩子帶離農村,流動兒童的比例在近期迅速上升;外流人員聚集地選擇多元化——除去經濟發達、工業密集的城市務工之外,外流人員逐漸集中在省內尋找就業機會,同時,相較原有以工廠、工地小工為主要就業方式,外出務工人員從事第三產業比例上升;經濟方面,由于外流嚴重且種植成本上升,四村中半數出現拋荒現象;村個體經濟較集體經濟發展更為迅速;村戶家庭消費恩格爾系數較高,但值得關注的是教育成為日常消費開支的第二大占比;同時國家與市場的補給在鄉村變遷建設中比重加大,低保與養老保險覆蓋率高,且部分地方政府在基礎保障之上推行了農村特殊補助。
(二)文化與政治
四省文化情況的調查集中于禮俗變化以及鄉土情結。以禮俗中突出的整酒風以及節日文化為例,雖然馬村仍存鋪張浪費之風,但繼政府“整酒”措施出臺后,大部分地區崇尚紅白喜事從簡;村民對傳統節日風俗的重視程度不高,盡管政府號召文化傳承和文化保護,但傳統文化的保留狀況仍不容樂觀;村民鄉土情結的調查劃分為老少兩組,較為年長的村民鄉土情結深重,在鄉村變遷的過程中堅定了鄉村發展的信念,相反青壯年在不斷接受城市文化的浸染下,鄉村觀念開始解構。相較文化經濟,村民的政治意識在鄉村中的改善最為薄弱,村民對于村內選舉以及村民自治的觀念相當匱乏,大多數村民了解政治、參與政治、融入政治的想法不足。
三、中心化與邊緣化
(一)中心化與邊緣化產生的原因
1.國家視角
(1)基層治理體系仍不健全。改革開放以來,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我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在鄉村的最低一級確立了村民委員會制度,實行以村民委員會為主的農村基層治理體系。在這一體制下,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帶領村民依法管理村中各項公共事務,享有自治權。該制度通過讓村民參與村中政治事務,培養了村民的民主意識,提高了村民參政議政的水平,體現了村民當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但同時,這種制度伴隨著權力的下移,脫離了政府的統一管理,村民委員會受到多種因素共同制約,不能發揮其正常作用,也助推了鄉村的“邊緣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地理位置——若鄉村位于偏遠地區,環境封閉,與外界社會交流甚少,先進的治理思想則無法引入村中。處于邊緣地理位置的鄉村,天然就帶有“邊緣化”趨勢。B:干部能力——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在鄉村的村委會換屆選舉中村民可以信任并選擇的有能力的村干部候選人不足,最終的結果就是上任的村干部不能勝任各項工作,沒有能力帶領村民實現村子發展。這也與鄉村精英流失有一定的關系。C:村民意識——由于缺少與外界社會先進思想的交流,又沒有能力素養過硬的村干部指引,導致村民相關知識不足,自治意識不強。
(2)國家扶持存在政策偏向。國家站在戰略的高度,會對國家的不同地區實行不同的發展規劃,施以不同的扶持政策。其扶持力度偏向必然會導致城鄉之間的基礎設施等建設水平出現差異,甚至拉大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政府實行的偏向城市的治理政策,推動城市經濟快速發展,而處于國家扶持政策邊緣的鄉村地區,由于投入不足,基礎設施仍處于較低水平,發展緩慢,不利于實現城鄉一體化。
2.市場視角
(1)資源配置陷入惡性循環。在市場經濟下,經濟基礎較好的地區,起步較高,就能更好地利用市場所配置的資源,得到很好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就會樂于在該地區配置更多資源。相反,經濟基礎較差的地區,市場就會在下次配置資源時減少甚至免去對該地區的投入。而在當前,我國城市地區就處在易于吸引資源支持的有利地位,鄉村地區處于難以獲得資源配置的不利境地,形成了富者越富、貧者越貧的惡性循環怪圈,加劇了城鄉之間的不平衡。
(2)在經濟上具有低重要性。我國大部分鄉村目前提供的商品仍舊是農產品,種類單一。且地域閉塞,交通不便,均不具備上述相應的作用和地位,難以主動融入到市場經濟大環境中,在以激烈的自由競爭為基礎的市場運行模式中處于不利地位,故在經濟上被再度邊緣化。
(二)中心化與邊緣化的影響
城鄉發展不平衡日趨嚴重,農民逐漸意識到城市擁有更好的就業機會和生存條件,加之農業發展潛力小,農民無法靠農業生產來滿足生活和發展需要,因此,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資源流入城市。城市在此過程中,滿足了城市化進程中對勞動力的需求,也刺激了消費需求,拓寬了消費市場[1]。但是,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流入也給城市建設和城市化發展帶來了消極影響:城市人居環境質量下降,城市污染加重;社會治理難度加大,城市就業競爭加劇,城市失業率升高。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將建設重心放在城市,大量農村資源被用于城市建設,導致城鄉發展不平衡,出現城市中心化和農村邊緣化的現象。為改變這一現狀,國家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的方針,并給予農村政策優惠,引導城市的先進技術、產品等資源流入農村[2]。這一方針政策實施以來,機器生產等工業技術、高科技產品紛紛傳入農村,打開了農村市場,農業生產效率得到了提高,農村企業數量增多,拉動了當地經濟的轉型與發展,農村逐漸與城市接軌。
(三)鄉村發展與前景
城市中心化的趨勢日漸突出,鄉村則被剝奪資源,陷入邊緣化境地。因此,許多學者和專家抱持著“鄉村衰敗論”的觀點——即鄉村在變遷的過程中,鄉村會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逐漸走向衰落。然而,本研究認為,在國家、市場的大力扶持下,鄉村在進化過程中表現出適應環境的能力不斷增強,并能夠從外界獲取資源作為己用的特征。鄉村在獲取資源的過程中開始自己內部的分化,并開始新的整合,從而得到更高水平的發展。鄉村發展的前景并非黯淡無光,相反,隨著我國國家從宏觀方面入手,彌補鄉村變遷中出現的社會缺口;市場從經濟方面,通過對資源的整合利用,從而實現中心化與邊緣化資源的平衡。鄉村不會走向衰敗,而是朝著一個更穩定、更堅挺、更繁榮的方向發展。
當下農村發展的第一步,是大力發展基礎設施,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有村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村民才會有更大的渴望追求精神上的完滿;打牢文化基石,糾正文化偏差,著名學者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曾展現了一幅以地緣和血緣為紐帶的中國傳統鄉村格局[3],打牢文化基石,就是要加強對傳統文化的宣傳,增強人們對于鄉土文化的認可,運用資源豐富文化底蘊,從而填充文化;糾正文化偏差,就是要凈化社會壞境,摒棄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把村民從“解構文化”中拉回[4],轉而維持、修復文化;合理資源配置,力促雙向聯結,鄉村美好前景的實現,依賴于資源的合理配置,依賴于城市和鄉村的聯合。打破部分農村蓬勃發展,另一部分卻因為資源的分配偏差而逐漸干癟蕭條的困境[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