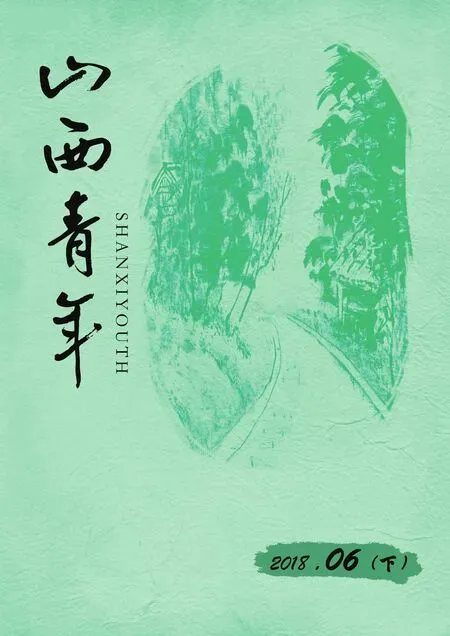淺析英國都鐸時期的社會特性
成銀枚
(河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新鄉 453007)
都鐸在英國歷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王朝,它處在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節點上,組建并鞏固了民族國家,把英國推進到可以發動現代化的起點。且資本主義率先在英國發展成長起來,并成為籠罩社會的優勢力量,進而成為一種“制度”,究其緣由,很有可能是在都鐸王朝積累起來的資本主義與政治合作和社會烘托的土壤上發展起來的。的確,都鐸時期的社會充滿生機與活力,這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當然,也對后來國家的發展有著潛在的影響。
一、都鐸君主政體的特殊性
都鐸王朝的議會比之以往有了明顯的變化,尤其是“王在議會”原則的萌芽和發展。該時期保留了一定的自中世紀貴族和國王的抗爭中形成的“自由”傳統,雖然都鐸諸王常常凌駕于議會之上,但都不否認“王在議會”的政治現實和必要性。宗教改革的進行使得上院教會貴族大大減少,顯露出上院的衰落趨勢,而下院權利卻得到加強。“隨著議會內部議員成分的變化,上、下兩院之間的人數由15世紀的1:2,變成伊麗莎白女王晚年的1:5.5。”[1]這種變化說明下院的重要性凸顯以及立法職能的加強,有助于加強議員們的參與意識、使人們從事議會辯論和立法活動的積極性得到提高,間接調節了當時的社會氣氛。
英國學者邁克爾·曼將“立憲”君主制共和國和絕對主義專制做對比,“凌駕于市民社會之上的權力,即專制主義;協調市民社會的權力,即基礎結構的活力,絕對主義國家在基礎結構方面并不比立憲國家強。”[2]顯而易見,這兩種制度以近代早期的英法兩國為代表。“英國與荷蘭是在地主和富商的同意下對這二者征稅。絕對主義政體則是在地主同意和協助鎮壓的條件下對有地的窮人和富商征稅。”[3]眾所周知,英國在國家建構中有一大特點是缺乏強制性武裝力量,而常備軍不僅可以保衛國家、鎮壓國內異端,還可以加強君主統治“市民社會”的權力。可見,英國的市民社會發展程度更高,基礎結構活力自然也更高,從缺少常備軍和征稅方式較為溫和的角度來講,英國社會受到壓榨程度較小。
二、社會流動與社會自治
英國的國家建構過程中不僅缺乏常備軍,它的國家機器還缺乏強大的官僚機構和中央政府,社會管理基本上由治安法官來完成,他們作為中間人平衡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同時以一種不領取薪俸且自愿擔任的形式節約了都鐸的政治成本,在濟貧與社會救濟上發揮著重要作用。這種可稱之為“社會治理社會”的方式是英格蘭社會管理的特性之一,它對減輕中央對地方的壓榨有緩和作用。
17世紀的英格蘭是“一個高度分層的農業社會”,[4]社會流動尤其是“垂直流動”比封建性更強的歐洲大陸容易得多,“層與層之間的界限”不那么明顯,而是有相當程度的開放性和靈活性,能對變化的環境作出較靈活的適應和反應,并能適時地根據各種因素的變化來調整每個階層自身的社會存在方式。”[5]英格蘭的社會等級的開放性是其顯著特征,通過自我奮斗而取得成功的人容易贏得社會尊重并獲得相應的社會地位。它近似上下流通的橢圓形社會,這種流通形式維持了社會的動態平衡,并激勵著人們奮發向上以改變自己的生存現狀。
三、商人階層的發展壯大
英國一直以來有“小店主的國家”之稱,16、17世紀,英國的商人階層開始形成,商人數量呈現大幅度上升的趨勢。同時,交易的范圍和種類,交易的形式和經營方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隨著商業的繼續發展,英國商人在意愿和制度上得到了社會的尊重和保障。人們更加理性的來重新判斷價值標準,社會上出現了一種適應商業發展的以財富和勞動為中心的新型價值觀。加上早期文藝復興喚醒了人們積極進取和創造的精神,因宗教改革產生的新教義和新信仰極大程度地鼓勵了商人追求財富的信念,商人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取得相應的經濟地位進而獲得政治地位。于是,商人從中央到地方在政治事務上的身影隨處可見,掌權者也越來越愿意吸納商人加入政壇。可以說,商人的社會地位經歷了從量的改變到質的飛躍。在商人們身上形成的節儉、勤奮、誠實守信、冒險、開拓創新的新教倫理精神廣為流傳,即韋伯所言的“合理謀利”,它營造了整個社會一副欣欣向榮的面貌。
四、結語
任何一個社會的發展都是在保持社會秩序的條件下進行的,否則就會動蕩、停滯甚至倒退。都鐸的社會轉型條件是比較充分的,它充滿了活力與煥發著生機:君主專制卻給人們留有一定自由;缺少常備軍,警察部隊,任用地方鄉紳減少了中央對地方的壓榨;英國社會的開放性和流動性推動個體的積極向上;整個社會對商業的尊重,鼓勵市民追求財富為社會發展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在這些條件下,社會的有序狀態和動態平衡得到了保障,為正在進行的社會轉型營造了良好環境。
[1]閻照祥.英國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51.
[2]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M].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86.
[3]邁克爾·曼.社會權力的來源[M].劉北成,李少軍,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89.
[4]許潔明.十七世紀的英國社會[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25.
[5]錢乘旦,陳曉律.英國文化模式溯源[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