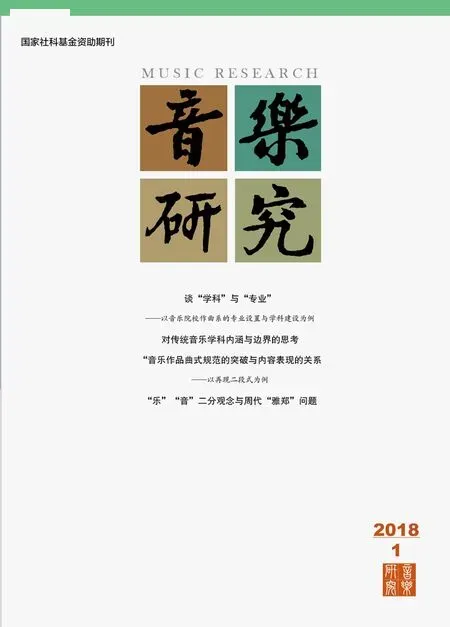繽紛世界與深居落點—對音樂與舞蹈學(xué)構(gòu)架下交叉學(xué)科理論研討之述評
文◎劉 欣
2017年10月13—15日,在吉林省長春市東北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召開了“音樂與舞蹈學(xué)構(gòu)架下的交叉學(xué)科理論研討會”。本次會議由東北師范大學(xué)與人民音樂出版社聯(lián)合主辦,承辦單位為東北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音樂研究》雜志和《北京舞蹈學(xué)院學(xué)報》。會議的主體部分以三種形式呈現(xiàn):第一,主題發(fā)言。由會議邀請的資深的音樂學(xué)與舞蹈學(xué)研究學(xué)者、《音樂研究》和《北京舞蹈學(xué)院學(xué)報》的主要編審共八位專家做主題性發(fā)言。第二,研討交流。包括東北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的青年學(xué)者論壇和這些青年學(xué)者與專家、與會教師現(xiàn)場研討交流等多項內(nèi)容的活動。第三,專場演出。分別推出舞蹈和音樂兩場專場實踐演出。來自國內(nèi)八十八所高校的兩百多名音樂與舞蹈專業(yè)的專家學(xué)者及師生代表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是一次全國性音樂與舞蹈相關(guān)交叉學(xué)科的交流盛會,旨在推動音樂舞蹈理論與相關(guān)學(xué)科理論交叉學(xué)科研究,整合多學(xué)科領(lǐng)域?qū)W術(shù)資源,推動年輕研究學(xué)者的進(jìn)步與發(fā)展,在立足學(xué)科本位的基礎(chǔ)上,培養(yǎng)新的學(xué)科增長點。會議內(nèi)容以音樂與舞蹈學(xué)構(gòu)架下的交叉學(xué)科為視域,將專題報告與青年學(xué)者論壇相結(jié)合,既有學(xué)科前沿的歷史性高瞻遠(yuǎn)矚,也有跨學(xué)科交融的創(chuàng)新性交流碰撞,力求通過廣泛的現(xiàn)有多學(xué)科成果經(jīng)驗深入交流,夯實音樂與舞蹈理論研究基礎(chǔ),發(fā)掘音樂與舞蹈理論研究新視角,于學(xué)科深居落點中領(lǐng)略與探尋繽紛世界的絢爛與神奇(伍國棟語),全面推進(jìn)學(xué)科發(fā)展。
八位音樂與舞蹈學(xué)的教授發(fā)言精彩紛呈,有基于對自己學(xué)術(shù)研究領(lǐng)域的深入闡釋之上的學(xué)科交叉層面的探查辨析;有通過學(xué)科交叉的思路與方法的運用,在傳統(tǒng)學(xué)科構(gòu)架下的綜合研究;對有在音樂與舞蹈這一學(xué)科領(lǐng)域下,對于音樂與舞蹈關(guān)系的感性解讀和理性比較;更有基于學(xué)科本位,對學(xué)科擴(kuò)展和交叉的高屋建瓴的思考。
一、于深居落點映繽紛世界:學(xué)科本位深入闡釋基礎(chǔ)上的學(xué)科交叉考議
上海音樂學(xué)院韓鍾恩教授的發(fā)言主題為《如何通過音樂學(xué)方式寫音樂》。他以音樂學(xué)寫作基本問題為前提,以如何通過音樂學(xué)方式寫音樂為命題,列舉了若干作品來討論三個問題——“從格物致知到格藝致美”“音響詩原”“當(dāng)代音樂應(yīng)該發(fā)出什么樣的聲音”,進(jìn)而將音樂學(xué)寫作的主要問題聚焦為音樂的“聽”與音樂學(xué)的“說”。
在講座伊始,韓鍾恩教授便對音樂聽什么、音樂學(xué)寫什么、怎么寫提出詰問,并提出對音樂學(xué)寫作的基本界定:不是用別的方式寫音樂,不是用音樂學(xué)的方式寫別的,是用音樂學(xué)的方式寫音樂。然后,韓教授通過對格物致知的深層解釋——面對直觀對象卻超越感性層面直接進(jìn)入忽略甚至無視直觀對象,并懸置甚至于顛覆感性直覺本身的理性層面,引入了格藝至美的新的設(shè)問思考——置身如此狀態(tài)下,作為音樂學(xué)學(xué)者,究竟如何通過直覺達(dá)至義理?尤其是如何面對直觀的藝術(shù)作品去實現(xiàn)應(yīng)有的審美觀照?韓教授從切入程序和切中目標(biāo)兩個層面對此進(jìn)行了回答和闡釋,指出切入程序要注意由音響結(jié)構(gòu)力及其描寫凸顯的藝術(shù)問題,而音樂美學(xué)目標(biāo)則為終究與規(guī)約音響結(jié)構(gòu)力,之所以是的基于原始美學(xué)規(guī)范想象的感性結(jié)構(gòu)力。
接下來,韓教授運用“音響詩原”這一概念,提出了藝術(shù)自在與美學(xué)自覺的同一的意義,進(jìn)而提出了當(dāng)代音樂的基本問題——什么是合乎當(dāng)代音樂自身存在的結(jié)構(gòu)發(fā)聲。韓教授說道:“可以肯定的是,每個時代的音樂都有其特定的形式,尤其是美的形式,問題是:當(dāng)代音樂僅僅是為求新而新?或者是為求平衡折返回歸的功能發(fā)聲?還是應(yīng)該合乎其自身存在的結(jié)構(gòu)發(fā)聲?當(dāng)代音樂家能否接續(xù)20世紀(jì)輝煌去再現(xiàn)21世紀(jì)的結(jié)構(gòu)發(fā)聲?當(dāng)代音樂學(xué)家又能否在當(dāng)代音樂中鉤沉歷史的聲音并考掘本有的聲音?”
在不斷地省問之上,韓鍾恩教授最后將發(fā)言歸結(jié)于對音樂的“聽”與音樂學(xué)的“說”的思考。感性地聽聲音——前提是需進(jìn)行音樂、樂音、音聲、聲音諸概念范疇多層次、多維度的意義邏輯澄清,“依語言建構(gòu)經(jīng)驗并使用工具以進(jìn)入音響敞開與真理相遇——憑存在本有的樣子去合式地說音樂并屬音樂的經(jīng)驗。”
《音樂研究》編審、中央音樂學(xué)院陳荃有教授在他的《對中國音樂史學(xué)科相關(guān)問題之漫議》發(fā)言中,首先通過對中國音樂史學(xué)科發(fā)展歷程的回顧,以該學(xué)科近年來的動向及原由的追索,探討其科研走向和題域所發(fā)生的變化。陳教授指出,21世紀(jì)以來,在音樂史學(xué)論著方面,通史著述無大的學(xué)術(shù)突破。代表性著作的修訂、增訂、重印和再包裝常見。新著及課題反映的領(lǐng)域更加拓寬,視野更為開闊,研究方法愈加多樣化。總而言之,音樂史各分支領(lǐng)域的學(xué)科研究已相對獨立,如音樂考古學(xué)、樂律學(xué)、音樂文獻(xiàn)學(xué)、音樂史學(xué)史、音樂圖像學(xué)等。一些分支領(lǐng)域甚至成為整個學(xué)界時代發(fā)展的亮點、熱點,如音樂考古、古譜解譯、音樂交流、文獻(xiàn)校釋。分析個中原由,或可能是學(xué)科走向成熟的必經(jīng)階段所致;或可能是相關(guān)學(xué)科發(fā)展的啟發(fā)、引導(dǎo)和帶動所致;也或可能是時代及科研制度的弊病所致。在未來的若干年中,中國音樂史學(xué)仍將因各分支學(xué)科、邊緣學(xué)科的發(fā)展而使自身得到深化、提高。音樂史學(xué)各分支學(xué)科和相關(guān)領(lǐng)域,將更多地吸收、借鑒兄弟學(xué)科,乃至其他人文社會科學(xué)、自然科學(xué)的成果和方法,以促進(jìn)各自的發(fā)展。由中國音樂史學(xué)和更多更廣泛的其他學(xué)科相交叉而產(chǎn)生的新興學(xué)科以及能夠體現(xiàn)中國音樂史學(xué)科百年發(fā)展成就的通史大著或?qū)⒊霈F(xiàn)。
接著,陳荃有教授通過對個案的觀察與分析,思考面對研究對象時多學(xué)科認(rèn)知方法的必要性;同時,借由黃翔鵬先生對學(xué)問方式的思考,提出了自己對學(xué)科與學(xué)術(shù)問題的基本認(rèn)識:“對于追求創(chuàng)新意義的學(xué)術(shù)研究來說,應(yīng)具‘問題意識’;而‘問題’之源,則在融結(jié)于‘對象’之上被充分占有之各類型材料。”并最后得出學(xué)問之道,在于由“學(xué)”而“問”,為“問”而“學(xué)”的精辟論斷。
雖然韓鍾恩教授與陳荃有教授的發(fā)言都是基于學(xué)科本位的探討,但在他們在言談?wù)撜Z中無時不映射著其對學(xué)科拓展與學(xué)科交叉的深層思考和啟悟。韓鍾恩教授在演講開篇,就對本次會議主題回應(yīng)指出,近年來隨著學(xué)科建設(shè)進(jìn)程的不斷深入擴(kuò)展,跨界、交叉、“X+”等理念不斷滲入到學(xué)界議程之中。雖然這種跨界與交叉會出現(xiàn)一些新的成果,但音樂學(xué)者必須明確的是,“嚴(yán)格意義上說,任一學(xué)科都是獨立自足的,任一學(xué)科也都不可能與別種學(xué)科毫無關(guān)聯(lián)。”因此,“真正意義上的交叉應(yīng)該立足本位,關(guān)聯(lián)別的,時刻警惕學(xué)科泛化與理論僭越。”
至于如何“立足本位,關(guān)聯(lián)其他”,兩位教授的發(fā)言內(nèi)容為我們做了最好的示范。韓鍾恩教授在提及當(dāng)代音樂的基本問題時,通過多重關(guān)系討論了音樂的邊界問題,進(jìn)而探索了當(dāng)代音樂研究的論域拓展。韓教授談道:“無論古今中外,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總是離不開自然與文化的關(guān)系,文化與藝術(shù)的關(guān)系,藝術(shù)與音樂的關(guān)系,音樂與音樂學(xué)的關(guān)系,音樂學(xué)與音樂美學(xué)或者音樂人類學(xué)以及音樂史的關(guān)系。”因為音樂屬性是文化產(chǎn)物、藝術(shù)作品、審美對象、純粹形式四者合一。所以,當(dāng)代音樂研究就會自然地進(jìn)入文化、藝術(shù)、音樂、音樂學(xué)論域,探討音樂遭遇具衍生性功能的文化問題,屬原生性結(jié)構(gòu)的藝術(shù)問題,有關(guān)情聲能否和合為一的美學(xué)問題,以及相關(guān)物自體、情本體、聲常體、聽元體的哲學(xué)問題。陳荃有教授則通過中國音樂史近年來學(xué)科動向的研究,歸納出音樂考古、音樂交流等各分支學(xué)科、邊緣學(xué)科的發(fā)展只有以問題為中心才能使中國音樂史學(xué)科自身得以深化和提高的觀點。可以說,兩位專家發(fā)言的具體研究內(nèi)容和透過內(nèi)容折射出的對本科本位與交叉的深層思考都值得后學(xué)者品味借鑒。
二、于深居落點集繽紛世界:學(xué)科構(gòu)架下的音樂與舞蹈關(guān)系辨析
北京舞蹈學(xué)院副院長,《北京舞蹈學(xué)院學(xué)報》主編鄧佑玲教授的發(fā)言題目為《舞蹈與音樂學(xué)交叉學(xué)科下的思考》。圍繞著這一發(fā)言題目,她主要論述了音樂與舞蹈學(xué)作為一級學(xué)科,應(yīng)該怎樣進(jìn)行學(xué)科建設(shè)的問題。她指出,自2011年藝術(shù)學(xué)升格為門類后,音樂學(xué)與舞蹈學(xué)合并為一個學(xué)科,但直到現(xiàn)在都各自在做自己的學(xué)科,沒有真正走在一起,到底它們是共在關(guān)系還是并列關(guān)系,需要分開建設(shè)還是合起來建設(shè)還是一個問題。如果要分開建設(shè),目前國家的“雙一流”大學(xué)和學(xué)科存在著舞蹈學(xué)科缺位的問題,而如果要合并建設(shè),則需淡化學(xué)科邊界,促進(jìn)學(xué)科融合。這種融合不是簡單的協(xié)同融合,而是高層次的融合,是音樂、舞蹈在同一藝術(shù)門類下,在探索共性的問題,找到共性的規(guī)律的基礎(chǔ)上的一種高層次的融合。鄧教授在講座中還提及了融合的具體方法,認(rèn)為可以從發(fā)生論、本體論、創(chuàng)作論、功能論、發(fā)展論、批評理論、方法論等角度來探索音樂與舞蹈學(xué)的共性,構(gòu)建音樂與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
在論及音樂與舞蹈學(xué)學(xué)科融合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前景時,鄧教授闡釋了舞蹈和音樂的密切關(guān)系。她的觀點是舞蹈不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存在,而音樂雖然可以獨立存在,但舞蹈作為人類藝術(shù)抒情的最高手段或形式,也可以起到傳揚音樂文化、推廣音樂的重要作用。不過,目前要做到學(xué)科融合還是困難重重,專業(yè)藝術(shù)院校的獨立建制、學(xué)科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共同體和已有的學(xué)科理論的融合建設(shè)等問題都需要逐步解決。只有撇開門戶之見,從優(yōu)勢互補的角度站位,才能促進(jìn)整體的一級學(xué)科建設(shè)。
鄧教授在發(fā)言中還強調(diào)了音樂舞蹈學(xué)科建設(shè)的重要意義,認(rèn)為音樂與舞蹈學(xué)科的建設(shè)和發(fā)展在當(dāng)代的功能和作用有三:可以滿足人們在衣食富足后,全社會多樣化的精神需求。可以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配合國家戰(zhàn)略目標(biāo)的實現(xiàn)。可以培養(yǎng)創(chuàng)意設(shè)計人才,培養(yǎng)會欣賞創(chuàng)意設(shè)計的大眾,提升創(chuàng)意的文化氛圍。涉及音樂與舞蹈學(xué)科建設(shè)的具體做法,鄧教授從弘揚民族藝術(shù)文化的角度提出四個方面的建議:要建立中華藝術(shù)的自覺、自信;讓中國的音樂、舞蹈文化走向世界;警惕文化他信現(xiàn)象的普遍存在;增強音樂與舞蹈學(xué)術(shù)理論和學(xué)科理論自信。
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長、舞蹈學(xué)研究專家歐建平教授的發(fā)言題目為《舞蹈與音樂關(guān)系研究》。在講座過程中,他運用直觀感性的方式形象地論述了舞蹈與音樂的關(guān)系。他認(rèn)為,在舞蹈與音樂、美術(shù)、文學(xué)等姊妹藝術(shù)的關(guān)系中,舞蹈與音樂的關(guān)系最為密切。人們對音樂與舞蹈關(guān)系的思考傳統(tǒng)上可以分為四種觀點:“靈魂說”“舞曲說”“主仆說”“并行說”。
舞蹈與音樂的結(jié)合方式上,歐建平教授提出了五種方法:(1)“踩點法”:指大多數(shù)傳統(tǒng)舞蹈的編導(dǎo)和表演都按照音樂提供的節(jié)奏去“踩點”跳舞的方法。(2)“借力法”:指借用爵士樂、搖滾樂、各類流行歌曲的“張力”來編舞的方法。(3)“借用法”:指不用原有的經(jīng)典舞劇音樂,而是根據(jù)古典名家名曲的不同特征,去選取現(xiàn)成交響樂編舞的方法。(4)“并行法”:指在舞蹈與音樂的創(chuàng)作中,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各行其道的方法。(5)“休克法”:指在舞蹈演出中,讓音樂驟停、驟起,將觀眾從審美疲勞中喚醒過來的方法。同時,歐教授還對舞蹈中使用音樂的三類方法,即“同步法”“異步法”“同異結(jié)合法”做了清晰的梳理和闡釋。
最后,歐教授由對于舞蹈與音樂關(guān)系的詮釋引發(fā)了對其創(chuàng)作的思考。“無論在舞蹈與音樂之間的關(guān)系上有多少種不同的觀點,無論在舞蹈中對音樂的使用上有多少種不同的方法,使這兩種藝術(shù)親密互動,在潛心學(xué)習(xí)并熟練運用傳統(tǒng)舞蹈與音樂的標(biāo)準(zhǔn)化語言和經(jīng)典性審美的基礎(chǔ)上‘適度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出技術(shù)精湛、令人驚艷,藝術(shù)精深、感人肺腑,制作精良、使人愉悅,傳達(dá)全人類共有的價值觀和審美觀,經(jīng)得起時間考驗的經(jīng)典作品,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
此外,歐教授在發(fā)言中還精心地選擇了多個有代表性的舞蹈音樂錄像視頻,形象地闡釋他的論點,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中兩個視頻。一個是芭蕾舞劇《天鵝湖》中王子與白天鵝雙人舞的小提琴獨奏的一段音樂,唯美曼妙,如歌如訴,舞蹈與音樂配合得天衣無縫;另一個是運用法國作曲家拉威爾的管弦樂作品《鮑萊羅》作為舞蹈音樂的男子舞蹈,從領(lǐng)舞者的獨舞開始,到最后的幾十個群舞者的全部加入,完全與音樂的曲式結(jié)構(gòu)契合,體現(xiàn)了一種與音樂表現(xiàn)密切相符的壯勇陽剛之美。歐教授以這種形象地佐證方法給大家?guī)砹松疃鹊母行詻_擊和體驗,也打動了所有的與會者。
鄧佑玲教授和歐建平教授的發(fā)言,帶我們重新審視了音樂與舞蹈的辯證關(guān)系。鄧教授更多地從學(xué)科建設(shè)的視角出發(fā),探索了音樂與舞蹈學(xué)在同一個學(xué)科框架下,如何進(jìn)行學(xué)科融合、科技整合的問題。而歐教授則以舞蹈音樂創(chuàng)作為前提,在傳統(tǒng)的舞蹈與音樂四種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引發(fā)了舞蹈與音樂結(jié)合方式和在舞蹈中使用音樂的方法的論述。兩位專家雖然研究的出發(fā)點不同,視角也各異,但相同的是對音樂與舞蹈融合思路的引領(lǐng)和探究。特別是鄧教授提出的可以從音樂與舞蹈學(xué)的共性切入,探索兩者諸如發(fā)生論、批評理論、方法論等共性問題,由此入手來構(gòu)建音樂與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體系的觀點,無疑為音樂與舞蹈學(xué)未來的學(xué)科融合之路指引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另外,在論及樹立中華藝術(shù)文化的自信與自覺方面,鄧佑玲教授的很多話語也是發(fā)人深省的。比如,她指出“文化自信是一種更基礎(chǔ)、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沒有本民族文化自覺地自信,就失卻了本民族文化發(fā)展內(nèi)生的動力,也就不具備傳播的影響力”。在中華文化五千年甚至更長的歷史中,流傳下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藝術(shù)寶藏“為現(xiàn)在的藝術(shù)教育、文藝創(chuàng)作、藝術(shù)生活、審美生活提供了足夠多的營養(yǎng)和養(yǎng)料”,我們有必要全力以赴地珍惜保護(hù)和開發(fā)利用之。發(fā)言中,鄧教授特別提及的增強學(xué)術(shù)理論和學(xué)科理論自信也是洞徹深刻的。她認(rèn)為,中華文化藝術(shù)中有一些獨特的范疇、概念、體系。如美學(xué)、藝術(shù)學(xué)本體論中的“意象”,審美體驗論中的“味”“悟”,藝術(shù)品評鑒賞論中的“品”“妙”、形與神、虛與實、似與不似、氣韻、風(fēng)骨,戲曲、舞蹈中的起范兒等。這類傳統(tǒng)的范疇和概念閃爍著傳統(tǒng)文化和哲學(xué)的智慧,在進(jìn)行學(xué)科理論建構(gòu)時應(yīng)充分重視和挖掘。鄧教授秉持的“我們的理論建設(shè)應(yīng)該建構(gòu)在自己文化的土壤上,應(yīng)該扎根”,這一學(xué)術(shù)觀念和思想得到了與會者的廣泛認(rèn)同和高度共鳴。
三、于深居落點觀繽紛世界:音樂與舞蹈學(xué)科構(gòu)架下的綜合研究
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舞蹈學(xué)院院長、舞蹈學(xué)研究專家于平教授的論題為《中國舞蹈原始發(fā)生的綜合研究》。于平教授認(rèn)為中國舞蹈的原始發(fā)生,雖然一直是舞蹈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但其研究狀況卻不盡人意,進(jìn)而于教授提出了基于這一課題的研究構(gòu)想:“舞蹈的原始發(fā)生是混沌初開時的綜合文化現(xiàn)象,需要有多重理論視角對其進(jìn)行綜合研究。”
于平教授的演講總體分為四個部分:一、“認(rèn)知建構(gòu)”與中國舞蹈原始發(fā)生的邏輯起點。二、“動力定型”與中國舞蹈原始發(fā)生的預(yù)成圖式。三、“集體表象”與中國舞蹈原始發(fā)生的圖騰崇拜。四、“意義指稱”與中國舞蹈原始發(fā)生的功能意蘊。
在第一部分,于教授根據(jù)皮亞杰認(rèn)知心理學(xué)中的“認(rèn)知建構(gòu)”理論,結(jié)合中國舞蹈史料提出了原初舞蹈者的活動指向和舞蹈的動態(tài)構(gòu)成最初是一個沒有分化的、完全整合的活動。第二部分,他又依據(jù)巴甫洛夫的運動生理學(xué)體系中的“動力定型”理論,指出在原始發(fā)生期的舞蹈動態(tài)主要(甚至全部)是人體的自然動態(tài),即自發(fā)的隨機行為的人體動態(tài),這種人體運動動力定型,主要受人的生理機能、生存環(huán)境、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習(xí)俗這四個方面的因素影響,其中最顯見的因素是生產(chǎn)方式。第三部分,于平教授借用列維·布留爾關(guān)于“集體表象”論述加深了我們對中國舞蹈原始發(fā)生之圖騰崇拜的理解。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解釋了所謂“集體表象”其實是集體對共同的宗教觀念構(gòu)成的一種表象的抽象化借代,這些表象的靈魂是“與共同本質(zhì)匯為一體的熱烈盼望和迫切要求,對保護(hù)神的狂熱呼吁”,并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圖騰集團(tuán)本身及個人與圖騰動物、植物存在互滲律,而互滲律則完全可以用來論證中國原始舞蹈與圖騰崇拜的密切關(guān)聯(lián)。第四部分,于教授運用了恩斯特·卡西爾的“意義指稱”理論考察了原始舞蹈的功能意蘊。
音樂學(xué)家、評論家居其宏教授的發(fā)言《音樂與舞蹈學(xué)構(gòu)架下綜合舞臺戲劇研究的困境與出路》,提出了他對綜合舞臺戲劇研究的深度思考。
居教授首先闡釋了綜合舞臺戲劇的綜合性及其研究的跨學(xué)科特質(zhì)。他指出,中國戲曲、歌劇、音樂劇和舞劇,是將現(xiàn)有的音樂、舞蹈、戲劇文學(xué)(包括詩歌)、舞臺美術(shù)、表導(dǎo)演藝術(shù)等多種藝術(shù)樣式和手段綜合起來,用以展現(xiàn)其高度綜合性的舞臺藝術(shù)魅力、表現(xiàn)一定戲劇目的的藝術(shù)樣式;是時間藝術(shù)與空間藝術(shù)、聽覺藝術(shù)和視覺藝術(shù)、表現(xiàn)藝術(shù)和再現(xiàn)藝術(shù)的高度綜合。正因為綜合舞臺戲劇的這種高度綜合性,對之所進(jìn)行的史論研究,在最典型的意義上,必然具有明顯的跨學(xué)科性質(zhì)。
其次,居教授還探究了傳統(tǒng)學(xué)科構(gòu)架下的綜合舞臺戲劇研究出現(xiàn)困境的根源。他認(rèn)為由于專業(yè)藝術(shù)教育的單科化,致使綜合舞臺戲劇研究也被單科化。在傳統(tǒng)學(xué)科構(gòu)架下——對戲曲的史論研究被歸入戲曲學(xué);對歌劇、音樂劇的史論研究被歸入音樂學(xué);對舞劇的史論研究被歸入舞蹈學(xué)。這種單科化的發(fā)展使綜合舞臺戲劇研究面臨著嚴(yán)重的困境。對創(chuàng)作實踐、史論研究及評論產(chǎn)生了嚴(yán)重的負(fù)面影響。
最后,居教授指明了綜合舞臺戲劇研究的出路。(1)依靠學(xué)者個人的跨學(xué)科積累與歷練。(2)開設(shè)碩士、博士生的跨學(xué)科教學(xué)。在有條件的院校,增設(shè)綜合舞臺戲劇研究方向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教學(xué),聯(lián)合多學(xué)科的學(xué)者擔(dān)任導(dǎo)師,開設(shè)相關(guān)的理論與實踐課程,經(jīng)過三至六年的教學(xué)實踐,為培養(yǎng)出跨學(xué)科、綜合性的研究和創(chuàng)作人才提供制度保障。(3)創(chuàng)立跨學(xué)科的綜合舞臺戲劇學(xué),將它從單科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提升到獨立的二級學(xué)科的平臺上,不再簡單依附于音樂學(xué)、舞蹈學(xué)、戲劇戲曲學(xué),從本科教學(xué)抓起,逐步拓展到碩士、博士學(xué)位教學(xué)和博士后工作站的合作研究,對綜合舞臺戲劇展開系統(tǒng)性、全方位、跨學(xué)科、多向度的教學(xué)和研究。只有這樣,綜合舞臺戲劇創(chuàng)作和研究評論才能得以全面發(fā)展、不斷地健康壯大。
于平教授與居其宏教授兩位專家都是聚焦于一個綜合文化現(xiàn)象和文化事物而形成理論多元、學(xué)科交叉的思考。中國舞蹈的原始發(fā)生表面看似乎是舞蹈史學(xué)問題,但若將其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去究其原因的話,則是一種紛繁復(fù)雜的事情。于平教授綜合運用了認(rèn)知心理學(xué)、生理運動學(xué)、原邏輯思維和語言哲學(xué)的研究成果,結(jié)合史料對中國舞蹈的原始發(fā)生進(jìn)行了多角度的探查考證,洞幽察微,析毫剖厘,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確實值得學(xué)者借鑒。居其宏教授長期從事歌劇音樂劇理論研究與評論工作,其根據(jù)多年的實踐研究經(jīng)驗,發(fā)現(xiàn)綜合舞臺戲劇研究由于自身的跨學(xué)科性質(zhì)在學(xué)科壁壘重重,界限森嚴(yán)的當(dāng)下,面臨嚴(yán)重困境,亟待解決。雖然在發(fā)言結(jié)尾居教授仍對舞臺戲劇研究的前景憂心忡忡,但其以學(xué)者的責(zé)任感振臂高呼的氣勢與魄力令聽者動容。
四、于深居落點思繽紛世界:學(xué)科中心與邊界拓展的省思
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研究員、南京藝術(shù)學(xué)院特聘教授伍國棟先生的發(fā)言題目為《繽紛世界與深居落點——音樂學(xué)學(xué)科的中心與歸宿》。
伍國棟教授以繽紛世界指代包括音樂學(xué)、舞蹈學(xué)在內(nèi)的社會科學(xué)研究,強調(diào)在這繽紛之中,各有本界也各有跨界,各有中心也各有邊緣。沒有本界和中心的學(xué)科,其早已不在。據(jù)此,他按照邏輯順序提出以下四個主旨判斷和命題。
第一,不同學(xué)科以不同對象劃界,形成了各自的學(xué)科歸屬。學(xué)科本界和論題中心的存在,是現(xiàn)化科學(xué)研究學(xué)科認(rèn)定的前提和歸宿,亦如自然界生物種群及具體對象分野,當(dāng)是文化構(gòu)成不同因素和多樣化展現(xiàn)的一種永恒。
第二,對象中心與歸宿是學(xué)科原點。學(xué)科理論建設(shè)需從原點出發(fā)然后再返回原點。學(xué)科并列并強調(diào)各自的中心與歸宿,是現(xiàn)代學(xué)科理論建設(shè)的基石,是逐步走向繽紛世界的原點。
第三,從原點進(jìn)入邊緣甚至越界是學(xué)科擴(kuò)展必然走勢。進(jìn)入論題邊緣甚至越界,是學(xué)科擴(kuò)展走勢的必然,但其性質(zhì)是論題中心的學(xué)術(shù)升級或再建新的交叉論題中心,并非是一種本界學(xué)科主位的消解。
第四,必須于音樂與舞蹈學(xué)理論的深居落點之處探尋繽紛世界的美麗。音樂學(xué)學(xué)科的理論研究,都需要認(rèn)定一個深居的落點——進(jìn)入新界后,需要回歸。藝術(shù)學(xué)研究落到實處,是其特殊性:技術(shù)型、表現(xiàn)型、實踐型使然。藝術(shù)理論需要藝術(shù)實踐支撐和闡釋。深居落點是學(xué)科趨向成熟之范式選擇,藝術(shù)家學(xué)術(shù)成功之經(jīng)驗總結(jié)。只有深居于此而不忘探尋繽紛世界之絢爛多彩才是研究之道。
伍國棟教授的發(fā)言從高處著眼,從全局出發(fā),是對本次研討會主題的一個提綱挈領(lǐng)式的總結(jié)。
在本次會議過程中,還安排了題為“交叉學(xué)科研究的國際視野”的東北師范大學(xué)音樂學(xué)院青年學(xué)者論壇,以及發(fā)言青年學(xué)者與參會專家討論交流環(huán)節(jié)。在青年學(xué)者論壇上,七位東北師大青年學(xué)者以不同的國際視角對音樂與舞蹈學(xué)的相關(guān)交叉學(xué)科提出了不同的建設(shè)構(gòu)想和學(xué)術(shù)主題思考。在討論交流環(huán)節(jié)中,首都師范大學(xué)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王安國首先作為主持人進(jìn)行即席發(fā)言,并對青年學(xué)者在論壇中的發(fā)言逐一點評,言近旨遠(yuǎn),句句直指問題,字字切中要害。而后,每位專家也依次從不同的角度對青年學(xué)者發(fā)言做出了評價,對其在論壇發(fā)言中所表現(xiàn)出的銳意進(jìn)取、探索開拓的膽識與勇氣一致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贊賞,但同時專家也對一些選題不夠嚴(yán)謹(jǐn)科學(xué)、內(nèi)容不夠集中凝練等問題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批評。
總體來說,本次會議是對音樂與舞蹈學(xué)理論層面有關(guān)學(xué)科交叉的意義與價值、定位與范疇、目的與方法的一次全面研討和深度思考。學(xué)科交叉與跨學(xué)科研究最早于20世紀(jì)的美國興起,隨后全世界開始掀起了交叉學(xué)科研究的熱浪。1985年,中國召開了“交叉科學(xué)大會”,之后“交叉學(xué)科”一詞逐漸在學(xué)術(shù)界廣為流傳。時至今日,交叉學(xué)科的發(fā)展與研究不斷普及學(xué)科交叉,成為當(dāng)代科學(xué)研究發(fā)展的一大趨勢和熱點。然而,對于音樂與舞蹈學(xué)這一新合并、建設(shè)不過六七年的學(xué)科來講,什么是真正意義上的學(xué)科交叉,如何限定音樂與舞蹈學(xué)學(xué)科交叉的內(nèi)涵和外延,怎樣進(jìn)行學(xué)科交叉,未來的學(xué)科交叉研究范式和具體研究方法如何創(chuàng)新等一系列的問題,都需要一代代研究者不斷地探索、分析和忖量。音樂與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交叉之路注定是艱辛而漫長的。
縱然前路曲折而幽遠(yuǎn),但只要明確目標(biāo)與方向,就會趨近真理而有所收獲。而對于音樂與舞蹈學(xué)這一學(xué)科進(jìn)行學(xué)科交叉目標(biāo)與方向的尋求與探究,正是本次研討會的最終意旨。從學(xué)科意義上來看,與其他學(xué)科相比較,音樂與舞蹈學(xué)的學(xué)科建成時間短,學(xué)科內(nèi)部亟待交融協(xié)作,學(xué)科外部亟待統(tǒng)整資源,內(nèi)外協(xié)調(diào)才能完成音樂與舞蹈學(xué)的承典與塑新。本次會議作為國內(nèi)難得的一次在音樂與舞蹈學(xué)這個一級學(xué)科構(gòu)架下,音樂和舞蹈專家共同參與的理論研討會,確實完成了定標(biāo)立向的歷史使命。通過與會學(xué)者的認(rèn)真研討及深層交流,不僅厘清了學(xué)科建設(shè)與發(fā)展的基本思路,加快了音樂與舞蹈學(xué)這一學(xué)科內(nèi)部與外部協(xié)調(diào)融合的步伐,對音樂與舞蹈學(xué)這一學(xué)科的整體建設(shè)和全面發(fā)展起到了良好的促進(jìn)和推動作用,其更重要的意義還在于通過幾位學(xué)術(shù)界權(quán)威專家的發(fā)言與交流,使廣大音樂學(xué)與舞蹈學(xué)研究者明晰了學(xué)科本位的堅守與在學(xué)科交叉點上創(chuàng)新的關(guān)系,為未來學(xué)科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途徑和道路做出了方向上的指引與導(dǎo)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