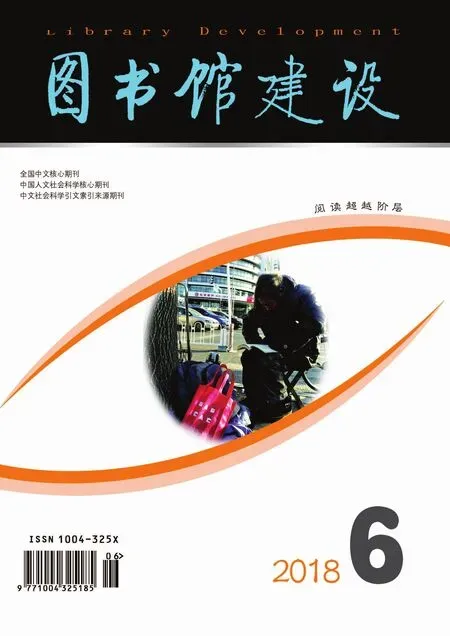論20世紀初日本在華所建四大圖書館的文化侵略功能*
王一心 (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文獻資料中心 江蘇 南京 210097)
1 引 言
日本的對華侵略,在軍事和經濟之外,從來沒有忽略旨在同化或奴化中國人民、削弱其民族精神、消弭其反抗斗志以便對占領地進行完全殖民統治的文化侵略。作為具有廣泛社會性的文化教育機構,圖書館在對華文化侵略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日本所重視。從在日租界設立居留民團,又于東北建立“滿洲國”到蠶食華北,日本政府將在華創辦圖書館作為文化滲透和文化侵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20世紀初的天津日本圖書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圖書館,還是抗戰全面爆發前夕的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上海近代科學圖書館,無不是在日本政府覬覦中國和朝鮮等國家而推行“日本大陸政策”的背景下建立的。其中,“滿鐵”圖書館更是“滿鐵”總裁后滕新平提出的“文裝的武備”殖民侵略思想的直接產物。隨著日本軍事侵略的逐步升級,在館藏、讀者服務、社會活動方面,這四大圖書館的文化侵略功能愈加顯著。
2 日本在華建立圖書館的歷史背景
2.1 日本大陸政策是日本侵華的根源
起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及持續了14年的侵華戰爭,是日本政府貫徹日本大陸政策的必然結果。所謂日本大陸政策,又稱大陸經略政策,即日本謀劃的自朝鮮、中國臺灣到中國東北、蒙古、中國華北、中國全境的分步驟侵略,進而吞并整個亞洲,繼而稱霸世界的侵略政策。作為19世紀中后期的日本基本國策,日本大陸政策的出籠,既與日本“以忠信、勇武為主要內容的封建主義倫理道德觀念的‘武士道’”[1]歷史傳統有關,更是日本明治維新后迅速走上近代化資本主義道路、軍國主義急劇膨脹而迫切對外擴張企圖雄踞亞洲之首乃至立于世界之巔的必然結果。
1895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這其實是日本實施日本大陸政策的一個重要步驟。戰后,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了澎湖列島和臺灣。1904年,為爭奪中國東北,也為繼續有效推進日本大陸政策,日本與俄國開戰。戰后,雙方簽訂《樸茨茅次和約》,日本從俄國手中奪得中國“南滿”地區的租借權[2]。之后,為了鞏固在東北的勢力范圍,以便日后將爪牙伸向中國關內,日本相繼在“南滿”地區設立關東都督府、“滿鐵”、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等殖民侵略機構[3],開始了對中國東北民眾殖民統治、奴化教育、思想滲透的文化侵略行為。
2.2 “文裝的武備”論是貫徹日本大陸政策的思想武器
表面上看,“滿鐵”是一家企業經營會社,實質上則是日本國家機關、政府的代行機構,是法學意義上的殖民會社。簡言之,它是為了執行日本大陸政策而特別設立的代行日本政府統治“南滿”的殖民機構。“滿鐵”首任總裁后藤新平是“文裝的武備”論的始作俑者,他認為殖民統治不應局限于經濟,還應該包括教育、衛生、文化等,“只有這樣,日本的大陸政策才能貫徹到滿洲民眾的生活中”[4]。所謂“文裝的武備”,其內涵是“以文事的措施,以備他日侵略之用”[5]。用他自己的話來解釋,也就是“揭王道之名以行霸道之實”[6]。
“文裝的武備”實施范圍無外乎宗教、衛生、教育、文化領域。僅就“文化”而言,“滿鐵”將其觸角伸及文化事業各個領域——出版、科研、社會團體、博物館及圖書館。從1907年“滿鐵”建立第一個圖書閱覽場開始,到“七七事變”爆發前,其在附屬地沿線一共建有31個規模不等的圖書館。無論是在開始時為在華日本人提供參考資料服務、滿足他們的精神需求,還是后來自覺承擔起宣傳日本文化、宣揚“大東亞共榮”和“五族(即漢族、日本族、蒙古族、滿族、朝鮮族)協和”的責任,再到全面抗戰后成為為侵略軍提供精神慰藉的服務場所、為戰事提供文獻資料的情報基地,“滿鐵”圖書館其實一直都在踐行“文裝的武備”的殖民思想。
2.3 “對支文化事業”的實質是文化侵略
1923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以此為標志正式開始推行在華文化事業,決定在北京設立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文化圖書館;在上海設立自然科學研究所。在華文化事業所使用的資金有兩個來源,一是應該退還給中國的“庚子賠款”,二是日本在英美的抵制下未能成功接收德國在山東的鐵路和礦產等方面多項權利而蠻橫無理地向中國強索的所謂“賠款”。也就是說,他們用中國人的錢在中國的土地上舉辦他們的文化事業。之所以說該文化事業是“他們的”,在于他們打著中日“合作”的旗號、宣稱該文化事業由雙方共同完成,卻在資金使用、人員配備、具體計劃等方方面面將所有權限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終使中國人認識到“對支文化事業”的真實目的是“伸張其國家行政權于中國領土,以肆其文化侵略,而懷柔中國人”[7]。
1936年5月,在日本制造挑起“華北事變”后,為應和蠶食華北的大計方針,日本外務省發布“對支文化事業”新規事業(又稱“新計劃”)。它“是日本為了配合即將全面發動的侵華戰爭而在文化事業上所做的方向性的調整”,其目的是使“對支文化事業”盡快擺脫“為學術而學術”的禁錮,而將其強行拉入政治和侵略的軌道;其內容是“中日之間,不必專事研究陳腐學問,或做考古學的研究,應先實行為中日兩國國民親善之工作。……實行有國際文化色彩的工作”,其中之一便是“在中國各地新設日本文化圖書館,積極介紹日本文化”[8]。在這種情況下,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上海近代科學圖書館相繼建立。
日本大陸政策是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上半葉日本的基本國策,根本目標是擴張和侵略。在此背景下,代行政府殖民統治的“滿鐵”應運而生。而為了貫徹“文裝的武備”“滿洲”殖民思想,附屬于“滿鐵”的“滿鐵”圖書館成立。“對支文化事業”是日本大陸政策指揮棒下的文化滲透方式之一,其“新計劃”更是作為所謂“親善”的工具,由此設立的北京、上海兩家近代科學圖書館不可避免地被賦予了政治的因素而無法保持文化的純粹。這樣歷史背景下建立的圖書館除了具備一般的收集、整理、保存、傳播文獻并提供利用的效用外,更多了一份文化侵略的功能。
3 圖書館的隸屬關系與人員構成
3.1 直隸政府決定了圖書館的非民間性
日本在中國建立的四大圖書館中,只有天津日本圖書館自稱是“自治團體”。事實上,該圖書館的確由生活在天津的10余位日本僑民聯合發起,于1905年8月7日成立。表面上看,它屬于民間組織,但實則與日本政府關系非同一般。第一,從日本政府的主觀意愿來說,欲使日租界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基地,故而必須注意對租界的管控,而對租界內包括圖書館在內的團體和組織也都務使“盡在掌握中”。第二,從圖書館常設委員、評議員構成看,“官員”不乏其人,其中官員評議員有16人之多,占評議員總人數的24.6%。第三,天津日本圖書館初建時,館址設在天津閘口日本俱樂部,而這個俱樂部是在日本駐天津領事的主持下成立的。第四,1907年8月,“大日本租界局”改為“居留民團”,天津日本圖書館劃歸其管理與經營,而居留民團直接聽命于日本總領事。這一切都顯示了該圖書館的日本官方背景,暴露了其與日本政府非同尋常的關系,也決定了它參與日本對華文化侵略的必然性。
如前如述,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上海近代科學圖書館是日本政府“對支文化事業”新計劃的產物,由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直接管轄。正如居留民團實則參與天津日本圖書館的館務——包括直接參與修訂《天津日本圖書館規程》《天津日本圖書館事務章程》《天津日本圖書館圖書閱覽細則》[9],兩家近代科學圖書館本身也沒有多少權力,文化事業部不僅在資金方面嚴格按照《對支文化事業特別會計法》的規定撥付,且嚴苛限制使用范圍,更插手館務工作,規定“圖書館館長、總務主任、司書、庶務、會計主任的任免必須經外務大臣的批準,圖書館助理、特聘人員的任免必須經總領事批準”①。而圖書館規程、經營方針的制定、修訂等必須由外務大臣批準;圖書館出版物必須經過外務大臣及北京、上海日本總領事審核;圖書館事務報告書、成績報告書、運營狀況必須定期提交給總領事等[10]。同樣地,“滿鐵”圖書館的管理規章也非由圖書館自身制定,隨著從“閱覽場”過渡到“簡易圖書館”又發展到“圖書館”,《圖書閱覽場規程》《簡易圖書館規程》《大連圖書館規則》等均由“滿鐵”會社制定。
日本在華建立圖書館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收藏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社會、產業、殖民、地方志、官方檔案、軍事材料等在內的一切關于中國的書籍、資料和情報,以便于其對中國的了解、認識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為蠶食、侵吞中國做文獻上的準備。因此,圖書館的任務是“用所藏圖書,配合當時的形勢發揮其作用”[11]。由此便不難理解“滿鐵”圖書館的隸屬關系——1906年,“滿鐵”成立;1907年,“滿鐵”圖書室籌建,隸屬“滿鐵”調查部;1908年12月,調查部更名調查課。顧名思義,調查部(課)是“滿鐵”所轄下的專門收集情報的調查機關,“從日俄戰爭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幾十年間,滿鐵調查部憑借從各方面收集到的大量情報資料,為日本有關方面制定侵華政策提供了方向和依據”[12]。顯然,“滿鐵”圖書館存在的價值,一是為調查部(課)進行情報資料調查提供文獻保障;二是為調查部(課)收集提交的6 000多份調查報告、出版發行的數千種圖書資料和雜志[8]進行專業的整理、分類和保存。
3.2 圖書館決策者官員占比高
無論是天津日本圖書館的評議員,還是“滿鐵”圖書館最早的創始人,抑或是各圖書館的館長,官員占比很高,而圖書館專業出身的微乎其微。除了神田城太郎(1920.2—1925.3)、佐竹義繼(1926.3—1926.5)、柿沼介(1926.5—1940.4)在加入“滿鐵”圖書館出任館長之前,分別在京都大學圖書館、京都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東京日比谷圖書館從事過圖書館專業工作以外,大多數館長從未與圖書館打過交道。“滿鐵”圖書館籌建者岡松參太郎有兩重身份,一是東京帝國大學法學教授、法學博士,一是“滿鐵”調查部(課)理事。事實上,“滿鐵”調查部(課)這樣的含有國家智庫性質的組織就是由他參與建立的。“滿鐵”圖書館既然隸屬調查部(課),那么,調查部(課)官員兼任圖書館館長似乎天經地義。先后擔任(或兼任)“滿鐵”圖書館館長的調查課官員有島田孝三郎(1918.1—1919.7)、唯根伊興(1919.7—1920.2)、水谷國一(1940.4—1941.3)、菊地池(1941.3—1942.2)、北川勝夫(1942.2—1945.8)等。
天津日本圖書館最初館務由常設委員(1943年1月29日改為圖書館委員)和評議員負責,不設專職館長。不少常設委員和評議員身份顯赫。常設委員主要有日本駐北京大使館官員奧田竹松、“大日本租界局”首任理事西村虎太郎等;主要評議員有日本駐天津總領事伊集院彥君、小幡酉吉。另外,至少還有兩名情報官員擔任評議員,一位是日本間諜特務機構內閣情報系統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負責人之一的阪西利八郎;一位是“日本老牌經濟特務”[13]吉田新七郎。
大量特殊身份的官員存在于圖書館事務中,勢必會強化對圖書館的思想控制,打破作為文化單位的圖書館的正常發展規律。出于維護本國政府利益的本能,官員們也會自覺地將圖書館視為文化侵略的輔助工具。
3.3 管理者的行為和思想傾向左右著圖書館的走向
由于職責所在,官員們總是習慣地竭力執行政府的決策,其行為難免利己(國)排他(國)。例如,從法學專業性上說,“滿鐵”圖書館籌建者岡松參太郎堪稱“法學大家”,撰寫過《注釋民法理由》《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論》等法學著作,“在日本民法學史上留下重大貢獻”[14]。但他同時又利用法學專長配合時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臺灣民政長官后藤新平參與中國臺灣的殖民統治,不僅“提供臺灣舊慣調查事業及臺灣舊慣立法法理論基礎”,而且“致力將臺灣的舊慣一種‘前近代’的法律,改編入西歐法體系”[15]。天津日本圖書館的評議員伊集院、小幡酉吉憑借其天津總領事的身份,以自己對所駐國的了解,竭力找尋為本國謀取更多利益的機會,而罔顧所駐國利益。前者于1903年4月代表日本政府與天津海關道唐紹儀簽訂《天津日本租界推廣條約》,強迫清政府對之前日本非法擴占的中國土地予以承認;后者于駐華大使參贊任內,在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時,協助公使日置益頻向中國施加壓力。
在圖書館決策和管理人中,不乏對中國深懷偏見之人。天津日本圖書館首任常設委員之一的奧田竹松曾經撰文《我觀清國人》,對大和民族懷有強烈的優越感,反過來對中國人極其厭惡,認為中國人只有個人主義而缺乏國家觀念,甚至將中國人列為“利之念熾盛之人種”“對利害計算極敏銳之人種”“膽怯懦弱之人種”,最終得出“固陋保守,難以改易”的結論[16]。常設委員、評議員、館長們多有反華傾向,因而積極支持或配合日本政府的侵華政策。上海近代科學圖書館首任館長上崎孝之助原是東京朝日經濟部次長,與圖書館從來沒有過關系,只因為對日本侵華“持積極意見”[17]而被推送上館長之位。
“九一八”和“七七”事變的爆發可謂一面照妖鏡,它將侵略者或支持侵略者的面目展現在世人面前。“滿鐵”圖書館奉天館館長衛藤利夫是“五族協和”思想的積極擁護者,他為“九一八”事變后奉天圖書館一改讀書消遣的文化場所而變為“王道思想的討論場、國家哲學的大熔爐”興奮不已,而把“滿洲國”的建立視為“宏偉的事業”,積極建議關東軍司令把以日俄戰爭為題材、宣揚日本武士精神的小說《肉彈》(櫻井忠溫著)的英文、法文譯本贈送給駐沈陽的上層外國人,為的是給他們“進行一次有效的歷史啟蒙”[18],從而為日本挑起戰爭辯護。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館長山室三良在“七七”事變后,撰文將事變之所以發生栽贓到中國人的身上:“考其根因,實由中國未能了解日本之真意,提攜未克實現有以致之。”[19]
決策和管理者們如此行為和思想無不與日本侵華政策同步,由他們掌管的圖書館自然不會只是“知識的海洋”那么簡單,參與文化侵略并為軍事侵略服務隨著戰爭的升級而成為圖書館的主業。
4 為文化侵略提供服務的館藏建設
4.1 服務對象的不同對館藏的影響
文獻是圖書館的物質基礎,因此,藏書被認為是圖書館的五大要素之一。無論日本在華創辦圖書館潛藏何種居心,藏書建設總是各類圖書館的基本工作。從藏書本身來說,它們雖然多半并不具有侵略屬性,但這不妨礙被懷揣侵略目的的人刻意利用。換言之,館藏文獻的作用因人而異,知識的載體也可以被用來當作工具或武器。這在日本在華創辦的四大圖書館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相對來說,天津日本圖書館、“滿鐵”圖書館建立較早,服務對象分別以在華日本僑民、“滿鐵”會社成員為主。天津日本圖書館由于經費的限制,館藏以接受捐贈為主,這使館方難以確立文獻資源建設方針,難以確定文獻收藏原則、范圍、重點,難以實施購藏標準,而只能停留在捐贈者捐贈什么、圖書館就收藏什么的隨意性、被動性、低層次館藏水平上。既然該館服務對象著眼于日本僑民,而樂意捐贈藏書的也是日本人,故館藏以日文書刊為主。來自在華與日本各地的機構與個人所捐贈的書刊的內容,當然與捐贈者的思想傾向、一己私好與個人趣味有關,他們的反華情緒對所捐書刊的品種當然有直接影響。在這些日文館藏中,意識形態意味比較濃重。這主要是軍國主義意識是當時日本的思想主流,日本大量的出版物要么是此類宣傳品,要么其中挾帶此類意識,要么為此做外圍與基礎服務。這類書刊的大量入藏,無疑強化了在華日本僑民的軍國主義思想,加劇了他們對中國的敵對態度。隨著中日關系的日趨緊張,日本加快侵華步伐,官吏、軍人讀者急速增加,館藏中有關中國方面的書籍隨之增多。“根據有關居留民團事務年報歷年閱覽圖書各類的統計,有關中國的圖書大都占據第二位,甚至有的年份還占據第一位”[20]。由館藏的變化可以發現,天津日本圖書館為文化侵略服務的程度是逐漸增強的。
“滿鐵”圖書館從在大連設立圖書室開始就被定位于為“滿鐵”會社成員提供業務參考、調查研究的場所[21],因此館藏側重文獻的收集,主要內容包括東北地區民俗風情、地形地貌、礦產資源等,涉及鐵道、礦山、港灣、產業、教育、衛生、工學、文學、政治、經濟、地理、歷史等方方面面,以日、漢、英3種語言為主。隨著“滿鐵”圖書館的不斷擴張,圖書館遍布東北鐵路沿線,除了大連,奉天、鐵嶺、開源、四平、公主嶺、長春、本溪、撫順、沙河口等地均設有圖書館。為了方便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為了更好地認識和了解中國以便日后占領和殖民統治,“滿鐵”對各個圖書館的館藏進行了功能分區。例如,最大、最主要的“滿鐵”大連圖書館側重“收集普通圖書,同時收集官方的檔案以及軍事機密材料”;奉天圖書館“主要收集古籍珍、善本和中國各地的重要方志”;長春圖書館“以收集東北地方文獻為主”;哈爾濱圖書館“重點收集有關滿蒙的俄文文獻資料以及有關蘇聯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文獻,特別是關于遠東地區的文獻”[22],等等。
天津日本圖書館和“滿鐵”圖書館都有為特殊人群提供專門館藏的服務。所謂“特殊人群”,主要指政府官員、高級軍人、“滿鐵”的上層職員、關東廳和關東軍機關的要員等。他們都持有“特殊閱覽證”。這種閱覽證不僅需經本人申請、所在單位批準,還要經過圖書館的審查核準,因此不是一般讀者所能得到的。以“滿鐵”圖書館為例,持有特殊閱覽證的特殊人群可以進入圖書館專設的“滿蒙”“殖民”“交通”3個內部參考閱覽室[23]。這樣的“特殊服務”,無論是閱覽者的“特殊”,還是館藏的“特殊”,都已超出單純的學術范圍,而與侵略緊密相連。
4.2 為特殊目的而進行的館藏建設
在以侵華為目標的日本大陸政策背景下建立圖書館,其目的性顯而易見。抗戰爆發前,“滿鐵”圖書館為了配合“滿鐵”對“南滿洲”進行殖民統治,規定其自身的任務是“廣泛搜集古今中外圖書資料,供給‘會社’業務的參考”[24]。因此,該館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地質資源、風土人情,特別是東北的地方志、地圖以及政府機構出版的一般不經售的重要調查資料是垂涎三尺”[25]。不限東北地區的“地方志”是“滿鐵”圖書館的重點館藏之一,它從“圖書室”時期便開始注重搜集,在很短的時間內便“搜集到中國各省通志、府縣志700部”[26]。1923年2月,該館獲專款用于采購地方志、地圖、圖繪、稿冊、非公開發售的油印本縣志、村志等[27]。經過十幾年持續不斷的搜購,僅“滿鐵”大連圖書館收藏的方志,1940年時便已高達2 300余部[28],數量驚人。如此不遺巨細地對于地方志的搜求,只為了對中國各地進行深入毛細血管的徹底研究。天津日本圖書館也自詡對中國縣志的收集是其館藏的“一大特色”。他們很早開始搜集以河北省為中心的中國北方各省的地方志,而以河北省地方志的收集最見成效。
為積極介紹日本文化而設立的北京、上海兩家近代科學圖書館,其運營當然以此為中心,所明確的目的也是“向中國學者、學生等人士介紹日本自然科學發達程度、最新發明發現、人文科學及其他日本事情”[10]。既然圖書館標明“科學”二字,那么,館藏必然偏向科學類,又以自然科學為主,涵蓋醫學、產業、工農業等,占比達70%,“人文科學書籍占百分之三十”[29]。既然以介紹日本先進文明為目的,館藏中的日文書刊自然占據主流。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開館之初,“以三萬五千元日金向日訂購各種科學書籍四五千種”[29]。在平時的館藏建設中,日本權威學者的著作、有關日本歷史產業文學等方面的最新著述、日本新聞報紙雜志、日本人述及關于中國的中國學論著、日譯歐美書籍等都是重點搜購的目標[10]。“七七”事變后,圖書館“為應其勢所趨,復多備有日本語學書及辭典等之副本,以供其需要”[30]。在日文館藏方面,“滿鐵”圖書館同樣重視有加。據不完全統計,僅“滿鐵”大連圖書館所藏日文圖書資料就高達94 115種、179 416冊,其中雜志1 906種、22 017冊,報紙104種[23]。
對于日本在華建立的圖書館來說,在藏書的語種方面,中文和日文各有用處,廣泛搜集中文古籍線裝書,乃出于對中國珍貴典籍的占有目的;將中國地方志列為所欲竭力搜求的館藏,其動機更是不言自明。因為地方志含有一區一地極為豐富的信息,是情報來源的重要渠道之一,尤其是在戰爭狀態下,地方志收集的意義不只可為經濟文化侵略提供幫助,甚至可為軍事侵略提供直接幫助;文化滲透少不了植入本國語言和文化,日文書籍便承載了這一使命。總之,這四大圖書館的館藏建設超越了公共圖書館以提供正當的學術研究和健康的精神食糧為己任的一般屬性,而多了一份輔助文化侵略的功能。
5 圖書館參與文化侵略的主要活動
5.1 舉辦日語學校進行日語教學
文化侵略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侵略者在被占領國推行己國語言。作為社會教育機構之一的日本在華建立的圖書館,有意識參與傳播和宣傳本國語言的方式,一是將日本書刊作為館藏建設的重點;一是推行日語教育、開設日語學校。在開辦日語學校方面,四大圖書館都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
1942年11月,天津日本圖書館開始在雇傭的華人職員中實行日語教學試驗。在獲取一定經驗后,于1943年7月開辦日語講習課,按照受教者日語掌握的程度,分為初等部、中等部,每周進行兩次教學[31]。1938年6月,上海近代科學圖書館針對中國普通民眾舉辦日語學習班。學習班規模不斷擴大,以至于次年4月改為圖書館附屬日語學校,也設初、中級兩個班,教員由本館日本職員擔任,教材以日本東亞學校主編的《日本語讀本》為主[32]。
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更將日語教育作為圖書館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方式是[19]:(1)設立日語學校。它在東城、西城、北城開設了3間日語學校,所用教材是自己組織人員編寫的《日文模范教科書》6卷、《日文補充讀本》6卷。學校以短期培訓班為主,學習期限3到6個月不等。(2)舉辦日語講座。“七七”事變后,北京的日偽電臺有專門的日語教學節目。該館不但在閱覽室里專門配備收音機供閱覽者收聽,而且還在節目結束后進行補充教學講座。1937年11月,圖書館特別聘請大學教授、文化學者開設日語基礎講座。(3)開設師范科。為培養更多的日語教員,該館開設師范科,招收有一定日文基礎的中國學生入學,學習期限6個月。(4)舉辦日語研究會。這是該館“把日語教育提升到專業學校級別”的措施之一,招生對象是日語程度達到一定高度的人。該會每周舉辦1次,時間90分鐘,3個月為1期。
如此熱衷推廣日本語,其目的當然并非如日本人自己所說的“用博日華親善之好轉,……且為一般學術及現代文化之要素”[30],而是企圖將日本文化強行輸入以便同化、奴役中國人。
5.2 舉辦展覽和演講宣傳“圣戰”
日本全面侵華后,中國人民奮起反抗,中日關系陷入冰點。為給中國人民群情激昂的反日情緒降溫,減少日本侵華的阻力,四大圖書館通過舉辦展覽和演講,以及制造輿論的方式為日軍侵略行為辯護,竭力宣傳“圣戰”,美化“中日親善”。
“滿鐵”圖書館的展覽從來都緊跟侵略形勢。“九一八”事變前,他們為配合日本占領東北和內蒙,舉辦“滿蒙研究資料展覽會”(1926.11)、“支那民族研究資料展覽會”(1930.10);事變后,則舉辦了反映關東軍占領熱河的“熱河文獻圖繪展覽會”(1933.5)、展示日軍侵略華北的“華北文獻展覽會”(1935)等。天津日本圖書館也不例外,1938年10月21日和25日,廣州、武漢先后被日軍攻陷后,該館不但用“午后休館”的方式加以慶祝,而且還于11月10日至13日,連續舉辦了4天圖書展覽,其主題的關鍵詞為:“支那事變”“中國情況”“日本精神”“國民精神的喚起”[33]。選擇這個時候舉辦這樣的展覽,其用心顯而易見。不僅如此,在“日俄戰爭”結束35周年的1940年,該館選擇在3月10日“陸軍紀念日”那天又舉辦了一場展覽,陳列了關于這場戰爭的相關圖書120部,以及印章、書畫、圖片、明信片等100多件實物[34],全然不顧東北人民因該戰爭而遭受的深重災難。
上海近代科學圖書館舉辦的展覽主要有:1940年12月14—27日的“近代日本文學展覽會”。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舉辦的展覽主要有:1938年12月10—15日的“日本中小學生兒童書畫展覽會”和“日本生活風景寫真展覽會”,1942年12月6—11日的“大東亞戰爭一周年紀念展覽會”,以及“日本藝術寫真展覽會”“北支蒙疆全貌展覽會”等,不但大力弘揚日本文化,而且為戰爭添粉抹彩。
口頭與文字鼓動當然也都是宣傳的有效方式。天津日本圖書館籌劃的天津讀書會在3年時間里舉辦過30場演講,演講者的身份有些是日本軍政界頭面人物,演講的內容有政治目光下的世界大勢與格局,有對皇道精神的宣傳,有日本必勝、在華日本人負有重大使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鼓動,有如何進行大東亞建設的講解等。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滿鐵”圖書館則利用館辦期刊《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館刊》《書香》進行“日本文化”和“圣戰”宣傳。《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刊》上刊登的《日本語與日本精神》對日本文化極盡贊美之辭。《書香》第26號發表的《滿洲圖書館的使命》、第33號發表的《時局與圖書館》、第39號發表的《滿洲事變與圖書館》等文章直言圖書館和圖書館創辦的刊物要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工具,要負有向中國人民宣揚“王道”思想的使命,“要從時局相密切的立場出發”[35]。“九一八”后,《書香》更專辟“事變”專欄,刊登《滿洲事變與世界正體》等一系列文章,以及軍部書信等,毫無愧怍地為侵略戰爭代言。
5.3 直接為軍事侵略提供服務
5.3.1 為侵略者提供地圖服務
地圖無疑是軍事侵略中必不可少的情報資料。“九一八”事變前,“滿鐵”圖書館向“滿鐵”會社提供了從中國搶奪的中國陸軍測量局制作的五萬分之一至十萬分之一的地圖。會社將其復印了2 000份,分發到各省[22]。日軍制造“九一八”事變,這些地圖發揮了很大作用。“滿鐵”奉天圖書館館長衛藤利夫親口說過一個“故事”:“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東北政府所在地臨時遷往錦州,日本軍隊仍然緊追不舍。一個夜晚,一位關東軍青年參謀來到奉天圖書館,查找中國出版的遼西地圖,該館平日積累的中國東北各地地方志派上了用場[36]。
5.3.2 為侵略者提供查閱資料的便利
曾經有3個日本特務深夜趕到“滿鐵”奉天圖書館要求查閱有關“黑龍江洲教育制度”的資料,館長衛藤利夫竭盡全力提供幫助,不但暖氣徹夜不斷,電燈整夜不滅,而且一直親自陪伴。“九一八”事變后,“滿鐵”圖書館以大連圖書館為中心,由24個圖書館共同參與,編制了《全滿二十四圖書館共通滿洲關系和漢書件名目錄》,免費贈送給關東軍等機構,為他們查閱資料提供方便。衛藤利夫不無得意地夸耀說:“你所要查找的題目,比如說礦山,或者大豆……只要用電報把書號傳送去,下一次列車無論停靠何處,都可以拿到書。”[37]除此之外,各個圖書館還從本館藏書中選出與戰事有關的圖書,編成“時局文庫”專供關東軍用于情報分析。
5.3.3 為侵略者提供精神慰藉
“滿鐵”圖書館一直都有以書籍作為精神慰藉產品的傳統,其慰藉的對象當然是長期離鄉背井的軍人。早在1918年9月,“滿鐵”圖書館便建立過“戰時巡回書庫”用以慰問西伯利亞派遣軍。“九一八”事變后,1931年12月19日,“滿鐵”圖書館發出募集圖書雜志倡議,其目的如《陣中文庫宗旨》所言,是為了對前線的戰士進行精神慰安。短短半年時間,“滿鐵”所屬各圖書館共收到捐贈書刊12萬冊。經過軍部的審查篩選,最后確定將109 800多冊組成“陣中文庫”送往前線[22]。天津日本圖書館也在抗戰期間組織過“巡回文庫”活動,軍隊是他們的“巡回”目的地之一。“七七”事變爆發,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即刻啟動“前線慰問文庫”,精心挑選文學類、時局類、娛樂類、實用類等圖書送往前線,用來“滿足皇軍諸將士戰斗閑暇之余閱讀,以了解有關支那的基本知識,增進對本邦歷史、文化等的再認識”②。
5.3.4 參與整理軍隊掠奪的圖書
1937年下半年,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后,在日軍特務部的直接安排下,由15名委員組成的“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和“占領地區學術資料委員會”成立,專門負責對華東淪陷區日軍掠奪來的珍貴古籍、有價值的文獻資料進行接收和保存。其后,“滿鐵”圖書館派出6名圖書館員和調查員于1938年7月和8月到南京對接收圖書進行整理,其中包括“滿鐵”大連圖書館書目部主任大佐三四五和館員青木實。而天津日本圖書館則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對日軍掠奪的文獻資料進行接收和整理。為此,他們在天津防衛司令部的安排下于1942年12月組織成立“軍隊管理圖書整理委員會”,對太平洋戰爭前英國工部局圖書館約13 000冊圖書、英租界維多利亞道上的天津俱樂部圖書室約9 000冊圖書、商務印書館附設的上海東方圖書館約22 000冊圖書以及來自所謂“敵性倉庫”的287冊圖書進行甄別處理[38]。這一切都表明這些圖書館已經由輔助文化侵略轉化為直接為軍事侵略服務。
6 結 語
日本在華建立的圖書館,其主要任務是用圖書館所藏圖書資料發揮情報參考作用。早期,它表現在大量購藏漢籍、典籍和地方文獻,為日本政府了解中國形態地貌、物產資源提供文獻支持 ;后期,隨著軍事侵略的進一步擴張,圖書館一來以其占據大量圖書資料的優勢自然成為情報中心,二來圖書館的工作重心也轉向對侵略者提供信息情報服務。除此之外,圖書館除了收藏中國文獻外,也大量引進宣傳日本文化、展示其先進文明發展成果的日文圖書資料,目的自然是為了文化滲透。為配合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圖書館還積極開辦日語短期培訓班,從而使其又變身為軍國主義的宣傳教育基地。全面抗戰爆發后,圖書館舉辦“陣中文庫”等活動,送書上前線以滿足侵略軍的所謂精神需求從而達到“慰藉”目的。由此可見,在戰爭環境下,原本單純的只是用來提供給人們精神食糧的圖書館也被日本侵略者利用而賦予侵略功能,使其淪為文化侵略的工具。
注 釋:
①來源于日本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北平近代科學圖書館關系雜件(經費關系 第二卷)”中的《館命令書》。
②來源于日本東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寄贈圖書報告(昭和十三年八月)》。
[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2015:23.
[2]何 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
[3]易顯石“.九·一八”事變史[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60.
[4]CCTV《走近科學》編輯部.二戰紀實: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紀實[G].成都:巴蜀書社, 2014:82.
[5]張素玢.臺灣的日本農業移民(1905-1945):以官營移民為中心[M].臺北“:國史館”, 2001:409.
[6]呂芳上.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1:和戰抉擇[M].臺北“:國史館”,2015:29.
[7]教育界反對日本文化侵略之宣言[J].中華教育界,1925,15(2):3.
[8]王向遠.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M].北京:昆侖出版社, 2015:213.
[9]天津日本居留民團立日本圖書館規程[G]//天津日本居留民團.現行法規匯編.[出版地不詳]:[出版社不詳],1926:172.
[10]石 嘉.抗戰時期日本在華北的文化侵略:以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為例[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7:23-31.
[11]楊力生.滿鐵大連圖書館[G]//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寧省大連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大連文史資料:第1輯.大連: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遼寧省大連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84:11.
[12]謝環環.滿鐵的“大腦”——滿鐵調查部[J].百科知識,2016(18): 55.
[13]孫立民,辛公顯.天津日租界概況[G]//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8輯.天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82:132.
[14]田口正樹.岡松參太郎與日本統治下之臺灣舊慣調查[C].小林貴典, 譯.//“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基礎法學中心.法文化研究(二):歷史與創新.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6:80.
[15]吳豪人.岡松參太郎論——殖民地法學者的近代性認識[C]//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編輯委員會.戰斗的法律人: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4:512.
[16]呂順長.清末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之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368-375.
[17]山根幸夫.東方文化事業的歷史[M].東京:汲古書院, 2005:175.
[18]王中忱.走讀記:中國與日本之間[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186-187.
[19]王 燕.抗戰時期的北平近代科學圖書館[J].蘭臺世界, 2016:87-91.
[20]萬魯建.天津日本圖書館述略[J].圖書館工作與研究, 2006(5):76.
[21]冷繡錦.“滿鐵”圖書館研究[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1:31.
[22]李 娜, 王玉芹.滿鐵圖書館的職能及其在東北的侵略活動[J].日本學論壇, 2008(3):66.
[23]程憲宇.滿鐵大連圖書館史略[C]//第一屆圖書館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出版地不詳]:[出版社不詳],2006:15-17.
[24]楊力生, 王泯虬.日寇侵略東北時期偽滿鐵大連圖書館史料[J].圖書館學研究, 1982(6):105.
[25]張海齊.偽滿鐵圖書館的圖書搜集方式及其危害[J].圖書館學研究, 1983(6):129.
[26]巴兆祥.中國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9.
[27]李曉菲“.滿鐵圖書館”及其帶給我們的啟示[J].圖書館建設,1998(1):74.
[28]韓俊英“.大谷文庫”藏書初探[J].日本研究, 1994(2):92.
[29]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部在平設科學圖書館[N].大公報, 1936-11-01.
[30]日本語講習會[J].北京近代科學圖書館館刊,1937(2):186.
[31]天津日本圖書館.華人傭人日語講習實施[G]//天津居留民團.昭和十八年事務報告書.[出版地不詳]:[出版社不詳], 1943:76.
[32]石 嘉.抗戰時期日本在上海的文化侵略:以上海日本近代科學圖書館為例[J].江蘇社會科學, 2015(1):223.
[33]天津日本圖書館.特記事項-日記雜抄[G]//天津居留民團.昭和十三年民團事務報告書.[出版地不詳]:[出版社不詳], 1938:150.
[34]天津日本圖書館.日露戰役資料展覽會[G]//(日)天津居留民團.昭和十五年民團事務報告書.[出版地不詳]:[出版社不詳],1940:559.
[35]“滿鐵”大連圖書館.滿鐵圖書館的使命[J].書香, 第26號.
[36]衛藤利夫.滿洲事變與圖書館[J].書香, 第39號.
[37]王中忱.滿鐵圖書館遺事[J].博覽群書, 2005(6):48-50.
[38]天津日本圖書館.軍管理圖書整理[G]//天津居留民團.昭和十八年事務報告書.[出版地不詳]:[出版社不詳],194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