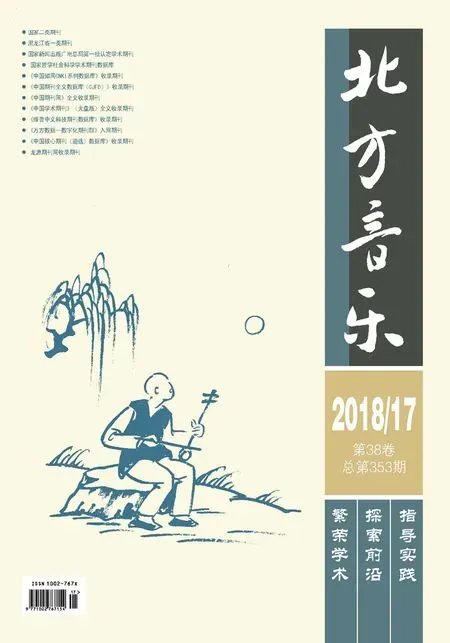論聲樂表演中二度創造的價值體現
陳香瑩
(四川音樂學院,四川 成都 610000)
一、二度創造與聲樂作品解釋的審美關聯
聲樂表演藝術活動,離不開聲樂作品解釋和二度創造這兩個環節。由于詞曲作者的想法并不能完全直接呈現在作品之中,嚴格說來,當詞曲作家把生動的情思以歌曲作品的形式記錄下來的時候,就已經抽掉了它活的靈魂,所剩下的不過是沒有生命的文字語言和樂音符號系列。要使作品重獲生命,這就要求演唱者首先對作品進行解釋,把詞曲作者的隱含意圖揭示出來,同時還要科學地判斷作品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和個性心理因素,從而把握特定時期的人類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本質特征。在此基礎上所做的二度創造,才能最貼近作品的本質,豐富作品的情感表現力。
二度創造與歌曲原創的區別在于,體驗的不同。第一度創造者的體驗是有感于客觀世界的,是從心靈發動的體驗,是個體生命認識與生命意志的一種表征,這是一個主動性過程。而二度創造則是從作品發動的體驗,作品中的內容起了一種導游的作用,帶領歌者去體驗作品所表述的世界。歌者必須帶著自己的經驗、認知,帶著自己的審美觀念和價值取向進入第一度創造者的世界,在此體驗上做再次創造,這是一個被動的過程。
什么樣的體驗,決定著什么樣的二度創造。從文化的意義上看,聲樂作品解釋所表述的內容對于歌者來說,可能是完全陌生的經驗世界,也可能是很親切的經驗世界,無論是哪一種,只要是與歌者的生命趣味相適應,歌者就會從中獲得強烈的震撼性體驗。(之所以說歌者的知識越全面,生活經驗越豐富,就越能把握歌唱的情感表現就是這個道理。因為歌者總能從不同的作品世界中獲得強烈的體驗。)歌者會很快把握住作品的情緒,會直接成為作品中情感的化身,會從中得到鼓舞,受到激勵,得到啟示。歌者的體驗此時雖含有個體的經驗,但更為重要的是,他已被聲樂作品解釋的內容所控制,完全沉浸在作品的世界中。從音樂的意義上看,再優秀的作曲家,使用再多的音樂表情術語都無法記錄出音樂運動的內在韻律和微妙變化,都無法顯示出聲音及頻率帶給人心理及精神的情緒反應和感受,更無法記錄下蘊含在音樂作品中的文化與音樂的因素巧妙結合所能展示與表現的種種情感和思緒。無論多偉大的作曲家寫下的曲譜都與他們的生活樂思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要使這種差距得到彌補,把這些隱藏的情思充分發掘,使樂譜無法展現的內容豐富起來,正如李漁所講:“變死音為活曲。”這一切都依賴于歌者的解釋——即最深沉的體驗。這個體驗過程是一個再生的過程,是一個領悟的過程,是一個審美超越的過程。
二、二度創造價值的實現
(一)二度創作的技巧運用
聲樂表演藝術是一種非常精確、細致、靈活,需要有高度表演技巧的創造行為。如果沒有高度的本專業的基本表演技巧的支撐,無論多好的音樂設想也不可能得到實現。因此說,二度創造需要借助專業技巧來表現,你所掌握的技巧能否承載你對作品二度創造的分量,應是一個重要問題。成功的聲樂表演離不開嫻熟的演唱技巧,歌唱技術的掌握和運用,如發聲方法、氣息控制、吐字行腔等,對于歌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對作品解釋得再透徹,對作品進行再精彩的二度創造構想,最終得靠演唱來實現。因此,技巧是實現二度創造的根本。
之所以說歌唱技巧而不是說歌唱技能,是因為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歌唱技能”是指掌握和運用歌唱這項技術的能力;而“歌唱技巧”則是指巧妙地運用歌唱技術的能力。前者不一定包含后者。就像一些歌者,其實已具備了演唱的能力,能順利地完成作品,甚至是難度較大的作品,展示出了扎實的基本功。但是,這種歌聲里總讓人覺得少了點什么,少了那么點“味兒”。這個歌唱的“味兒”其實就是靠“歌唱技巧”來抒發的。沒有技巧的運用,也就沒有歌唱的“味兒”。這種技巧的運用,能使作品的處理更細膩,情感更豐富,使歌聲更動聽。
因此,對于聲樂的二度創造而言,更為重要的是把基本技術靈活運用于歌曲藝術表現的能力,或者說是根據歌曲藝術表現的需要,創造性地運用基本技術的能力,這就是“歌唱技巧”的意義所在。例如,歌劇《白毛女》選段——《恨似高山仇似海》,其中有“雷暴雨翻天我又來”一句,為了表現一種憤怒的力量和傷痛悲哀情緒,“雷暴雨翻天”幾個字唱得鏗鏘有力,而這個“來”字的唱腔則可以運用戲曲里的技巧,帶哭腔去表現,在力度和情緒上形成對比。再有,“我是叫你們糟蹋的喜兒,我是人”一句,這里要用連說帶唱的技巧來體現一種悲怨的情緒。又如作品《血里火里又還魂》里的一句“雨啊紛紛的下,打在臉上冷透心”,民族唱法的音色是明亮的,但明亮的音色不足以表達某些很含蓄、內在、深層的情感,所以當唱到“冷透心”三個字的時候,可以多一些氣聲,虛一點,暗一點,表達這種凄慘的境況。我們在二度創造中對中國聲樂作品進行這樣的技巧處理,是不被西方音樂體系認同的,因為“音色、狀態不統一”。但是在中國卻被廣泛應用,這種多變化的音色正符合中國人的審美,能更直觀地體現情感。所以,同樣一種現象,因為不同的美學系統,就會得到不同的價值判斷。比起西方,中國的音樂是多元的,而在西方,它對音色的講究,比較趨向唯一的,某種特定美的追求。如唱中國聲樂作品的時候要更靈活,力度的強弱,情緒的緩急,音色的明暗,還有潤腔等,這些技巧的靈活運用都是必不可少的。這就要求在聲樂作品解釋階段就能準確把握西方聲樂作品和中國聲樂作品各自的特點。
(二)二度創造的自由度
在聲樂演唱活動的整個過程中,歌者既是解釋者,也是二度創造者。作為一個解釋者需要歌者對待作品要理性,要嚴謹。可是,同又作為二度創造的歌者,怎樣對作品進行二度創造呢?二度創造跟第一度創造不同,二度創造受到第一度創造的限制,歌者的主觀意識必須服從客觀事實,必須認識到二度創造的自由度直接取決于歌者的基本價值立場,即二度創造不是為了“賣弄技巧”,而是為了求得對作品本身的深化。這需要一種科學認真的態度,在作品解釋的基礎上做出合理的情感創造。
例如,在對陜北民歌《蘭花花》里,其中的一句“你要死來你早早的死”進行二度創造的時候,普遍歌者都是把這里唱成一種“詛咒”的情緒。但是從作品背景所表達的內容來看,蘭花花是一個美麗、善良、有教養的姑娘。在這樣一種人物性格背景下,演唱這一句就不應該有那種“牙尖嘴利”的表現。在那個年代,很多男人患癆病,便以娶親的方式“沖喜”。因為家里窮,蘭花花被迫嫁給一個病懨懨的男人,主人公的情緒應該是既嘆息自己的命運又可憐那個半死不活的男人。她期待他早死早了,自己才能得以逃脫。在這樣一種情緒下,這一句的演唱是無奈,是委屈,是可憐,是期待,所以,不能唱得那么硬,否則出現在大家面前的便是一個“尖酸刻薄”的聲音形象。
自由的二度創造本身是藝術實踐和演唱技巧乃至藝術勇氣達到一定水平的產物。創造的自由絕對不是“初學者或外行的胡作非為”,更不是“任性的生理沖動的產物”,可以說不經過訓練或不具備成熟的演唱技巧就不可能有二度創造的自由。而具備了一定的演唱技巧又確實需要自由地二度創造。在這個條件下,自由的二度創造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對作品的不完善之處進行突破。聲樂作品畢竟是用文字和音樂符號創作出來,呈現出的是一個總體的音樂感覺設想,在很多細致的地方,給歌者提供了二度創造的空間,使之可以在這些地方對作品進行個性化創造,從而達到對作品地審美價值的突破。二是對經典演唱的突破。在優秀歌曲的傳承過程中,不自覺會形成某種形式的經典演唱,包括語言、音色情感等一系列技巧運用,大多數歌者自覺地遵守這種演唱模式,只是進行微小的變革,而對于有創作才能的歌者,他可以完全實現個人的藝術自由,甚至背離傳統或否定傳統,這種藝術革新常常需要以冒險作為代價,很多優秀的歌者通過這種冒險和反叛達成了藝術的自由,他們在艱苦訓練的基礎上確實做到了二度創造的自由,而且不在意別人的武斷或無理的評價。
三、結語
聲樂表演是一門涉及到音樂美學、和聲學、表演學、聲樂心理學等范圍的藝術學科,不僅需要我們對歌唱技能的刻苦學習,更需要我們對一切相關學科進行探索研究,尋找一切有價值的能為聲樂表演藝術所用的理論知識。演唱技能的訓練不能成為聲樂學習的最終目的,再精湛的技能也只是聲樂表演的工具而已。技能始終是為情感的表現服務的。脫離了情感,再高超的技術都不會使演唱生動感人。因此,在歌唱技能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對聲樂表演的理性思考就變得尤其重要。生來嗓子條件就好的人不少,歌唱技能好的人也不少,可真正能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能達到相當水準的歌唱家卻并不多。因為,真正的歌唱家所具備的,絕不只是不凡的演唱水平。聲樂界千軍萬馬的大軍,能到達鼎盛境界的又有多少呢?在演唱技能達到一定的水準后,需要的,更是一個聲樂演員的思想深度。
在這個充滿著競爭和壓力的社會,想要成為一名優秀的聲樂表演者,對自己進行全面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以前人們常說,“搞藝術的人是瘋子!”我們需要這種“瘋狂”,因為藝術需要激情,可激情不是藝術的全部,藝術需要我們去思考。當我們冷靜下來,認真地對自己所學的藝術專業進行試探性分析時,在藝術的感性層面掩蓋下看到了它閃爍著的理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