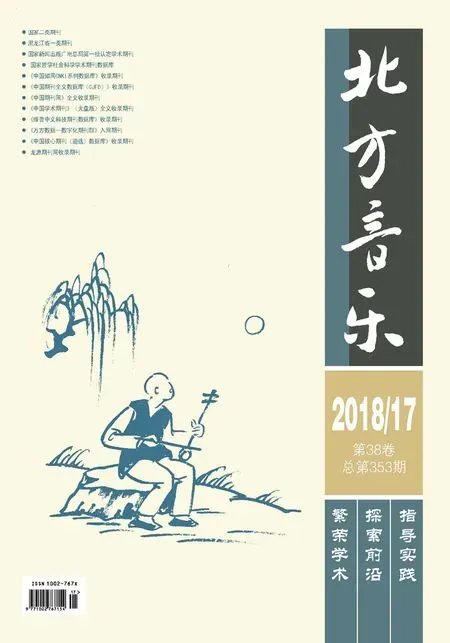聲樂演唱中“字”與“腔”的內在聯系
漆欣欣
(四川師范大學,四川 成都 610000)
一、語言在聲樂演唱中的重要性
語言是學習聲樂演唱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說把唱歌比作建筑,那么氣息是支撐的框架,語言就是堆砌在框架上的每一塊磚瓦。每咬一個字,都對歌唱時聲音的共鳴及位置有所影響,而聲樂演唱學習的過程,就是將這些語言全部裝進自己聲音的共鳴里,使它不跑出共鳴之外,只有這樣歌曲的表現力才會配合氣息發揮到極致,才能更好地演繹出每一首作品中鮮明的形象色彩,展現其藝術價值,從而打動人心。
自古以來就有許多音樂工作者對唱歌的音律、音韻及咬字作出了許多研究與貢獻。在元朝時燕南芝庵就作出了一部《唱論》,它可以說是中國現存最早的聲樂論著,它總結了前人歌唱藝術的實踐經驗,為研究中國宋元聲樂藝術提供了重要的歷史資料。《唱論》扼要地論述了唱曲要領,從對聲音、唱字的要求到藝術表現,以及十七宮調的基本情調,樂曲的地方特色,審美要求等均有涉及,并有不少精辟之見。在聲音方面,他要求“聲要圓熟,腔要徹滿”,避免散、焦、乾、冽等毛病。演唱必須注意雄壯而不可“村沙”,輕巧而不可“閑賤”。還要掌握抑揚頓挫,推題婉轉等技法,并忌“字樣訛、文理差”的弊病。由此可見,他認為唱歌時,腔體和聲音要飽滿,嘴上一定要著力,不能懶散,唱歌咬字時嘴上一定要用巧勁,不能盲目使力。
此外,元代周德清作了一部戲曲(北曲)曲韻專著——《中原音韻》。其中也在提到了演唱者在語言、聲韻、格律等方面存在許多問題,他提出:“欲作樂府,必正言語,欲正言語,必宗中原之音。”[1]周德清以北曲雜劇作品為對象,總結其發聲規律,收集了北曲中用作韻腳的五千多個常用詞語,將聲韻規范為十九個韻部,每個韻部之下又分為平聲、上聲、去聲。周氏在對北曲的深入研究中認識到,北曲在創作中存在著許多問題,例如不講究格律,他認為要使北曲更好地發展,就必須做出規范,尤其是語言的規范更為重要,由此也就產生了音韻學著作《中原音韻》。
那么,不僅僅是戲曲,在現代的聲樂演唱中也是一樣,特別是中國歌曲。演唱中國歌曲時,講究每一個字都要飽滿、字正腔圓,展現其特殊的韻律。我國的詩詞、曲等韻文體都各有其格律,比較講究語言的聲韻,有合轍押韻的特點。中國字在聲樂演唱過程中講究歸韻,這也是從中國傳統戲曲的演唱上借鑒而來的,戲曲演唱中有“十三道韻轍”之說,這與周德清的《中原音韻》有一脈相承之處。“十三道韻轍”分別是:中東轍、一七轍、言前轍、灰堆轍、由求轍、人辰轍、發花轍、搖條轍、懷來轍、梭波轍、乜斜轍、姑蘇轍、江陽轍。在練習演唱十三道轍時,任何一個轍口都要裝進腔體里,共鳴才能通暢,吐字的分寸、準確度直接與聲腔有密切聯系,唱歌時我們要求要做到字正、聲通、腔圓。
二、“字”與“腔”的關系
筆者首次對“字”與“腔”的關系這個話題產生興趣是在看到汪毓和所著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中,程硯秋大膽提出改變過去京劇創腔“以字就腔”的成法,敢于以“以腔就字”的新原則創立新腔。[2]“以字就腔”和“以腔就字”這幾個字深深吸引了筆者,在筆者的聲樂演唱學習過程中,遇到許多關于“字”和“腔”的困擾,在一路摸索中學到一些心得,希望與聲樂學習者參考交流。
書上所解釋的民族民間唱法,是源于中國農村的一種演唱風格。講究以情帶聲、以字帶聲、字正腔圓、聲情并茂,唱法風格性強。而美聲唱法是17世紀產生于意大利的一種演唱風格,更注重對歌唱者通過對發音位置、共鳴及氣息的掌握來形成良好的歌唱狀態。由此可見,程硯秋“以腔就字”的觀念是來自于西洋聲樂的經驗,對中國的京劇唱腔進行改進,同時也將美聲唱法的理念帶到中國,使中國的的傳統唱腔注入新的血液,推動了中國傳統聲樂的發展。
有關于“字”和“腔”的問題,一直是聲樂工作者多年探討的焦點,關于先立字還是先立腔,以及腔和字在演唱過程中的內在聯系的問題,一直在聲樂界頻頻討論。我國戲曲與民族唱法傳統的訓練方法一直是遵循“以字就腔”的原則,傳統觀念認為“字正”才能“腔圓”。例如中國著名聲樂家應尚能曾在他所作的《以字行腔》里提到:“以字行腔就是要從字出發來建立唱腔。字是代表語言的,也就是說,唱腔要與語言密切相結合。如果按照西洋的傳統公式,把唱說成是聲音加字,那么就強調了聲音,抹殺了字的重要作用。”毫無疑問,“字”在一首聲樂作品中承載著一大半的藝術價值,特別是中國的文字,博大精深,源遠流長。
然而,“字正”就一定“腔圓”嗎?近年來不斷有人對這個傳統觀念提出了質疑,并倡導結合西方“以腔就字”的原則對中國傳統民族唱法進行改造。中央音樂學院聲歌系資深聲樂教授黎信昌在2002年的“全國青年歌手大獎賽”上就曾點評發言中曾提道:“字正未必腔圓。”并且早在1997年第二期《中央音樂學院》肖黎聲發表的《以腔行字——美聲唱法之我見》中,就提出建立一個“美聲唱法的中國學派”,將自西方唱法引進中國后出現的“美聲唱法咬中國字難”的老問題進行進一步探究,由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美聲唱法中國學派的訓練,則由于美聲唱法的特定藝術規格及行腔方法所決定,必須使中國漢字咬字發音方法作相應改變,以至形成一定意義上的“腔領字行、字隨腔走”,所以應叫做“以腔行字”法。
上述種種還有許多音樂家都對聲樂演唱“字”與“腔”的問題進行研究,那么,到底是應該“以字就腔”還是“以腔就字”呢?筆者認為:“以腔就字”的觀念給中國傳統民族唱法帶來了飛速的發展,在根本上說是前進向上的,因此,我們必須重視它的科學性,從當前所活躍在舞臺上的民族唱法的聲音來就看,民族的“以字就腔”和美聲的“以腔就字”是可以結合的,對于不同的階段應有不同的方法,如歌者還未建立穩固的演唱方法和歌唱狀態,就不必過分強調每個字的個性, 要把重點放在建立美聲唱法聲音形象的規格上,不然就會破壞歌唱聲音以及歌唱旋律的通暢性以及連貫性。立字時,如不顧及立腔的方法,所立之字也就會偏離美聲唱法中國學派的軌道,立腔時,如不顧及咬字方法,就會影響甚至破壞歌唱樂器的制造,立不了腔。
三、結語
總之,腔與字之間具有相互影響、相互支撐的內在聯系,我們要在良好氣息支撐的基礎上充分控制自己的聲音,通過刻苦訓練和長期磨合,使之在“字”與“腔”之間找到一個良好的平衡點,對聲音運用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