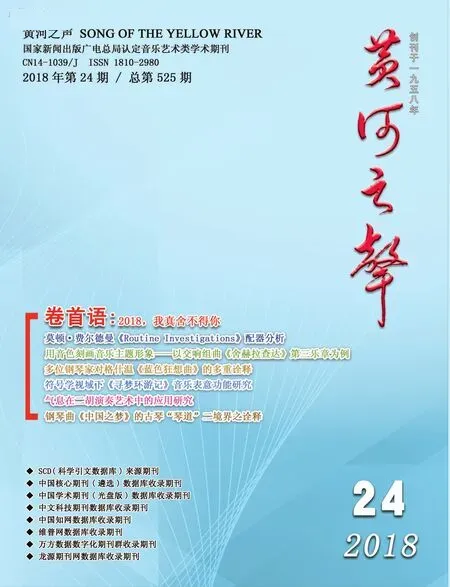古琴音樂的“留白”探析
李 瀟 瀟
(山西師范大學臨汾學院,山西 臨汾 041000)
一、古琴音樂中的“留白”
古琴樂音的形散會在其音響呈現中形成一種“留白”。
所謂古琴音樂之“形”,宗白華先生有這樣描述:“偃仰顧盼睎,陰陽起伏,如樹木之枝葉扶疏,而彼此相讓。如流水之淪漪雜見,而先后啟承。”意思是古琴的樂音形狀就猶如陽光下樹葉留下斑駁的陰影,又似水波泛起的微微漣漪,樂音虛實相濟勾勒出顯隱交織的線條流動。
古琴音樂之“形散”在于“單”。老子言“五音令人耳聾”,太多的樂音會破壞主體心靈與音響的共鳴,單音或少音的樂音音響更為純粹,干凈。例如古琴按音的演奏技法中,按音的演奏是一個獨立的實音,在其之后加入綽注技法而出現若干虛音的音響的延續,表達內心起伏的情感,這即是中國音樂“形散神聚”在器樂演奏中的實際表現。在琴曲《酒狂》中第一段與第二段相同旋律音演奏的對比,第一段三拍子節奏中,分別用散音、按音、帶起三個技法連接發出三個單音的音響,而第二段同樣的旋律音分別用散音、按音加綽上的技法連接發出的是兩個單音和一個虛音的音響,第二段的因為綽上技法的加入而使音樂線條有了連綿的起伏,聽覺上產生微微上滑的效果,則明顯多了綿長的韻味在里面。
二、“留白”中傳遞樂境
古琴音樂的音響“留白”傳遞出一種“空”的音樂妙境。
在琴曲演奏中,“留白”的部分大都會用吟、揉、推、拉等技法作以潤飾,手指力道的微小差異都會產生不一樣的“空”的聽覺體驗。例如《陽關三疊》演奏中,四段中每一段結尾處都有相同的旋律重復,每一小節的長音仿佛都是曲中詩人面對與友人分離時長長的嘆息,長音的空白若是用“撞”的技法則產生一波三折的短促的音響,是一種不舍之情較為強烈的表達;若是用“吟”的技法則更加細膩;若是用“揉”的技法則可以體現出詩人欲揚還抑的內心情感;曲終則沒有任何技法潤飾,曲終長音的空白與前三段空白之處相比則多了更為悠遠綿延的表達。因此所謂“空”并不是沒有變化,而是變化無窮的內涵。
三、“留白”中浸透心境
“對于情,非中國所特有,但中國文人音樂,乃至整個中國音樂都主張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中國文人的表情性質基本上不是情感論、更不是激情論,而是心境論。”古琴音樂中的“留白”,突出反映了文人中正平和、不偏不倚、進時即退、顯時即隱、揚時即抑的柔韌迂回的審美心境。
中國傳統音樂崇尚含蓄的藝術傳達,具體到某一具體音樂形式中非古琴音樂莫屬。古琴音樂中的“留白”,在虛實相濟的運指中傳達似有若無的音樂線條,需要演奏者及欣賞者雙方主體心靈的沉靜安寧,這種含蓄內斂的音響特征我們可以視為一種弦外之音的樂境描述,更深層次反映的是中國文人心境論。“含蓄”字面可解釋為包容、蘊藏于內而不顯于外。也指言語、詩文等意未盡露,耐人尋味。在孫犁的《秀露集·進修二題》中對“含蓄”的解釋是:“所謂含蓄,就是不要一瀉無遺,不要節外生枝,不要累贅瑣碎,要有剪裁,要給讀者留有思考的余地。”
古琴音樂的“留白”中浸透著文人靜觀自省的主體心境。文人音樂的整體音樂風格偏向一種清幽恬靜,這種“靜”是對文人在日常生活中不愿節外生枝的行事作為,也是保持自我獨立人格的必需要求,透過樂音涵養心靈。在“靜”的心靈要求中,文人要做到的是主體內心的平和適中,收斂克制。因為只有在“靜”的身心狀態下才能實現對自我內心的清晰認識,并時刻修正自己擺脫外界的瑣碎干擾。文人將最濃烈的情感放在古琴高音域表現,是文人對情感表達有意的剪裁布置,文人通過音樂審視自己,但不愿將內心完全展現于他人,樂曲中含蓄的情感表達很大程度上突顯空白,這“空白”恰恰是文人留給自己的內心思考,更是遇“知音”的距離。文人音樂所具有的含蓄的美學特征,是文人直指內心的要求。
古琴音樂的“留白”中浸透著文人對待客觀事物的淡然處之的心境。所謂“淡然”不是單一乏味,而是刪去外物的束縛,其中可能會有些許對客觀現實的逃避,但對于自我來說,文人希望通過淡化外事外物來換得一份和平淡靜的心性。這種淡然,影響著文人在創作音樂的過程中會選擇清凈的客觀環境,也影響著文人音樂偏向“散慢”的律動,呈現散拍子的特點,“散”一般都與“慢”的速度相配合,帶來的是一種寧靜的氛圍,人在一種趨向于靜的環境中,由外部的肢體動作過渡到內心的心理活動都會漸漸趨向平靜,以更加突出內心清靜的心境。
古琴音樂的“留白”中浸透著深遠的弦外之音。如果說指上音是文人心境有形有聲的表達,那么弦外之音就是文人心境無形無聲的渲染,具有隱含而深遠的意味,即文人音樂最終的指向——心境。
四、結語
綜上所述,“留白”的藝術創作手法不僅僅存在與中國繪畫藝術領域中,在中國音樂中亦有“此處無聲勝有聲”的留白呈現,中國音樂的空白的空間處可能就是文人在尋覓知音的心靈距離,可能就是此藝知音自古難的歷史距離,可能就是中國音樂一直追尋的“弦外之音”、“大音希聲”的心境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