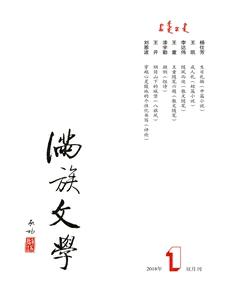關東古榆圖
楊子忱
少小,在我老家屯頭道北,有一株古榆,長得繁繁茂茂,郁郁蒼蒼。對于這株古榆,我留有兩個印象:頭一個是,每年到了春夏之交,也就是農歷四月初八、十八、二十八,這三個廟會日期間,總有一些老媽媽、老奶奶,領著兒孫,來到樹前,燒香上供,叩頭許愿,認古榆為干媽媽或干姥姥。我曾問過,她們說,古榆壽長,認它做干親,好養活,能長命百歲。另一個是,有一次,我在古榆下,看鄉親備犁,其中一位叔伯問我:“你是讀書人,懂的多,可曉得犁上哪顆塞子叫做‘千斤塞?”我真有點門外漢了,頻頻搖頭。他告訴我,這個塞子,就是犁上管犁地深淺的那個木片。又說:“立木能頂千斤塞, 別看它小,作用可不小。”還說,由于榆木結實,堅挺,又多彎,所以做犁轅,砍“千斤塞”,往往少不了它。
后來,我離開家鄉,到外地去了,時間一久,對于這兩個印象,也就忘卻了。對于那株古榆的印象,也有些淡化了。然而,我在外場卻見到了更多的古榆。這里,有雙陽長山村古榆、雙陽靈巖閣古榆、雙遼雙山街古榆、九臺莽卡村古榆、舒蘭亮甲山和轎頂山古榆、德惠西河堡古榆、舒蘭八棵樹和神樹底下古榆、蛟河牛心頂子古榆、樺甸陳木匠溝古榆、鎮賚黃榆坨子古榆、安圖明月溝古榆、敦化黃泥嶺古榆、汪清百草溝古榆、輝南榆樹岔古榆、洮南東興鄉古樹村古榆。民國年間,在草地白城洮南府,曾當過洮遼鎮守使的“草頭王”吳俊升“吳大舌頭”住過的府邸附近,也有一株高大的古榆。當然,這都是關東地界的。我還曾細細想過,以古榆的“榆”字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像吉林境內的,就有榆樹溝、榆樹臺、榆樹川、榆樹灣、大榆樹、雙榆屯、孤榆樹、榆樹排子、榆樹崗子、榆樹崴子、榆樹頂子。我故里九臺上河灣鎮,紅朵溝西,黃花甸北,椽子背南,就有大榆樹林、小榆樹林、榆樹趟子。吉林永吉南,過了五里橋子,就是榆木橋子。我去過通榆,通榆系由開通和瞻榆兩縣合治而成,其中舊瞻榆,有一株古榆,在鎮西南隅九公里處,接管營子屯沙崗上。舊志載:“歲歲開花,年年見莢,枝繁葉盛,樹大蔭深,播能望耠,種可試犁。”算來,已有四百余度寒暑了。晚清時期,長春城內有座“榆園”,植榆數百,參天蔽日,落影搖曳,春來榆錢覆地,配以人工水荇,蔚為壯觀。那時園亭上,曾有一聯,云:“滿池水荇能藏月,遍地榆錢可買春。”甚是熨帖。因其年頭古老,被尊為長春第一楹聯。昔時,名噪一時的長春孝子墳,也有一株古榆,其墓即倚樹而建。然而,最為隆盛的,當數榆樹市之古榆了。榆樹市,昔年為縣,舊稱大孤榆樹屯,蓋因城南王家屯,有一孤榆,大且巍,粗且豐,故而名之。至于后來,易為“榆樹”,那是名號刪繁就簡而致,更具代表性了。“參天攬霞,獨立蒼穹,形同華蓋,蘊力無瀚”,且“環榆作障,既可防風,又能阻匪,以為護城”,這是《榆樹縣志》老志所載。縣志還載,至民國初年,城周邊壕,尚有巨榆3203株。清同治十一年,即公元1872年,由榆樹鄉紳于岱霖等帶頭,捐資倡建,創立“種榆書院”,其門首有一聯,云:“入室自升堂,一代階梯基小學;樹人同植木,百年梁棟蔚孤榆。”“孤榆”,即指當年榆樹舊稱“大孤榆樹”而言。此聯貼切得體,道出育人同植樹的哲理關系。
也是由此所致吧,晚清時期,榆樹“種榆書院”,在八十年間竟培育出兩名翰林、四名京官、八名進士、十六名舉人、三十二名貢生。其中,僅榆樹黑林子鎮太平川村于氏一家,就出現“叔侄五進士,兄弟兩翰林”的盛況。雖屬舊時科舉,但也充分反映出當年于氏之家治學之盛,碩果之隆。據載,太平川于氏老宅南園子,當年就曾植榆百株。于家厚榆,榆也給予了于家以好兆頭。這個兆頭,又綿延到“種榆書院”,以及更廣更博。現在,聯想開來,不能不說,這種盛況,與榆樹的品格、風采、蔭護,息息相關,脈脈相通。現今,在榆樹福安鄉夏寶村東南,尚有一株古榆,高十數丈,冠八坪余,罩地數畝,兩百余年樹齡。據說,該榆之根系,即源自于“種榆書院”古榆,以為延續學風,接續文氣,綿續文脈。當然,這里所講雖多是學識上的事,但也不乏市場經濟意義。榆樹以榆樹錢命名的“榆樹錢酒”以及以昔年天德盛燒鍋命名的“天德盛高粱酒”,皆已譽享千里,名貫四方。1999年10月31日,我來到永吉烏拉街鎮,觀瞻了那個位于舊街村西的古城遺址,那里尚有古榆數百,其中兩株,通體斑駁,樹老梢焦,軀干形成空洞,似有火燒痕跡,但還鐵干弘枝,鋼杈虬勁,直向青天。人說,它是明末清初遺存,已有四百三十多年歷史。清初多爾袞的母親,即烏拉街人。據說她曾見過這株古榆。這株古榆,曾被譽為“公主榆”、“貝勒榆”,又稱“圣榆”。當年古榆旁,即烏拉國的都城大烏拉虞,也就是舊街村,還叫老城里,原烏拉國皇宮舊址。可惜的是,公元1613年農歷正月十七日,被后金首領努爾哈赤帶兵焚毀。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后一個王朝建立于多榆的遼寧新賓縣赫圖阿拉山城。清皇室愛新覺羅氏之祖陵永陵,亦曾有一株古榆,傳說為天河岸邊榆籽飄下,落地生根,遂成巨樹。為此,乾隆帝弘歷,還以《神榆賦》為題,志詩一首,勒石刻碑以頌之。又傳說,“老罕王”挖參,曾背父親骸骨,來過這里,為了孝敬,置骸骨于樹丫。結果,老木空心,滑落樹洞,待再看時,見洞無底,海水翻花,溝通地河。遂以為天意,便拓地立墓,奠定祖陵,山也因之而名,賜號啟運。這雖屬神話傳說,但也透出榆樹育人的源遠流長的歲月內涵。迄今,在遼寧撫順城至新賓赫圖阿拉山城的古道上,尚有樹齡在四百年以上的古榆十六株,樣子猶如十六位大將軍列隊守護。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先封有四帝,入關之前續有二帝,入主北京之后又傳十帝,前后計十六帝。相傳,這十六帝與十六榆,正好匹配,亦算巧合,遺為趣談了。
其實這里所言,只是古榆隆赫之一面。我真正認識古榆,則還是起于纖微小事。在我老家九臺三臺東,松花江對岸,舒蘭境四間房鎮南,有個地名,叫“秫秸橋子”;榆樹十四戶鄉東,有個地名,叫“土橋子”。實際上,這兩座橋,既不是秫秸的,也不是黃土的,如果硬說成那物,也只能是指其表面,而真正支撐起橋的,恰恰是榆木。是榆木撐起這橋的骨架,挺起這橋的脊梁。古寬城子,也就是寬街、寬城,即今長春,當年它的西門聚寶門外,有座雙橋子,兩橋皆為榆木搭建。“雙橋子,不大擠,一年一臺子弟戲。沒有戲臺子,借著土崖子。沒有點燈油,就著月亮地。沒有橋面板,鋸株老粗榆。打個飛旋腳,弄個狗啃泥。唱出打金枝,缺少郭子儀。來出群英會,周瑜沒生氣”,這是百年古謠了,說的即是這里。由此,我再回想到少小,回想到老家的那株古榆。那株古榆,每年春天,都要結出嫩白圓碧的莢,稱之為“榆樹錢”。榆樹錢,簡稱“榆錢”,形同銅錢,也似硬幣。其味辛辛,其汁淡淡,有點微甜。當年,我們這些鄉村的野小子,總是爬樹采摘,伸手擼取。它不僅好吃,還能解餓解渴。其實,榆樹內皮那層嫩肉,還含有一種粘粘的汁液,用水浸泡內皮,把汁液引出,加在粗米糙面里,壓成饸饹、做成面條、搓成馇子、或包成大菜包子,能多打餡。在那災荒連連、缺糧少米的年月,吃它很是抗餓,能填飽肚子。也正因為這樣,它曾成為了那個年代那些闖關東人倚榆結廬、就地拓荒、謀取出路、尋求生機的一種金貴的救命草。說到闖關東,我又記起一事。近年,聽聞山東聊城的清代名宦劉墉,即那位被稱為“宰相劉羅鍋”的,后人日子過窮了,移居到長春城西,也就是孟家屯附近的廣寧王屯。那里原名為“大孤榆樹屯”。為何有這名?據說,劉氏先祖,在離開老家時,曾折井臺古榆一枝作杖,來到這里后,插地生根,向天成株。年深月老,日久天長,鄉親投奔,民戶驟聚,遂立屯興村。上述這些,蓋起于古榆。由此,我又情不自禁地聯想到,榆樹市秀水鎮大于村周家油坊屯,那顆村民打井時挖出的至今已有六萬余年的“榆樹人”古人類頭骨化石。關東古榆,多像關東漢子,于是,我的一首贊譽關東古榆的詩,油然而生,颯然而至,詩曰:“關東蒼莽蘊雄風,無際古榆皆盛情。樹大根深基底厚,枝繁葉茂影蔭隆。千秋脈脈堪奇偉,萬載悠悠亦普遍。俎豆瓜瓞桑梓地,天華韌衍共榮生。”
確實,關東古榆,樹大枝繁,根深蒂固,源遠流長,真個歲月滄桑,時光荏苒,履跡倥傯。無疑,堪稱一幅生生不息、代代相續、口口相傳、立體直觀的《關東古榆圖》,因以命之。
〔特約責任編輯 王雪茜〕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