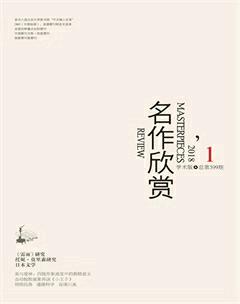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中的《雷雨》和曹禺
徐安琪
摘 要:本文從《雷雨》和曹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書寫中的變遷,看到文學背后的權力話語的變遷。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是需要理性地對待的,我們不能要求文學史的書寫超出時代語境,而文學史不斷地更替正代表著一種對話本質。
關鍵詞:中國現代文學史 《雷雨》 曹禺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各個版本中,對曹禺的評論角度也是異常豐富的,正如《雷雨》,它在文學史上的命運就是起起伏伏的,文學史編撰者從不同的文學史觀角度評價該作品,同時,不同版本的文學史對曹禺本人也有一定的解讀。而“說不盡”的曹禺,是文學史上的一個特殊現象。中國現代文學史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在其編寫的過程中也體現了文學史觀和時代語境互相交錯的關系。
一、1949年以前有關曹禺和《雷雨》的評論
早在曹禺出現在文壇之際,《雷雨》打響國內話劇演出熱潮的第一槍時,曹禺便置身于文人批評家的評論之中,甚至被魯迅列入左翼戲劇家的行列。眾所周知,曹禺因為《雷雨》而備受關注,下面筆者將從《雷雨》的命運看曹禺的地位變化。
中共在抗戰時期,積極地將優秀劇目推向時代潮流之中,同時也動員知識分子以筆代槍。據曹禺自己回憶:“從抗戰開始,我同共產黨人接觸得越來越多。1938年,在重慶見到周恩來總理,談得就更深了,周總理是十分直率的,他給我多年的教育和幫助,是我終生難忘的。”①而國民黨政府當局,則是一再阻撓曹禺戲劇的演出。1938年,國民黨當局認為《雷雨》有煽動工人罷工的嫌疑,因此下令禁止其上演。1941年皖南事變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認為悲劇《雷雨》不適合抗戰時期,因此發出正式文件禁止《雷雨》再版,同時,也取消了《雷雨》的演出。顯然,《雷雨》在國民黨當局的眼中是一個反面教材,也就是說,雖然《雷雨》還會上演,但是由于當局政府的明確表態,《雷雨》在話劇界的地位被邊緣化了。
所以,1949年以前,曹禺就被列為左翼戲劇家之一,而后的文學史中也有曹禺的出現。
二、1949年以后文學史中的曹禺和《雷雨》
1949年后,新文學史的編纂大多是有組織、有領導地進行的,因而具有了“正史”的特征。其中,最早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就是1951年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由王瑤編著的《中國新文學史稿》。這部《史稿》普遍被認為是文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曹禺在1949年以后成為進步的知識分子,受到中共的青睞,參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動。同時,他對自己的作品也進行了很大程度的刪改,不過他對中共倡導的革命力量不甚了解,所以修改后的作品被批評。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無論修改反響如何,曹禺的修改是服從于政治的,因此他主動糾正了作品中無產階級缺失的問題。所以,葛一虹認為:“對于五四以來的我國現代話劇文學作品……經歷了一個反復認識的過程……曹禺修改舊作的失敗,是當時時代環境的影響。”②但是,如果曹禺不重寫《雷雨》,那么劇作就很難吸引人民群眾了。《中國新文學史稿》對曹禺的《雷雨》也有評價,其首先認為《雷雨》是“新文學運動以來戲劇創作上稀有的成就”,但否定了《雷雨》的神秘主義,也就是命運觀,接著肯定了《雷雨》的社會現實意義,將其拔高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力作。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中指出了周樸園、繁漪、周萍、侍萍等人物形象的特點,分別用專橫、苦痛、軟弱、悲慘來形容他們,可以看出作者主要從《雷雨》的現實主義分析。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中也對《雷雨》有所評價。其中,劉綬松認為,《雷雨》更能表達“社會劇”的觀點,他從階級性的角度進行分析。《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稱:“我們不僅在劇本中看見了一個大家庭的隱秘的罪惡,而且我們分明地看見了在劇本中表現出來的復雜尖銳的階級的關系。”這種看法在當時是典型的二元對立的階級對立法。在1949年以后,審視劇本的視角都是采用這種階級對立法。劉綬松采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法評論作品的傾向特別明顯,比如他就指出《雷雨》中的“宿命論”色彩,認為這是作品的缺陷,這與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解讀不謀而合。《中國新文學史初稿》認為這種宿命論色彩和神秘主義會“限制作品對于現實挖掘和反映的深度”。第一次“文代會”后,1951年開明書店出版了《曹禺選集》,此時中共明確了文藝必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所以曹禺開始主動強化人物間的階級矛盾,消解了最初營造出來的“欣賞的距離”,為的是“讓劇作中帶有向敵人作生死斗爭的正面力量”。在開明版中,曹禺不僅刪掉了《雷雨》的序幕和尾聲,而且對劇中的人物、結構也進行了大幅度改寫,他希望“對今天的觀眾還能產生一些有益的效用”。改寫后,結尾處周萍沒有自殺,四鳳沒有尋短見,周沖也沒有電死,《雷雨》不再是一部悲劇了。中共接受的是馬克思主義,因此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進而要求人民群眾都要有好結果,于是悲劇就不符合時代要求了。自此之后,各種版本的《雷雨》也都從階級斗爭的角度重新塑造,并且曹禺本人也多次否定了《雷雨》在20世紀30年代的命運主題,而肯定《雷雨》作為階級斗爭以及反封建的意義。無論是文學史的評價還是曹禺本人的傾向,都是努力符合時代話語的要求。
三、新時期文學史中的曹禺和《雷雨》
20世紀80年代以來,激烈的階級斗爭已經不復存在,人們的文學觀念也在不斷演進。20世紀80年代也是一個學科自覺的時期,文學史敘述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即許多文學史教材需要調整步伐,重寫文學史適應改革開放的需求。唐在1978年開始重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其中對于《雷雨》的評價也更換了側重點。唐版認為《雷雨》的深刻思想意義在“暴露了資產階級的罪惡”,“而且引導觀眾和讀者不得不追溯形成這種悲劇的社會原因”。從人物形象分析也可以看出唐試圖恢復“五四社會問題劇”的解讀,將繁漪解讀成追求自由、解放、愛情的資產階級女性,將侍萍解讀成被家庭壓迫的女性。關于《雷雨》的“神秘主義”,唐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沒有回避該問題,而是進行了直接的批判,指出作者“主觀上對產生這些悲劇的社會歷史根源當時還缺乏科學的認識,把悲劇的原因解釋為‘自然的法則……這種思想認識影響了作品反映現實的深廣程度,并且帶來一些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弱點”。從文學史編撰角度看來,他遵循了改革開放后實事求是的要求,并且把主要視角投放在“反封建”的意義上,試圖淡化階級對立色彩,但是依然也遵循著現實主義的角度,沒有恢復《雷雨》的命運觀。現當代文學研究進入一個對既往文學史編纂系統反思的時期,即“重寫文學史”時期,出現了一大批學理性與創新性都很強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錢理群等人撰寫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這本著作對于曹禺《雷雨》的研究則側重于藝術技巧、戲劇語言等角度進行分析,雖然對于主題方面依然是從“社會問題劇”角度強調“反封建”意義,但是這種賞析已經是對當時的語境的突破了。朱棟霖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雷雨》的主題分析基本恢復了曹禺的原意,即看到了作品中“人性”的一面,更肯定了序幕和尾聲的作用,淡化了政治解讀,認為“人物的血緣糾葛與命運巧合更真實、更典型地反映了人性的復雜性與人生的殘酷性,悲劇的結局引人思索,在思索中探究釀成悲劇的根源”,并且在藝術風格等方面進行分析,也側重了作品的美學價值,符合“回到文學本身”的20世紀80年代話語。
四、結語
從曹禺和《雷雨》在文學史中的敘述變遷來看,其背后體現了一種思潮和政治關系的變化,每個階段的文學史都是時代話語的體現。筆者認為,文學史作為一門學科,其背后是權力的體現,但是我們需要客觀地看待權力一詞。針對文學史學科來說,文學史的編纂應該要沿著時代的前進而變化,但是對于研究者來說,我們也不能苛求他們能超越時代話語。其實對待文學史也像對待文本一樣,“文本是由作者與主人公兩位價值不同、地位平等的主體之間的交流與對話構成的”,像復調小說就很好地說明了一種對話關系,所以作者的聲音只是眾多聲音中的一個。文本閱讀過程中,有敘述者、批評家、讀者等各種聲音,因此也會產生不同于第一文本的其他文本,從而走向文本之外的新語境,這是對話雙方互動的結果。因而我們要明確,文學史的編纂也是多方面聲音的融合,客觀對待文學史也就是客觀對待時代語境。
① 曹禺:《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見《曹禺劇作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頁,第373頁。
② 葛一虹:《中國話劇通史》,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版,第362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