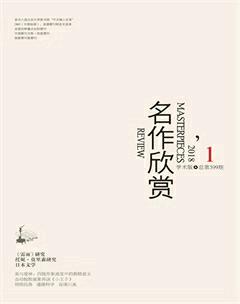中西“神圣瘋子”的“惡”
陳小玲
摘 要:中西方宗教信仰不同,但卻有相似的“神圣瘋子”。在馬塞爾·埃梅作品《呆兒木什》與丁國(guó)祥作品《癲子良云》中,二人共同書寫的“神圣瘋子”異于一般的宗教信仰者,如界限模糊的善惡觀,倫理與宗教上善惡的對(duì)峙。然而“神圣瘋子”不惡不瘋。通過(guò)“神圣瘋子”的“惡”,可反思人是如何從單純追求生、欲、利的自然人,升華為真善美的文化人。
關(guān)鍵詞:神圣瘋子 惡 馬塞爾 埃梅 丁國(guó)祥
我們常把人對(duì)命運(yùn)的抗拒、個(gè)人與社會(huì)的沖突、智者與庸眾的斗爭(zhēng)、理性與張狂的分離等人稱作“瘋子”。西方在圣與俗的對(duì)立中產(chǎn)生了“神圣瘋子”。而在中國(guó)的傳統(tǒng)下,我們也有著佛學(xué)影響的“神圣瘋子”,這是不同宗教文化下相同的文學(xué)樣態(tài)。
《呆兒木什》是法國(guó)作家馬塞爾·埃梅的一篇短篇小說(shuō),刻畫了一個(gè)擁有強(qiáng)壯體魄的瘋子呆兒木什。埃梅筆下的呆兒木什犯了死罪。但懺悔師卻通過(guò)談話發(fā)現(xiàn),他的心靈如泉水一般純凈清澈,沒(méi)有邪念,木訥的表情和言語(yǔ)似乎沒(méi)有靈魂。他殺人的動(dòng)機(jī)只是為了音樂(lè)。上帝將三位老人復(fù)活,一切都清零,但他還是沒(méi)有逃過(guò)“法律”。
《癲子良云》塑造了一個(gè)執(zhí)迷佛教的瘋子良云。因?yàn)榛忌狭司窦膊。詮囊粋€(gè)資優(yōu)生變成一個(gè)輟學(xué)生。他的精神病況傳聞席卷了他的生活全部,而他的精神也越來(lái)越不正常。最后,他被關(guān)在遠(yuǎn)離村子的谷場(chǎng)。幾年后,一個(gè)故友的探訪卻讓良云的瘋蒙上了一個(gè)問(wèn)號(hào)。二人共同書寫的“神圣瘋子”不同于一般的宗教信仰者,如界限模糊的善惡觀,倫理與宗教上善惡的對(duì)峙。反思“神圣瘋子”的同時(shí),我們可以看到人是如何一步步成為人。
一、“神圣瘋子”合理的惡
善惡是宗教永恒的話題。各門宗教中,傳統(tǒng)的解釋通常將惡看作是百害無(wú)一利。宗教中常有“惡”沖破阻礙成佛得道。如《呆兒木什》中呆兒木什希望能夠每天都聽(tīng)到音樂(lè)。而靠年金生活的三個(gè)吝嗇老人卻常常讓他不能如愿,于是他殺死了這三個(gè)老人。世上的人認(rèn)為他犯了殺人罪,呆兒木什最后也不覺(jué)得自己有錯(cuò),也不在乎死刑。《癲子良云》中良云希望保護(hù)他的豬朋友,把好心給他加幾片豬肉的父親的眼珠子挖了下來(lái)。這些都是“惡”。
宗教中的惡是可以被原諒的,“惡只是善的一種低級(jí)形式”。《圣經(jīng)》言:“神看著一切創(chuàng)造的都甚好。”內(nèi)含“從惡出發(fā),也可以回歸上帝”之意。佛教也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惡”可被原諒,被拯救。《呆兒木什》刻畫了許多耶穌的故事,訴說(shuō)的教條是上帝可以原諒每一個(gè)有罪的人,只要他的心思純正。而《癲子良云》展現(xiàn)了小乘佛教的思想,人生本苦,贖罪而活。大凡宗教,都是讓人棄惡從善的。在這里,兩篇文章中的惡并不是值得贊嘆的品質(zhì),而是作為一種契機(jī),引人去從善,引人皈依,得道。
閱讀過(guò)程中,不難發(fā)現(xiàn)作者悲憫情懷很深。行文間常懷同情的筆法去刻畫兩個(gè)瘋子,刻意描繪“神圣瘋子”的合理性。首先,兩位作者都借助了一個(gè)俗世認(rèn)可度高的角色去與瘋子直接對(duì)話。《呆兒木什》中,作者借助了懺悔師這個(gè)人發(fā)出感慨:“這是個(gè)搬運(yùn)工的身體,兒童的靈魂,他殺了三個(gè)瘦小的老人,并沒(méi)有什么邪念,如同一個(gè)孩子打開(kāi)布娃娃的肚子,又或者扯下布娃娃的胳膊腿……”《癲子良云》中借助章若吉的耳朵,聽(tīng)到了良云訴說(shuō)他的苦難與得道;還借助章若吉的眼睛,描繪出村子內(nèi)部自身存在著問(wèn)題:“月光還沒(méi)有暗下去,章若吉清楚地看得清父親的臉色和眼神。也看到了父親回頭向村西牛欄望去的動(dòng)作。”這些人物作為文學(xué)上的一種中介,浸潤(rùn)了作者的情緒再現(xiàn)在文章中,文章同時(shí)具有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的敘述,使得文章合情合理。“瘋子”之惡在于癡,而“癡人”有其可恨之處,卻亦有其可憐之處。
再者,文章中刻意引用了許多宗教中的禪語(yǔ)照應(yīng)原典。《呆兒木什》中情節(jié)中不斷反復(fù)的“小耶穌”和呆爾木什變回小嬰兒的神顯;《癲子良云》中良云充滿智慧的言語(yǔ)以及襲母事件中,呼喊的“我不想做人”。這些故事上有意無(wú)意地與《圣經(jīng)》的小耶穌代替世人受罪重新降生的故事、小乘佛教“諸行無(wú)常、諸法無(wú)我、諸漏皆苦、涅寂靜”的“四法印”相照應(yīng)。
最后,文章中的時(shí)間描寫隔絕了宗教的“現(xiàn)代化意識(shí)”,使得他們的瘋癲是可以被原諒的。《呆兒木什》寫在二戰(zhàn)前,作品中有著濃濃的20世紀(jì)20年代法國(guó)的鄉(xiāng)村氣息。《癲子良云》中,能夠看到中國(guó)現(xiàn)代農(nóng)村的影子,書寫的時(shí)間狀態(tài)是中國(guó)20世紀(jì)60-80年代的事情。兩個(gè)“神圣瘋子”的生活年代存在“宗教邊緣化”的傾向。
總而言之,兩位作家安排了一條向善的解脫之路給兩名“神圣瘋子”,并且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極力描述了他們的心路歷程,顯得合理妥當(dāng)。
二、倫理與宗教上的善惡對(duì)峙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宗教的“惡”與科學(xué)的“惡”是不一樣的。從倫理方面看,兩人是犯了故意傷害罪,但是在宗教上,良云只是犯了人生三苦“貪嗔癡”中的“癡”。這種錯(cuò)誤,人人都會(huì)犯。
初看《呆兒木什》和《癲子良云》的前半部分,會(huì)發(fā)現(xiàn)作者刻意懷著悲憫之情,制造了兩個(gè)“宗教狂熱者”。呆兒木什殺了三個(gè)弱小的老人,絲毫沒(méi)有反悔之意,良云枉費(fèi)了父親對(duì)自己的關(guān)心,挖掉了父親的眼珠子,令人害怕。馬克思曾說(shuō)宗教是一種顛倒的世界觀,是“還沒(méi)有獲得自身的自我意識(shí)和自我感覺(jué)”。恩格斯、尼采等哲學(xué)家的宗教批判都消解了對(duì)上帝的盲目崇拜與神圣權(quán)威。這些先知的哲學(xué)家們都看出了,不將上帝的虛構(gòu)合理消解,人性之光無(wú)法照耀。
假設(shè)缺少了宗教的光環(huán),呆兒木什和良云之間閃耀的向教之心,在這些哲學(xué)家的眼中便顯得黯淡無(wú)光。但他們的人性之美便又重新煥發(fā)出光彩。
當(dāng)他們面對(duì)心愛(ài)之物時(shí):呆兒木什唯一的應(yīng)聲就是哼唱促使他犯罪的那支樂(lè)曲。良云被倒吊在屋柱上時(shí),眼球突出,目光兇殘,鼻子的呼吸聲震天響,嘴里卻念起佛號(hào):“阿彌陀佛,菩薩救我。”而后良云在回憶他的痛苦——平靜——痛苦的時(shí)候,臉上顯現(xiàn)超脫年齡的成熟,使得這個(gè)人充滿了人性與哲理的光輝。
這些人性之美在消解了刻意的宗教環(huán)境后,顯得這兩個(gè)“神圣瘋子”的固執(zhí)格外迷人。作者描寫瘋子的人性之美,目的是贊揚(yáng)這些心靈純粹之人。endprint
文章的后半部分便逐漸顯現(xiàn)出了“瘋子”以外的世界,倫理要求兄友弟恭、案子要公正評(píng)斷。相比之下,那些旁觀者的行為又是如此的荒誕。《呆兒木什》中的判決官因?yàn)楹ε鲁袚?dān)責(zé)任,將此事一層一層地向上級(jí)請(qǐng)示;《癲子良云》的父親兄弟得知良云精神有問(wèn)題后,就沒(méi)有將其當(dāng)作人看待,倒吊在屋頂十幾天,晚上兄弟們輪流來(lái)揍他。這些瘋子以外的人,除了作者刻意挑選的第三者,其余都是空有倫理道義形式,全無(wú)行為章法的人。看上去,這些旁觀者的世界展現(xiàn)出來(lái)的“正常”更加瘋狂。
文章中倫理與宗教的矛盾就像是互為擋箭牌。倫理和宗教兩者本質(zhì)之間確實(shí)存在矛盾,但文章中更多的是心口不一之人制造出的矛盾。旁觀者處死呆兒木什的行徑是善是惡?檢察官、監(jiān)獄長(zhǎng)等等的人物都有著各式各樣的齷齪想法,故此,他們給出了這樣的指令:“殺人兇手蜷縮了一點(diǎn)兒,這種事絕不能用來(lái)妨礙司法條文的執(zhí)行。”檢察官們真的重視法律嗎?并不,他們每個(gè)人都在言升遷之事。在處決呆兒木什一事影響到自己時(shí)候,用接收到的“法律指令”說(shuō)話。這些人竟不如一個(gè)瘋子來(lái)得純粹與實(shí)際。旁觀者依賴倫理,生活在倫理中多年,然而倫理卻不是他們所信仰的,于己有用時(shí),自己滿口倫理仁義,于己有害之時(shí),滿口利益當(dāng)先。這難道不是一種“惡”?
倫理與宗教上的善惡對(duì)峙并不是簡(jiǎn)單的二元對(duì)立,但是在世間擁有純粹的心靈,并且忠于自己的內(nèi)心之人,實(shí)在難得。呆兒木什和良云便是這樣的人,忠于宗教信仰時(shí),便放下屠刀,超脫了金錢、工作、生死,只求達(dá)到癡迷之物。最后得到救贖時(shí),整個(gè)人脫胎換骨,涅重生。這不得不歸因于“神圣瘋子”比常人更純粹的心靈,更勇敢的追求。
任何作品都是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記錄。它們記錄了個(gè)人對(duì)自然、社會(huì)、思維三大科學(xué)領(lǐng)域的反映形態(tài)與認(rèn)識(shí)過(guò)程。馬塞爾·埃梅的《呆兒木什》與丁國(guó)祥的《癲子良云》反映了“神圣瘋子”這一共同的母題,便是從“神圣瘋子”界限模糊的善惡觀入手,然而,我們分析倫理與宗教上的善惡的對(duì)峙后,便知“神圣瘋子”并不惡也不瘋。人從單純追求生、欲、利的自然人升華為真善美的文化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
參考文獻(xiàn):
[1] 馬塞爾·埃梅.呆兒木什[J].南方文學(xué),2017(1):39-41.
[2] 丁國(guó)祥.癲子良云[J].南方文學(xué),2017(1):34-38.
[3] 曾祥芹,韓雪屏.閱讀學(xué)原理[M].開(kāi)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
[4] 金麗.神圣瘋子——從《圣經(jīng)》視野解讀西方文學(xué)系列論文之七[J].廣西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3(1):132-136.
[5] 陳堅(jiān).貝施特和智論“惡”的宗教價(jià)值——兼談宗教中的“善惡”觀念[J].宗教學(xué)研究,2005(3):97-103.
[6] 丁麟茜.西方宗教批判的意義及其限度[J].云南社會(huì)科學(xué),2017(1):62-68.
[7] 居納爾·希爾貝克,王寅麗.宗教批判與意識(shí)現(xiàn)代化[J]. 哲學(xué)分析,2010(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