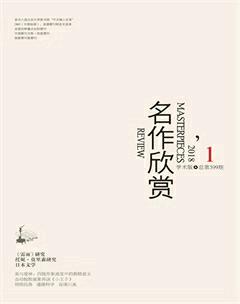“荒誕藝術”的審美意趣略論
金亞萍+侯小鋒
摘 要:荒誕藝術的誕生打破了西方傳統思想的束縛,對此前的古典主義、文藝復興、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藝術做出了最徹底的反叛。“叛逆”成為最具代表性的藝術精神,藝術變得難以定義,審美變得了無深度。然而,看似荒誕不經的“藝術”,卻支撐起了“泛藝術化”的大時代。
關鍵詞:荒誕藝術 叛逆 標示性 意義缺失
荒誕派戲劇是荒誕藝術最突出的代表,荒誕派戲劇起源于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法國,有著深厚的“存在主義哲學”思想基礎;《等待戈多》《禿頭歌女》《椅子》等荒誕戲劇作品為人們所熟知,然而,“荒誕”并非源于戲劇,在荒誕派戲劇作為“荒誕藝術的巔峰”被人們所熟知之前,杜尚、卡夫卡、達利、畢加索等藝術家的作品中已然出現了“荒誕情節”。此處的荒誕藝術亦是一個泛指概念。“‘荒誕以理性的勇氣揭示了世界景象和人性本體的非理性本質,可以說,荒誕哲學把握了人與世界的真實關系,因而它不是理性的對立面而是一種理性的特殊形態。”如今,“荒誕”似乎成了“后現代”“后后現代”“超現實”“怪誕”“波普”的同義詞。
一、“叛逆”的藝術精神
“叛逆”是荒誕藝術最突出的品格。“叛逆”的出現或許是“上帝死去”以后的迷茫,“上帝之死”不僅僅是對宇宙物質失去信心,更令人否定絕對價值,不再相信某種客觀的價值觀之存在,這種絕對觀念的缺失就是虛無主義的開端;人們知道了原來“人的手中可以什么都沒有”,上帝不存在之虛無便是荒誕藝術的“始作俑者”之一。如加繆所說:“自思想被承認的那一刻起,荒誕就成為一種激情,一種在所有激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激情。”科學技術發達帶來的個人生活空間的異化,世界性的戰爭帶來的失望與迷茫,上帝已死的吶喊……主體缺失帶來的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機造就了“精神缺失”的大時代。“叛逆”正是在“上帝已死”的幻滅語境中萌發出的新芽。
(一)“難以定義”的藝術 人類生存境遇的裂變引發了精神缺失和審美觀念的裂變,在缺失和裂變之后潛藏的是“意義危機”,洞察力極強的藝術家對意義危機做出的外化表現便是“顛覆藝術”。《泉》《4分33秒》《帶胡子的蒙娜麗莎》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轟動,并非取決于它本身的藝術價值,而在于它顛覆性地向人們闡釋了另一種態度——“藝術已死”。
藝術的題材和載體一波比一波令人詫異,新的藝術樣式層出不窮,如何給藝術下定義已經成為一個時代性難題,學界泰斗和先鋒對于此莫衷一是。1917年,馬塞爾·杜尚把男用小便池送入紐約獨立藝術家協會的展覽,成為現代藝術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從此以后便有了“實物藝術”;約翰·凱奇開創性地用“沉默”的方式演出了《4分33秒》后,便有了“行為藝術”。馬賽爾·杜尚1919年在《蒙娜麗莎》的印刷畫上給蒙娜麗莎畫了兩撇胡子和山羊胡須,取名為《帶胡子的蒙娜麗莎》;1939年,他對《蒙娜麗莎》進行了再次創作,這次創作只留下了“達利式”的翹胡子;1965年,他對蒙娜麗莎進行三次創作時,什么也沒做,只是換了一個標題:《剃掉了胡子的蒙娜麗莎》。杜尚的藝術創作行為和藝術表現形式似乎是“顛覆著被顛覆的”,先是否定別人,創造自我,然后再否定創造過的自我,重新再創作自我,可謂是“絕對的自我反叛”。這種重復的動作是否能稱作“藝術”?安迪·沃霍爾是最廣為人知的先鋒藝術家,他對藝術之重新定義通過《時間膠囊》可見一斑,1974年他把自己認為值得收藏的東西放進紙箱里,滿了就打包收藏起來,直至1987年他去世,一共攢了612個紙箱!當箱子被逐一打開,呈現在人們面前的無非是一些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產生的垃圾,甚至庸常以至于虛無,這些看起來毫無意義的瑣碎,如今卻成了各國藝術家爭相模仿的“典范”。這種儲存“生活垃圾”的方式是否能叫作藝術?人們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不僅僅他們的作品是藝術的,他們的行為也是藝術的。人們不禁要問:“什么不是藝術?”這個問題恐怕難以回答。難以回答不是因為藝術無定義,恰恰相反,而是在現代社會形態之下藝術的定義太多。藝術實驗一再創造出新樣式,對藝術下定義,也許是徒勞無益之舉。
(二)“無深度”的審美 關于安迪·沃霍爾藝術“無深度”的思考,杰姆遜用“平面”“無深度”“淺表化”來形容他及其他的作品。杰姆遜似乎認為對于沃霍爾的作品根本無法解釋或者沒有闡釋的必要。如安迪·沃霍爾自己所言:“我的畫面就是它的全部含義,沒有另一種含義在它表面之下。”《瑪麗蓮·夢露》就是瑪麗蓮·夢露,鮮艷迷離的色彩,在無盡的重復中看不到藝術家的態度,因為存在所以存在,不依賴于任何人,也不具有任何言外之意。這種片面化同樣存在于《等待戈多》里狄狄和戈戈的行為和對話中,“無深度”的藝術正是對人的存在連同對世界與人的關系的反叛及其對現存之境的反叛,正因為感覺不到存在的意義,“悖謬”和“虛無”才成為“無意義的意義”之所在,片面化的藝術表現形式也就成了“反叛”的載體。
二、“荒誕”的藝術形態
在現代藝術開始之后,異項藝術越來越受到關注,藝術形態是藝術精神的外化,“荒誕藝術”作為典型的“異項形態”是藝術標示性的具體體現。藝術角色的“理據性”的消失讓藝術意義表達更加深沉;藝術形態的“非邏輯性”的塑造,也成為突出藝術特點的手段。利用荒誕的形式來表現藝術形態實則是對藝術精神的另一種極端化表達,這種具有“異項標出性傾向”的表達正是荒誕藝術最直接的自我獨白。
(一)藝術角色的“理據性”消失 荒誕藝術用非理性和非邏輯的語言表現周遭的一切,在藝術表達中充滿著“非理據性”,然而,“消除理據”未必意味著意義缺失,從某種角度講,消除理據或是丟開理據是為了另獲深意。
就像《等待戈多》那樣,戈多是誰,他什么時候會來,他是不是真的會來,所有人都不得而知,但是卻有人為了等待戈多說著荒誕的話,做著荒誕的事,戈多成了一個“實無存在”的存在,以失落理據獲得了特殊意義。在戲劇里,狄狄與戈戈問答,狄狄問:“戈多是誰?”戈戈答:“戈多就是戈多,我也不知道戈多是誰。”這里的“戈多”幾乎可以用任何詞來替代,此處無理據,但其意義必是“等待”的真諦。在此,理據性滑落后又陡然上升,印證了那句名言:“謂之有托佳,謂之無托尤佳。無托者,正可令人有所托也。”沒有理據的“存在”本來不表達任何意義,也正是因為擺脫了理據性才得以追求到希望通過語句的隨意性揭露人潛意識精神活動真實面目的意義。“戈多”,作為劇里最神秘的角色遲遲未上場,這一角色的藝術形態或許在每一個人心里都是不同的模樣,理據性的消失無限擴大了欣賞者的“臆想”范圍,比“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式的解讀更加“肆意”;理據性消失讓戲劇里的“戈多”成了每個人潛意識里的“真實存在”。同時,無論是作為文字理解層面上還是作為戲劇里臆想式的戈多,“戈多”這一存在都成為意義不在場時所需要的符號;由于其擺脫了“理據性”,暫時性缺乏意義,因而淪為了語境的工具,在前后情節和釋義壓力的雙重壓迫下,被迫表示出了強加的意義,在“荒誕”的視角之內,沒有意義的“荒誕”反而成了最有表現力的符號。
(二)藝術形態的“非邏輯”表現 “非邏輯”相對于“邏輯”而存在,失去邏輯便會本末倒置,但在荒誕藝術作品里,藝術形態的“非邏輯化”表現往往是增強藝術張力的重要手段。就像薩爾瓦多·達利的諸多作品里表現的那樣,“荒誕”的藝術形態已經成了其作品最突出的藝術特色。
達利《記憶的永恒》畫作中表現出了許多類似弗洛伊德所揭示的“夢境與幻覺”的情節,畫面中“荒誕”地創造出了反形式、反傳統、反邏輯的“軟表”形態,顛覆了世人對正常形態的理解:對于時間的流動和存在與否成為永恒的思考題。視覺層面上所表現出的“軟”和現實存在的“硬”本末倒置,用“不正常”替代了“正常”,這種處理手法與《禿頭歌女》中那個時間錯亂的掛鐘頗為相似,失去時間的掛鐘在提醒著:時間的錯亂,秩序的錯亂,意義的喪失。非邏輯的荒誕式藝術表現正是來自于某些“非邏輯”的感知、形而上的異化和痛苦。在荒誕藝術里,正是運用了某種“變形”把想象力從理性和科學的禁錮中解放出來,創造了其獨特的藝術形態。就藝術形態而言,“荒誕”是荒誕藝術里的“正常”,非邏輯、非理性的藝術形態似乎建立于“形而上”之上,大跨度地超越了時空界限,打亂了時間秩序,用超現實的手法傳達不可傳達的東西,解釋不可解釋的事情。荒誕的表現形式成為現代藝術的主流,“非邏輯”和“叛逆”是對精神缺失的反抗和新的尋求,它以反叛的姿態出現,對抗著已經發生異化的現存秩序。
誠如“四體演進規律”所認為的那樣,繼“神時期”“英雄時期”“人的時期”之后,“頹廢時期”已然君臨;崇高感消失,讓位給懷疑論,“荒誕藝術”便是這一規律在現代人類社會中的外化;“反諷”和“叛逆”本身就是意識的終結,同時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發展和自我批評。“荒誕”作為一種表意方式,無可爭辯地成為現代藝術最典型的審美意趣和最核心的審美范疇;它打破了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最終徹底摧毀了藝術本身,無意義之意義成為荒誕藝術的極端歸宿,或許,這就是荒誕藝術的審美意趣之所在。
參考文獻:
[1] 程倩.荒誕觀念的歷史語境及其文學形態.[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3).
[2] 加繆.西西弗的神話[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3] 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