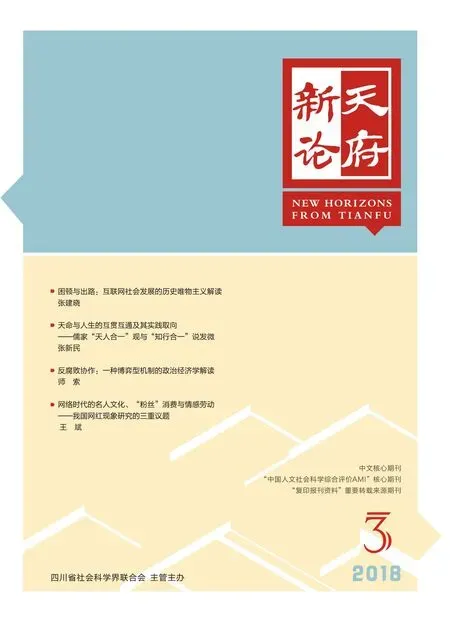網絡游戲、手機游戲的文化反思與道德審視
峻 冰 李 欣
一、語義擴展與文化蘊涵
游戲在本質上屬于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席勒在 《美育書簡》中甚至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①席勒:《美育書簡》,徐恒醇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第90頁。當然,席勒此處所說的 “游戲”實指審美的游戲,即起源意義上的文學藝術創作,并非現實生活中的娛樂性游戲活動。
在寬泛的意義上,游戲是指以物質需求滿足為前提,在特定時空范圍內遵循特定規則的以精神需求滿足為最終目的的社會行為方式。它大致可分為現實活動性游戲和電子游戲兩類。古代的蹴鞠與當下人們所熟知的足球、籃球、乒乓球、羽毛球、象棋、圍棋、斗地主、麻將等較為傳統的現實活動性游戲大不同于現代的電子游戲。電子游戲 (electronic games)又稱視頻游戲 (video games),泛指20世紀末才逐漸完善的依托電子設備平臺進行的交互游戲。時至今日,隨著數字技術與互聯網的飛速發展,電子游戲則多指網絡游戲 (簡稱網游)、手機游戲 (簡稱手游)。網游、手游既是在現代科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化藝術活動,也是特殊的文化藝術商品,類似于電影、網絡視頻等。
其實,球類、棋類、牌類等多為集體參與完成的文體游戲,與單人或多人參與完成的網游、手游在本質上不是一回事。電子游戲改變了人類游戲的行為方式。現實的文體游戲是一次性的社會行為,因參與者的即時在場性使每一次游戲行為都各有個性、情境,并不黏附思想觀念等意識形態的東西;其自我約束和相互監督德機制、游戲規則的相對可變性使游戲主要的娛樂功能和較弱的象征功能內指,而不易也不要求現實的對象化——游戲僅僅是游戲。
在網絡游戲產生之初,人們對沉迷網絡游戲的人嗤之以鼻,認為游戲如同鴉片,打游戲更是一種玩物喪志的無意義行為。現今,數字技術和新媒介的快速發展及基礎設施的日漸便捷性,使依托于互聯網的游戲門類迅速席卷龐大的受眾群體。也因此,不打游戲的人反而受到孤立和歧視。回顧中國電子游戲產業,從 “街機游戲”、“單機游戲”再到網游和手游,在信息、數字技術支持下快速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游戲產業。
二、文化語境與道德盲點
21世紀以降,各式各樣文化的發展都離不開以互聯網、移動智能終端為標志的信息、數字技術革新。基于科技的高歌猛進態勢,文化形態也逐漸轉向 “數字化生存”。互聯網、智能手機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重要途徑和手段。對相當數量的年輕 “網生代”來說,網絡、智能手機所營建的虛擬想象性世界成為其自我表達的新陣地;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與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媒介形態牢牢地捆綁在一起,網絡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他們的 “異度空間”;借助數字技術與新媒介的合謀共融,他們不斷創造和傳遞極為個性化的不無從眾意味的又可謂 “后現代”的文化。由新技術與新媒介共謀催生的網游、手游對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力滲透,技術失控論日漸引起人們的關注。對流行文化和奇觀世界天生好奇的青少年群體愈益成為網游、手游的受害者。毋庸置疑,商業利益驅使下的游戲產業生態滋生了諸多不可回避的急需解決的新問題。
基于互聯網平臺與數字化現代視聽技術之上的網游、手游是前所未有的近二十年來才成長起來的新事物。視聽形象的先驗性、符碼的象征性、編碼結構的暗示性、游戲規則的不可變性等使其并不是一次性的純粹娛樂性行為,而是有固定文本的可持續復制、傳播的文化藝術活動。它能夠一次次傳遞被游戲制作者先于游戲玩家植入的主體意識、文化觀念、審美情趣和思想傾向,進而影響受眾的語言習慣、情緒表達方式和實踐行動規范等。
現實活動性游戲因一次性、自娛性、不確定性等特點一般不會對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產生太大的影響。而玩家多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網游、手游,因游戲 (尤其是手游)施行的個人化、隨意化、時空的碎片化及與日常生活無節制的同構化,其缺少把關人的緣于自然逐利、感官刺激滿足、窺視癖迎合及泛娛樂化目的,而自覺不自覺地附著的一些少兒不宜的反主流價值觀的思想觀念,極大地左右未成年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建構,進而影響處于模仿成人階段、本能具有好奇、探秘心理的孩子們的思維習慣和現實言行。因自我約束意識缺乏,行為被誘導、實踐被規約等導致的未成年人對網游、手游的沉迷,大大擠占正值緊張求學階段的孩子們本就不多的有效學習時間,應該在場的富有教益的經典文本的缺席自然有損所應倡導的中外優秀文化、中華美學精神的傳承和弘揚訴求。
2017年,《人民日報》、新華社曾多次發文評價一款名為 《王者榮耀》的游戲,使這一現象級游戲迅速成為人們觀察與審視的焦點。2017年4月20日召開的UP2017騰訊互動娛樂年度發布會上,騰訊集團高級副總裁馬曉軼公開宣稱:《王者榮耀》游戲累計注冊用戶已逾兩億,并已成為全世界用戶最多的多人在線戰術競技手游。在此后不久,人民網亦發表評論稱:“(王者榮耀)日活躍用戶超過8000余萬人,每7個中國人就有1個人在玩,其中 ‘00后 ’用戶占比超過20%。”①《評 〈王者榮耀〉: 是娛樂大眾還是 “陷害” 人生》, 人民網,2017年7月3日,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7/0703/c1003-29379751.html.之于網游、手游,“防沉迷”一直是一個欲舊還新的話題,因這款游戲引發的涉及青少年沉迷其中的負面新聞時有發生。盡管 《王者榮耀》游戲制作團隊立即推出所謂的 “防沉迷系統”,但此種現象不禁啟人深思:如 《王者榮耀》這樣的網游、手游,為何會讓人如此迷狂?
三、交流困境與盲目從眾
直面青少年群體于電子游戲世界的狂歡,不得不讓人思考:究竟是何原因讓孩子們蜂擁而上?值得人警醒的還有哪些方面?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和討論可從 “個人與社會”、“個人與他者”、“個人與自我”這三個層面展開。
(一)個人與社會:共同性與個性化/流行文化與自我認同
“當代社會,流行文化成為一種大眾普遍接受的文化樣態;對流行文化最為敏感的青少年群體正在流行文化的 ‘趨同性’和 ‘模仿性’特質影響下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雷同行為。”②劉芳:《“制造青春”:當代流行文化與青少年的自我認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頁,第3頁。作為大眾傳媒與商業市場合謀共生的流行文化,已逐漸從精英階層蔑視的對象變成當今社會各階層競相追捧的文化形式。“當代中國,流行文化對青年人的影響力甚至已經超過了主流文化的影響力,超過了家庭和學校正統文化的影響力,越來越多的主流媒體,成為了流行文化的制造者和傳播者。”③劉芳:《“制造青春”:當代流行文化與青少年的自我認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頁,第3頁。
在某種程度上,作為衡量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個指標,自我認同可謂青少年成長階段的重要心路歷程。一如埃里克森所說:“青少年期是自我認同產生、發展再到成熟的一個關鍵時期,也是最容易出現認同危機的時期。”④Erikson, Erik 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68.在此階段,青少年對社會上任何事物都保有新鮮感和好奇心。這一群體對流行文化的追逐與偏好,有意識地討好式地與所屬群體的偏好保持一致,即自我認同中的 “共同性”——對網游、手游的趨同性追逐實是青少年群體欲借此來確認自身歸屬以及群體中的 “共同”部分。有了 “共同性”的基本 “安全”條件,其方開始尋求 “個性化”的自我表達,也即 “我”是一個怎樣不同于他人的我及 “我”在群體中的位置。在后現代消費文化的氛圍中,對物質乃至金錢符號意義的消費觀念也深深影響了當代青少年;其中一些人甚而通過向游戲充值來確認和提升自我在群體中的地位。但當這一 “個性化”的行為被同齡者趕上時,之前產生的滿足感旋即消失,遂互相追逐進而在一次次對先前消費行為的超越上獲得自我身份的一次次確認——這顯然是青少年群體復制、模仿消費社會中成人行為的結果。對缺乏信息辨別能力的青少年而言,在其尚未完成完全的“社會化”之時,極易陷入膚淺的對 “物”與 “符號”的跟風式消費,并以此來建構自我身份認同和之于群體的個體地位。
換個角度看,在大的社會泛文本中,由大眾傳媒塑造的流行文化也時時刻刻影響著青少年的認知、態度和行為。“我們像港臺明星那樣說話,像韓國明星那樣打扮,做出歐美明星的表情,像日劇那樣戀愛。”⑤陸玉林,常晶晶:《我國青年文化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簡析》,《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數年前多數人認為打游戲是一種浪費時間的無意義行為,而現在卻成為不少人競相追逐的時尚。當電子游戲的娛樂文化借大眾傳媒可給人帶來經濟利益和社會地位時,網游、手游等的“無意義”被暫時蒙蔽,游戲主播、游戲解說甚至成為青少年群體夢寐以求的新職業,因為而今現實生活中并不乏通過網游、手游及相關產業從 “草根式”人物到月入百萬元、名利雙收的游戲主播的戲劇式轉變的例子。無疑,這一現象值得人們警醒。因為當流行文化制造出一個個輕而易舉的神話般的 “成功”夢想時,無辨別能力的青少年便會產生對主流文化的質疑,甚而不再相信傳統權威和“知識改變命運”的經典律例。而當這一文化現象越來越甚之時,傳統的主流意識文化便會產生被解構和被動搖的危險。
(二)個人與他人:群體排斥與社交孤立
存在主義心理學用 “存在孤立感”一詞意指個體在現實世界中的人際孤立感 (有人格障礙或缺少社交能力的個體難以與他人進行正常交流所產生的距離感和疏遠感)和內在孤立感 (希望參與人際世界的個體因主觀經驗的獨特性、分離性與自我體驗性而致與他人無法交流、溝通的孤獨感、焦慮感)。美國社會心理學家雪莉·特克爾在 《群體性孤獨》一書中詳細地探討了在線社交網絡與短信文化對人與親戚、朋友和社會的交往方式的改變。她將互聯網與數字技術影響下的人際交互比作一種復雜的舞蹈——隨著將更多的交互放到電腦和手機上,人們正在忘記如何跳舞。她認為,人們已置身機器人時刻,并將重要的人類關系,包括生命中最脆弱的時刻都交給了機器人;但那種能夠做期望中自己的在線時刻,卻失去人們過往習慣的那種彼此相連的粗糙的、人性的部分。她堅稱,人們對人工智能的依賴是不健康的。大多時間呆在線上,人們便會在非虛擬的生活中變得空前孤立,導致情感脫節,產生抑郁、焦慮感。①雪莉·特克爾:《轉折點》,《群體性孤獨》(序),周逵、劉菁荊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人和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是一種平行的關系,但人和機器,或者人和科技的相互依存是不平行的,后者對情感有侵蝕性。就像很多人對Facebook的情感十分復雜。即便我們偶爾覺得有了Facebook,生活簡直一團糟,但同時我們也不清楚如果沒有了Facebook,我們又該如何生活。我不記得有哪一款消極軟件能像它這樣深深扎根于文化交流與人際交流。科技讓我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可以在任何地方交流,也讓我們的寂寞無處不在。”②雪莉·特克爾:《好像是一個陌生人處于一個陌生的世界》,《新周刊》2012年第8期。
由于對網絡虛擬世界和電子游戲的過度沉迷、依賴,人們 (尤其是青少年)很容易在這一興趣點上形成簡單的排他性的交際圈子——過往由貧富差別、信仰異同、知識多寡、形象美丑等形成的交際鴻溝被輕易填平。當然,由網絡游戲、手機游戲等興趣點重新織就的圈子與圈外世界則重現新的交流障礙。也正因如此,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馬菲索里曾提出 “新部落”一詞,即社會群體之間不再依賴于階層、性別和宗教等傳統的結構因素、消費方式,“成為個人創造當代社交以及小規模社會群體的新形式”。③鮑鯧:《網游:狂歡與蠱惑》,蘇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0頁。而當群體以 “新部落”的方式重新結合之后,被排斥在群體之外的人則會產生社交孤立感。
確乎如此,青少年因社會閱歷尚淺,多缺乏辨別是非的能力,從眾心理嚴重。當同學中的大多數都在玩同一款網絡游戲且課下熱議的時候,被排斥于此群體之外的少數人則會感到與此群體格格不入的孤立感,由此便產生群體內外的沖突與調控。在群體效應的影響下,不少青少年為防止產生這種“群體排斥”與 “社交孤立”的孤獨感、恐懼感,并增加與同齡人的親密關系而加入網游、手游的隊伍中來。這也即是大衛·里斯曼在 《孤獨的人群》中所提出的 “他人導向性人格”:“他人導向的孩子從小時候起,就從大眾傳播媒介中學習生活的藝術和與他人交往的訣竅。”④大衛·里斯曼:《孤獨的人群》,王崑、朱虹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3頁。
(三)個人與自我:“影子的影子”的影子與自我想象的投射
由于一出生就 “浸泡”在網絡所構建的世界中,故青少年群體在今天又被戲稱為 “網絡的原住民”—— “隨著虛擬與真實的日趨融合,互聯網正在改變他們的生活和思維方式,甚至成為他們的生活空間和環境本身”⑤李春玲,科茲諾娃,等:《青年與社會變遷: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45頁。。
柏拉圖在 《理想國》中寫到一個關乎洞穴的比喻:洞穴中有一批自出生就被禁錮在這里的囚徒。其身后和身前各有一面墻,身后墻的正上方有一堆火,火光可清晰地把器具的影子投射到囚徒前面的那面墻上。由于只看到過影子,囚徒自然認為影子是此間唯一真實的事物。柏拉圖就此提出一個著名的觀點:“影子的影子”描述了模仿與藝術的關系,即人們所看到的世界并非真實的世界,而是真實世界的影子;藝術品是模仿人類世界創造的,所以是真實世界的 “影子的影子”。同理,既然人們所看到的世界是真實世界的影子,那么網絡空間之于人們所生活世界的 “選擇性的表達”即可稱之為“影子的影子”,而網游、手游等電子游戲作為基于虛擬網絡空間而存在的產物,其話語表達與存在形態均憑依網絡空間的規則和秩序,故可說成是 “影子的影子”的影子。在重重模仿之下,沉迷于網游、手游的青少年離現實越來越遠;而習慣于游走在 “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世界中的他們,遂把可謂 “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游戲世界看作真實世界本身,將其作為一切思維方式和行為標準的準繩。
在這個 “‘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游戲世界,青少年更是在大眾媒介符號和 ‘擬像’的過度生產與再生產中目眩神迷,神魂顛倒,無所適從,找不出其中任何固定的意義聯系”①劉芳:《“制造青春”:當代流行文化與青少年的自我認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217頁。。這便產生一個普遍的現象:缺乏判斷力和信息選擇能力的青少年,盲目追求符號膚淺的意義,通過游戲消費,帶入自我投入式的想象;青少年通過不斷往游戲中充值或為他人充值來滿足自我虛榮感,同時管理自我在同伴中的印象。這多少類似于后現代消費社會中人們借消費來體現自身階層和品位的現象。其實,這是自我想象的投射,誤以為消費了具有某個階層的符號意義的商品,自己在他人心中就可以被歸屬為某個階層。
四、道德底線與責任意識
現實已一再證明,沉迷網游、手游導致了不少青少年的人生悲劇,對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也產生了較大的負面作用。為此,網游、手游必須有道德底線。習近平同志 《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②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10月15日。這就要求網游、手游開發、運營商者基于良心之上的自省自律和道德約束。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顧倫理道德影響、一味追逐利益的網游、手游制作與運營顯然是極不妥當、極不負責的;政府相關部門出臺有關規定加以管理、限制無疑是可以理解而且也是極為必要的。事實上,不僅是網游、手游,即使是廣播、電影、電視等文化藝術產品,無論在古今中外,都是有管理、有限制的。
(一)源頭:做有責任擔當的游戲開發運營商
不應諱言,作為市場行為的游戲產業的盈利目的似無可厚非。但作為社會的子系統,游戲業界應主動開發具有社會良性效益的游戲產品,在取得經濟效益的同時主動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
1.展示出 “解毒”的誠意
勇于社會擔當,開發優質健康的游戲產品。雖然不能視游戲為洪水猛獸,但其當下所造成的社會負面影響亦不可漠視。換句話說,網游、手游的開發、設計不能一味追求轟動效應、刺激體驗和經濟效益,亦要多想其對國家、社會乃至個人所造成的影響。漠視道德倫理、奉行經濟至上主義的游戲開發運作顯然是要不得的。因為在 “數字化生存”時代,人們的行為多從媒介中尋找依據;而在眾生狂歡的游戲過程中,網游、手游等提供給受眾的文化產品所暗藏的價值取向、審美情趣、判斷標準等將會影響受眾,在不遠的將來,其影響也許遠遠超過傳統學校教育對人的影響。實際上,《中國游戲產業報告》已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2017年上半年中國游戲市場實際銷售收入高達997.8億元 (人民幣),同比增長26.7% (210.3億元的收入增量為2009年以來所有上半年增收的新高),中國的游戲用戶也達至5.07億人。①《 2017年1—6月中國游戲產業報告》, 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網,2017年 7月 27日,http://www.chinaxwcb.com/2017-07/27/content_358780.htm.對此現象,經濟學家愛德華·卡斯特羅諾瓦將之稱為現實空間向游戲空間的 “大規模遷徙”。“同時,我們還把認知努力、情感能量和集體關注慷慨地從現實世界轉投到游戲世界,創造出一座龐大的虛擬倉庫”②簡 ·麥戈尼格爾:《游戲改變世界》,閭佳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4頁。。鑒于此,游戲業界開發出積極的、向上向善的、有正能量的、有社會責任感的至少是有益無害的優質健康的游戲產品極為必要也十分緊迫。
建立有效的防沉迷系統十分必要。好奇心強、自控能力弱、辨識能力差的青少年的注意力極易為流行事物所吸引,進而沉迷于不無炫酷意味的網游、手游等游戲體驗中,影響學習進步和身心發展。建立有效的防沉迷系統,同時從內容源頭上遏制其另類意識形態的發展則十分必要。《王者榮耀》官方制作團隊因此推出 “成長守護平臺”,并采取一系列規約來限制未成年人上網的時長和消費額度,體現出游戲開發、運營商在經濟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平衡的努力。
2.肩負文化抱負,切勿成為商業附庸
游戲的設定離不開中華文化,具有文化抱負應為必然。騰訊集團副總裁程武在 “中國國際數字產業娛樂大會上”就表示:互動娛樂產業在本質上是文化創意產業,除了商業價值,還應該具有一種文化抱負。
承當文化抱負的理想應真真切切地將弘揚傳統文化作為游戲長期的核心價值觀輸出,力求對受眾尤其是青少年群體產生較為積極的影響,并與主流意識形態產生良性互動。切勿夸張、扭曲、歪解歷史,切莫讓網游、手游等成為文化的粉碎機和商業陰謀。
(二)過程:相關部門在網游、手游流通環節應有所作為
在數字技術發展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電子游戲文化,同樣難逃后現代消費文化的影響。網游、手游從 “一種生命的自由感和精神世界的解放”演變成文化工業的產物,而對金錢的追逐又使其漸向商業利益妥協。單純依靠電子游戲企業的自律顯然不太現實,政府相關部門在游戲的流通環節也應有所作為。
站好崗:加大對相關條例的執行力度。由文化部發布,于2017年8月1日正式實施的 《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為中國第一部專門對網絡游戲進行管理和規范的部門規章。它系統地對網絡游戲的娛樂內容、市場主體、經營活動、運營行為、管理監督和法律責任做出了明確規定。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實施 重點保護未成年人》,2010年8月2日,http://www.scio.gov.cn/index.htm.類似于此,為保護未成年人所頒布的相關條例,如 《網絡游戲管理暫行辦法》《關于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實施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的通知》《網絡游戲防沉迷系統開發標準》等,都從各方面提出了限制未成年人上網時間、預防未成年人迷戀網絡的規約,但它們多為條款性質的內容,法律效力相對較低且強制性較弱,在執行過程中更是缺乏相關專門機構對其進行監管,因而收效甚微。
把好關:嘗試建立電子游戲分級制度。早在1996年,美國匹茲堡大學心理學家金伯利·揚便注意到互聯網上癮問題,遂在賓夕法尼亞州成立 “互聯網上癮康復中心”;2009年,美國另一家網癮戒除中心在西雅圖成立。由此可見,沉迷網絡乃普遍現象。事實上,有些國家業已建立 “網絡游戲分級制度”。為防止網游、手游等電子游戲所黏附的色情與暴力對青少年的危害,美國頒布年齡分級法:“在美國公平貿易委員會的監管下,非營利機構 ‘娛樂軟件分級委員會’將游戲分為6個級別:3歲以上兒童、6歲以上兒童、10歲以上兒童、13歲以上兒童、17歲以上成年人、只限18歲以上成人。其中 ‘只限18歲以上成人’的標準是:游戲里有長時間的高強度暴力或色情及裸體圖像。此外,標準還采用不同深度的黃色和紅色來標識游戲中的暴力或色情內容。美國公平貿易委員會還提醒家長采用游戲機或電腦中的 ‘家長控制’設置,或安裝過濾軟件,以防止青少年接觸不良信息。”①《美國實行網絡游戲分級管理 六個級別劃分清晰明確》,中新網,2010年4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it/it-itxw/news/2010/04-20/2235841.在澳大利亞,如果相關企業對青少年沉迷網游放任不管,該企業將被處以11000~14100澳幣的罰款(約合人民幣58622~75143元)。韓國對縱任青少年沉迷網游的企業的處罰力度也很大,其 《青少年保護法》明確規定:企業有義務針對未滿16歲的青少年的網游時間進行強制性控制,即在深夜12點至早晨6點之間切斷其網游信號,違規者可被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0萬韓元以上罰款 (約合人民幣60000元)。對網游尤其是手游附帶的色情和暴力問題,中國的法律法規尚存較大空白。顯然,除了要不斷完善相關法律規約體系,還需建立專門的監管和防控機構,適當加大監管和懲罰力度。
(三)終端:家庭教育乃為良方
曾有一位小學生這樣說:“當我孤單的時候,媽媽就把手機給我。”這句話折射出一個較為普遍且不容忽視的現象:家庭教育對網游、手游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缺乏足夠的認識。
孩子的成長離不開家長的教育和引導。“回顧互聯網不長的發展史,防沉迷一直是兩代人斗爭的主題。只是當年被父母扭著耳朵從網吧拎回家的少年,悠然長大,成了半夜捉到孩子還在玩手機的憤怒父母。”②《學生沉迷是家庭教育問題》, 人民網, 2017 年 7 月 11 日, http://tech.sina.com.cn/i/2017-07-11/doc-ifyhwefp0538427.shtml.其實,對青少年對網游、手游的沉迷,父母亦要承擔較大的管束責任。曾有學者采用問卷的方法研究家庭因素對青少年沉迷電子游戲的影響,發現 “在家庭生活匱乏的情況下——表現為家庭關系不和睦或父母離異、隔代教育或父母長期不在身邊、親子互動缺乏等,青少年出現游戲沉迷現象的比例明顯高于正常情況。正因為父母不在場或者長期與父母互動缺乏而造成的精神空缺,青少年社會化過程中所必須的精神支持、鼓勵和指引轉而在電子游戲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滿足”③劉德寰,彭雪松,謝新洲:《作為補償機制的游戲沉迷——青少年游戲沉迷的家庭因素》,《廣告大觀》(理論版)2014年第3期。;有學者 “通過對16個網癮青少年的深度訪談分析發現親子關系具有暴力、專制、溺愛、忽視等特征時,孩子最易沉迷網絡”④蘇斌原,張衛,蘇勤,喻承甫:《父母網絡監管對青少年網絡游戲成癮為何事與愿違?——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模型》,《心理發展與教育》2016年第5期。。鑒于此,營造良好的家庭環境和融洽的親子氛圍,也是根治青少年網游、手游成癮的一個重要路徑。
五、思考之外與哲學啟示
青少年是國家、民族的未來,其健康發展必須引起廣泛的重視。遏止青少年網游、手游成癮這一現象,亟須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從源頭 (游戲制造商和開發商的嚴格自律)、過程 (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作為)、終端 (家庭教育的關愛營建)等各方面共同促動方可見成效。
有學者不無擔憂地說:“如果人們已經習慣了數字化生存,人類過分地依賴電腦,如果哪一天數字系統徹底崩潰了,人類將如何生存?”⑤遲宇宙:《對抗性游戲——’70以后東西方文化批判》,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9年,第404頁。在 《技術至死:數字化生存的陰暗面》一書中,白俄羅斯科技互聯網批評家葉夫根尼·莫羅佐夫反復闡述了這樣的憂慮:數字化生存的誘惑,即當代人們企圖使用游戲化或流行的量化跟蹤等數字技術手段來 “解決”所有問題。但如果我們看不到數字化生存的陰暗面,便終將毀于我們所鐘愛的 “技術”。⑥參見葉夫根尼·莫羅佐夫:《技術至死:數字化生存的陰暗面》,張行舟、閭佳譯,電子工業出版社,2014年。無疑,這對網游、手游的制作、運營商和游戲玩家的 “泛自由論”、“自由選擇論”和 “自由掌控論”提出了深刻的警示。
強調 “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①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外國文藝》1980年第5期。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也不得不承認所謂的 “自由選擇”因選擇的痛苦、恐懼及其極端境遇而最終是自欺的也是虛無的。因外部世界的不可知,僅憑個人“自由意志”驅使的選擇既是自由的也是盲目的——行動主體不可能知道 “自由選擇”的結果是惡還是善,因而薩特亦認為個人的自由 “完全離不開別人的自由,而別人的自由也離不開我們的自由”②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外國文藝》1980年第5期。;“人可以作任何選擇,但只是在自由承擔責任的高水準上”③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外國文藝》1980年第5期。,而且必然存在的道德化傾向使人 “不能選擇更壞的”,“選擇的總是更好的”④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外國文藝》1980年第5期。。這樣,盲目且要負責的個人 “自由選擇”實際上不可能達至真正的 “自由”。因而,薩特在 《存在與虛無》一書中總結道:“自由,顯然就是在人的內心中被存在的、強迫人的實在自我造就而不是去存在的虛無。”⑤薩特:《存在與虛無》,陳宜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第566頁。
《孟子·離婁章句上》:“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1789年頒布的法國大革命綱領性文件 《人權宣言》第4條寫道:“自由即有權做一切無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概言之,自由之所以是自由,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下和在一定的限度內。也就是說,只有合一定規矩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周易·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無疑,這些都值得網游、手游的開發、運營商以及廣大網游、手游玩家自省、深思、警醒。當然,新生事物從出現到進入社會符號系統,必然要經過歷史經驗的洗禮和社會編碼體系的調節。顯然我們不能簡單地視電子游戲為洪水猛獸;我們期待有一天網游、手游問世時就帶著正能量,進而塑造現實世界的真正 “英雄”,用簡·麥戈尼格爾的話說, “讓每個人都擁有改變世界的力量”⑥簡·麥戈尼格爾:《游戲改變世界》,閭佳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第2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