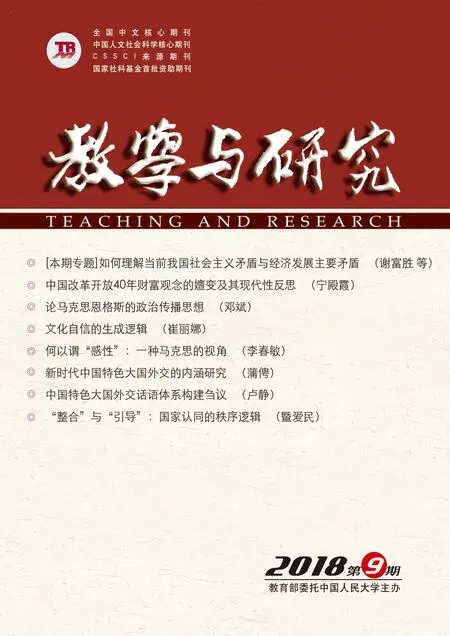何以謂“感性”:一種馬克思的視角
——以《1844年經(jīng)濟學(xué)哲學(xué)手稿》為例
“感性”是哲學(xué)世界觀的重要范疇,對感性的闡釋貫穿于哲學(xué)演進的不同階段,它在造成哲學(xué)話語體系分野的同時,也衍生出不同的思想范式。馬克思堅持將感性作為探尋世界的基礎(chǔ)和開端,馬克思視野中的“感性”本質(zhì)上是一種“感性活動”(即實踐),是體現(xiàn)人的主體性的對象化活動,它是馬克思對“思辨哲學(xué)”進行批判性反思、建構(gòu)新的世界圖景的重要路徑,不僅如此,在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主題的現(xiàn)代化轉(zhuǎn)變中,“感性”是一個重要維度,它打開了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與后馬克思主義動態(tài)融合的視域,本文僅以《1844年經(jīng)濟學(xué)哲學(xué)手稿》(以下簡稱為《手稿》)為例,嘗試梳理馬克思對感性的思考及這種思考的當(dāng)代性。
一、“感性”的歷史生成
在哲學(xué)話語體系的歷史嬗變中,“感性”的闡釋向度是多維的,“感性”與“理性”相對,對“感性”的探討往往與“感覺”“身體”“愛欲”等生命體驗聯(lián)系在一起,它通向“現(xiàn)象”而非“本質(zhì)”、“質(zhì)料”而非“形式”、“形而下”而非“形而上”的領(lǐng)域,對“感性”的貶抑有著悠久的知識論傳統(tǒng)。
在古代哲學(xué)世界觀的建構(gòu)中,“感性”從未缺席。柏拉圖主張“理念世界”與“可感世界”的分離說,前者是真理的領(lǐng)域,后者是意見的領(lǐng)域,前者是不變的、唯一的、永恒的本質(zhì)世界,后者是易逝的、多產(chǎn)的、有朽的現(xiàn)象世界,“理念世界”統(tǒng)攝“可感世界”,人要獲得真知,必須在可感的個別事物之外,探尋那個理智可知的真實的領(lǐng)域。“當(dāng)一個人企圖靠辯證法通過推理而不管感官的知覺,以求達到每一事物的本質(zhì),并且一直堅持到靠思想本身理解到善者的本質(zhì)時,他就達到了可知事物的頂峰了”。[1](P298)亞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圖的“分離說”,將物理學(xué)的研究對象確定為運動著的事物之中的“形式”和“形態(tài)”,主張本質(zhì)即蘊藏在“可感事物”之中,所謂理念其實就是“可感事物”之內(nèi)的“形式”,經(jīng)驗世界的“具體實體”都是質(zhì)料和形式兩者的統(tǒng)一,因此,回到“可感世界”才是真理之路。在此之后的晚期希臘哲學(xué),“感性”與倫理世界的意義建構(gòu)聯(lián)系在一起,伊壁鳩魯派的快樂主義滲透著“感覺主義”的原則;斯多亞派信奉“按照自然生活”,將對感性的順從視為一種非理性的情感;新柏拉圖主義則繼續(xù)沿著柏拉圖的路線,將超越“可感世界”、向“理性”的攀升作為靈魂打破肉體禁錮的必修課。失范的世界催生著新的秩序和世界根據(jù),基督教哲學(xué)應(yīng)運而生。在基督教哲學(xué)的世界圖式中,感性與塵世相連,它是朝向現(xiàn)世的,神的意志在于驅(qū)除感性的主觀隨意,使靈魂得以拯救,非感性在其中獲得了絕對的優(yōu)先性和統(tǒng)治性,神的意志是感性世界的根據(jù),人對上帝的仰望和人的自我救贖奠定了宗教世界觀的基本格局,對感性的探討從屬于神學(xué)問題。如:在安瑟爾謨(Anselm)關(guān)于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中,上帝的無限完滿性是無法從可感世界中找到依據(jù)的,必須訴諸“上帝”這一概念本身的完滿性,通過對“上帝”這一概念的邏輯分析得以實現(xiàn)。
文藝復(fù)興重新發(fā)現(xiàn)了人,人與世界的可感性從超驗的神的意志中解放出來,這在一定程度上恢復(fù)了感性的合法性,一個“感性”的世界得以呈現(xiàn),人文主義者對人性的高揚賦予了人本身在世界中的崇高地位,人性的解放意味著感性的解放。從笛卡爾開始的近代哲學(xué),理性主義內(nèi)部出現(xiàn)了經(jīng)驗論與唯理論的對峙,唯理論從天賦觀念出發(fā),經(jīng)驗論從感性經(jīng)驗入手,“感性”在近代認(rèn)識論探討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知識的基礎(chǔ)和來源上,洛克批判了天賦觀念論,主張經(jīng)驗是知識的唯一來源,他的探討直接導(dǎo)向了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主義認(rèn)識論。貝克萊的“存在即是被感知”,把心靈作為感知的前提,“感性”的心靈具有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康德指出:傳統(tǒng)形而上學(xué)的虛假性在于理性對感性直觀和感性經(jīng)驗的僭越和任意構(gòu)造,康德重視感性,將人的感性定義為:“通過被對象所刺激的方式來獲得表象的這種能力(接受能力)”。[2](A19/B33)感性在接受表象的過程中不是被動的,確切地說,感性直觀的質(zhì)料是被給予的,但其形式是先天的。在實踐理性層面,康德是理性主義者,主張以純粹理性為基礎(chǔ)進行道德實踐,純粹理性是與經(jīng)驗論者和啟蒙學(xué)者所主張的“感覺”或“情感”相對的。
二、“感性的直觀”:對超感性話語的消解
馬克思對感性的思考受到費爾巴哈的深刻影響,費爾巴哈是促使馬克思經(jīng)由思辨哲學(xué)通向?qū)嵺`哲學(xué)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馬克思對現(xiàn)實的感性世界的關(guān)注,費爾巴哈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示。
1.對思辨哲學(xué)“理想總體”或“抽象總體”的消解。費爾巴哈將斯賓諾莎、謝林和黑格爾分別作為近代思辨哲學(xué)的創(chuàng)始者、復(fù)興者和完成者,認(rèn)為思辨哲學(xué)與神學(xué)有著本質(zhì)上的共通性。他敏銳地指出:“思辨神學(xué)與普通神學(xué)的不同之點,就在于它將普通神學(xué)由于畏懼和無知而遠(yuǎn)遠(yuǎn)放在彼此世界的神圣實體移置到此岸世界中來,就是說:將它現(xiàn)實化了,確定了,實在化了”。[3](P101)從而把“彼岸的精神世界”理解為非對象化的神秘東西,因此,思辨哲學(xué)視野中的“絕對”從心理學(xué)來講是一種抽象,這種抽象抽去一切具體規(guī)定的異質(zhì)性,并將其實體化,在這個意義上,“形而上學(xué)是秘傳的心理學(xué)”。[3](P104)不僅如此,如果我們歷史地看,這種思辨哲學(xué)的抽象總體只是舊的“神學(xué)—形而上學(xué)”的翻版,是“理性化和現(xiàn)代化了的神學(xué)”,[3](P103)但它本質(zhì)上是人的本質(zhì),是超越和排除了人的世界之外的人的本質(zhì)。神學(xué)的本質(zhì)的無限性其實是“抽象的有限本質(zhì)”的體現(xiàn),思辨哲學(xué)意義上的“絕對精神”不是別的,而是一種有限精神,它在抽象的過程中完成了與自身的分離。歸根結(jié)底,“僅僅被思想成存在的絕對,不是什么別的東西,只是存在本身。”[3](P102)
2.對思維與存在關(guān)系的再思考。費爾巴哈將思辨哲學(xué)作為超感性哲學(xué)話語的終結(jié)者和集大成者,對思辨哲學(xué)的批判滲透了他對哲學(xué)基本問題闡釋路徑的新洞見。他將“思維與存在的同一”作為思辨哲學(xué)的中心點,指出這種“同一”的實現(xiàn),是通過將“思維與存在的對立”放置在思維之內(nèi)完成的。這樣,對思維之對立物之存在的思考就轉(zhuǎn)化為思維對自身的反思,思維與存在的對立就成為思維與自身的對立,這種對立的揚棄只能在思維自身中,通過思辨活動得以實現(xiàn)。但這種存在只是與思維同一的存在,是被思維捆綁的抽象了的存在。它只表明:絕對精神囿于自身,無法通達存在本身。在這個意義上,費爾巴哈指出,思辨哲學(xué)的抽象歸根結(jié)底是在自然之外探尋自然的本質(zhì),人之外探尋人的本質(zhì),在這個過程中,存在之于思維的先在性被顛倒了。在其中,“思辨思維本身卻是全部實在的尺度,它只認(rèn)為它自己可以進行活動的,可以作為思維材料的那種東西是實有的”。[3](P156)哲學(xué)的客觀來源和進程,服從于它的主觀來源和進程,“存在既然被思辨思維哲學(xué)拉進他的范圍而概念化了,所以存在也就只是一個純粹的幽靈,這種幽靈與實際的存在與人們所了解的存在,是絕對矛盾的”。[3](P156)費爾巴哈倡導(dǎo)的新哲學(xué)把“存在”看作是“存在的對象”、“存在于自身的對象”,新哲學(xué)的基石是“提高了的感覺實體”。[3](P168)
3.重新確定“感性”的致思路線。費爾巴哈嘗試重建“感性”的合法性,他指出:“人的感覺在舊的超越哲學(xué)的意義之下,是沒有經(jīng)驗的、人本學(xué)的意義的;它只是本體論的,形而上學(xué)的意義。”[3](P168)費爾巴哈將“感性”的意義與“真理性”、“現(xiàn)實性”等同,一個對象得以在真實的意義上存在,必須通過感覺,僅僅通過思維本身是無法完成的。不僅如此,思維本身亦是通過感性得以確證的。他認(rèn)為,“只有現(xiàn)實性的現(xiàn)實事物或作為現(xiàn)實的東西的現(xiàn)實事物”[3](P166)才可以作為感性對象的現(xiàn)實事物,即“感性事物”,感性的原則的實質(zhì)是人性的原則。費爾巴哈將感性提升到存在論的高度,指出:“在我看來,感性不是別的,正是物質(zhì)的東西和精神的東西的真實的、非臆造的、現(xiàn)實存在的統(tǒng)一;因此,在我看來,感性也就是現(xiàn)實。”[3](P68)在這里,感性一方面指向了對象世界,即“感性的自然”,這里的自然是一個現(xiàn)實的自然,不是被絕對精神統(tǒng)攝的自然;另一方面指向了人的主體世界,即“感性的人”,這里的人是將理性、意志與愛作為內(nèi)在本質(zhì)的人。不僅如此,“感性”本身具有本體論意義,“真理性,現(xiàn)實性,感性的意義是相同的(identisch,同一的)。只有一個感性的實體,才是一個真正的,現(xiàn)實的實體”;“感性的、個別存在的實在性,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用我們的鮮血來打圖章來擔(dān)保的真理”。[3](P166、68)
費爾巴哈將“感性”作為批判舊哲學(xué)尤其是思辨哲學(xué)的利器,馬克思對此給予充分肯定,認(rèn)為這是費爾巴哈的“真正的發(fā)現(xiàn)”。具體來說,這種“感性”的致思路徑“把基于自身并且積極地以自身為根據(jù)的肯定的東西同自稱是絕對肯定的東西的那個否定的否定對立起來”,重新賦予“肯定的東西”即“感覺確定的東西”以合法性,設(shè)定了“現(xiàn)實的、感性的、實在的、有限的、特殊的東西”,[4](P246)揚棄了無限的東西,確立了真正的唯物主義和實在的科學(xué)。后者宣告了思辨哲學(xué),包括自柏拉圖以來的哲學(xué)—形而上學(xué)對感性觀的破產(chǎn),這是費爾巴哈的偉大功績。但是,馬克思同時指出了費爾巴哈感性論的有限性:“費爾巴哈對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僅僅局限于對這一世界的單純的直觀,另一方面僅僅局限于單純的感覺。”[5](P75)他的感性最終陷入到單純直觀的窠臼,“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確實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他沒有把人的活動本身理解為對象性的活動。”[5](P54)費爾巴哈的感性論是必然陷入困境的感性論,這種困境就是“普通直觀”與“哲學(xué)直觀”的二元性,以至于“他要是不用哲學(xué)家的‘眼睛’,就是說,要是不戴哲學(xué)家的‘眼睛’來觀察感性,最終會對感性束手無策。”[5](P76)應(yīng)該說,費爾巴哈提出了真問題,但重建感性的任務(wù)在費爾巴哈這里還是一項“未竟的事業(yè)”。
三、理解“感性”的兩條路徑
馬克思視野中的“感性”不同于黑格爾的“感性確定性”,這種“感性確定性”是被直接給予的東西,它是無中介的,與對象自身是一種漠不相關(guān)的關(guān)系,除了對差別的無限肯定,“感性確定性”并沒有獲得更多的規(guī)定性。因此,“感性確定性”作為認(rèn)識的初級階段必將被揚棄。馬克思視野中的“感性”也不同于康德的感性直觀純形式,后者是作為認(rèn)識的先驗條件,先天的直觀形式在這里是作為現(xiàn)象的普遍有效性。
(一)作為外在感知的“感性”
對于馬克思而言,感性首先是基于外在感知的,作為外在感知的“感性”不僅是經(jīng)驗的起點,亦是邏輯的起點,它是具體的、直接的和現(xiàn)實的,思維的各種抽象必須以之為基礎(chǔ)。馬克思指出:“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產(chǎn)物;但是,決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著的、自我產(chǎn)生著的概念的產(chǎn)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產(chǎn)物。”[6](P19)對于認(rèn)識活動而言,作為外部感知的“感性”具有先在性,“任何一個對象對我的意義(它只是對那個與它相適應(yīng)的感覺說來才有意義)恰好都以我的感覺所及的程度為限。”[4](P84)這種外部感知是人通過感覺器官,包括作為感覺器官延伸物的諸種實踐手段,現(xiàn)實地與外部世界打交道的過程中獲得的,通過直觀形成感覺、知覺和表象,在這一過程中,外部的感性質(zhì)料被給予和建構(gòu)。在這里,“直觀”作為感性的能力,它是非反思性的,是經(jīng)由感官直接被給予的外部世界的映象,感覺、知覺和表象是直觀的三個層次。
馬克思的感性論并不排斥“直觀”,但這種“直觀”既不是康德式的先驗直觀,也不是費爾巴哈式的簡單直觀,而是一種現(xiàn)實的直觀能力,這種能力是社會—歷史的構(gòu)造物,現(xiàn)實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著直觀的形式和內(nèi)容。馬克思強調(diào)基于外部感知的“感性”的社會歷史性,批判各種抽象的“感性論”。首先,作為外部感知的客體,“對象如何對他來說成為他的對象,這取決于對象的性質(zhì)以及與之相適應(yīng)的本質(zhì)力量的性質(zhì)”。[4](P236)只有有音樂感的耳朵才能享受美的音樂,“囿于粗陋的實際需要的感覺,也只具有有限的意義”。[4](P237)對象能成為對象本身,是基于某種社會過程。其次,對于外部感知的主體而言,人的感覺器官以及相應(yīng)的外部感知的能力不是給定的,而是伴隨著人的自我生成的現(xiàn)實過程。“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chǎn)物”,[4](P237)“人的思維的最本質(zhì)的和最切近的基礎(chǔ),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不僅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xué)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fā)展起來”。[7](P329)在這里,作為外部感知的客體和主體不是自然客體和自然主體,而是作為一種社會過程的產(chǎn)物、一種社會產(chǎn)品被不斷生產(chǎn)出來的,這一社會過程即使“感性”成為人的自我確證,“人不僅通過思維,而且以全部感覺在對象世界中肯定自己。”[4](P236)同時,它也是創(chuàng)造與自然的本質(zhì)的豐富性相適應(yīng)的人的感覺系統(tǒng)的現(xiàn)實路徑。
(二)作為內(nèi)在體驗的“感性”
作為內(nèi)在體驗的“感性”建立在外在感知基礎(chǔ)之上,它主要關(guān)涉“情感”“需求”和“意愿”,并進一步拓展為欲望與需要、意志與創(chuàng)造力、烏托邦與想象、意識與社會心理、情感與規(guī)訓(xùn)等領(lǐng)域。馬克思關(guān)注作為內(nèi)在體驗的“感性”,并將其作為理解人的現(xiàn)實性的重要方面,指出:“人作為對象化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個受動的存在物;因為它感到自己是受動的,所以是一個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zhì)力量。”[4](P104)
在馬克思的感性觀中,對人的感性的貶抑不僅直指思辨哲學(xué)的困境,也是舊唯物主義哲學(xué)的藩籬。馬克思拒斥將人等同于物或機器,人的物質(zhì)性本身內(nèi)含著人的感性之維,人的身體組織以及與之密切相連的身體體驗現(xiàn)實地塑造著人“經(jīng)驗”世界的基本方式,也是一切理性的抽象必須朝向的領(lǐng)域,意識的出發(fā)點不是某種先驗的意向性結(jié)構(gòu),而是基于身體組織的知覺和直觀,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必須從遵從世界在我們身體中的呈現(xiàn)開始,這既是人的經(jīng)驗成果的源泉,也是建構(gòu)人的現(xiàn)實性的著眼點。人的自我生成是一個感性過程,在其中,“情感”“意志”和“需要”是持續(xù)注入的,它們直接生成人的“意義”模式,后者建構(gòu)我們行為的諸種“應(yīng)當(dāng)”。
作為內(nèi)在體驗的“感性”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常被忽視,馬克思的社會—歷史敘事中被認(rèn)為沒有“情感”“意志”和“需要”的位置,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勞動的形而上學(xué)”的責(zé)難亦源于此。在這里,對馬克思感性觀的探討關(guān)涉一個更為根本性的追問:個體的主觀經(jīng)驗是如何嵌入到社會歷史的宏觀敘事中的。總體而言,馬克思是將內(nèi)在體驗的“感性”歸之為“上層建筑”的范疇,如果說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經(jīng)濟基礎(chǔ)與上層建筑是作為一種宏觀的社會動力系統(tǒng)的話,那么,“情感”“意志”和“需要”則呈現(xiàn)了一種微觀的內(nèi)動力機制。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xiàn)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gòu)成的整個上層建筑。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zhì)條件和相應(yīng)的社會關(guān)系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和構(gòu)成這一切。”[5](P611)在這里,作為內(nèi)在體驗的“感性”不是抽象的神秘物,而是一種社會建構(gòu),“情感”“意志”和“需要”本身不應(yīng)僅僅被理解為一種自然情感,它們是有中介的,這個中介就是現(xiàn)實的物質(zhì)生活過程,離開了這個過程,“情感”“意志”和“需要”只能停留在觀念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而非現(xiàn)實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指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xiàn)實生活過程。”[5](P72)
四、從“感性”到“感性的活動”
馬克思沒有囿于對“感性”本身的探討,而是將“感性”導(dǎo)向了人的對象化活動,從而實現(xiàn)了從“感性”向“感性活動”的飛躍。這是馬克思感性觀區(qū)別于以往感性觀的重要維度,“感性”由此被賦予了存在論意義。馬克思分別探討了作為“感性活動”主體的“感性的人”、作為“感性活動”客體的“感性的世界”。
(一)“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感性活動”的主體
馬克思的“感性”是朝向現(xiàn)實世界的,“感性”的人是馬克思理論的出發(fā)點。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zhì)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5](P56)“感性”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馬克思強調(diào):“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shè)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fā),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shè)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fā)”。[5](P73)他將“從事實際活動的人”作為出發(fā)點,這是馬克思嘗試超越德國古典哲學(xué)、完成從“人間升到天國”的重要轉(zhuǎn)向。這意味著人本身不是某種思辨活動建構(gòu)起來的抽象物,也不是某種機械論意義上的自然物質(zhì),人本身不是某種被給予的定在,亦不存在某種被人的‘生物學(xué)的’本性所賦予的人性。“說人是肉體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現(xiàn)實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這就等于說,人有現(xiàn)實的、感性的對象作為自己本質(zhì)的即自己生命表現(xiàn)的對象; 或者說,人只有憑借現(xiàn)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xiàn)自己的生命”。[4](P103)換句話說,必須將人本身置于他的對象化活動中加以理解。“人不是抽象的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國家,社會”。[5](P1)“從事實際活動的人”導(dǎo)向了一種實踐場閾,是變革現(xiàn)實與人的自我生成相統(tǒng)一的辯證發(fā)展過程。
“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首先是擁有多重的感性體驗的人。馬克思強調(diào)對人的感性體驗的尊重,認(rèn)為每一種感性體驗都連接著人的現(xiàn)實性。“人的眼睛與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與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4](P236)感性體驗的匱乏是人的感性枯竭的體現(xiàn)。在馬克思的感性觀中,人的感性體驗不僅關(guān)涉?zhèn)€體性,更關(guān)涉社會性,對個體的感性體驗的漠視將帶來嚴(yán)重的社會問題,而對民眾感性體驗的尊重已被視為現(xiàn)代政治的一項基本承諾。這種尊重意味著凡個體的情感、意志、愿望所關(guān)切的,在社會秩序允許的范圍內(nèi),應(yīng)當(dāng)以某種形式被給予關(guān)注,并落實到政治實踐中。其次,“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是能動與被動的辯證統(tǒng)一。這里的“實際活動”既不是純粹的意識活動,亦不是一種單純的受動活動,而是一種“對象化的活動”。這種活動既把人的尺度加諸于外部對象之上,使客體本身成為人的“對象”,揚棄了客體的給定性和自在性,同時,也是對人自身的純粹主觀性的“揚棄”,這源于“他的欲望的對象是作為不依賴于他的對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4](P103)“物質(zhì)生產(chǎn)實踐”是最基本的,它是人的感性的類生活,是“感性的現(xiàn)實”與“現(xiàn)實的感性”辯證統(tǒng)一的基礎(chǔ),也是生成人的感性豐富性的現(xiàn)實道路。
(二)“感性世界”:“感性活動”的客體
在馬克思的感性觀中,作為“感性活動”對象的外部世界具有客觀實在性,同時,它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chǎn)物。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的直觀主義的自然觀時,指出:“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決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直接存在的、始終如一的東西,而是工業(yè)和社會狀況的產(chǎn)物,是歷史的產(chǎn)物,是世世代代活動的結(jié)果”。[5](P76)
“感性世界”首先關(guān)涉外部自然,這個自然具有先在性,是人類感性活動的前提和條件。一方面,“感性的外部世界”作為“勞動的生活資料”,即勞動對象;另一方面,它是作為維持肉體生存的手段,即直接意義上的“生活資料”。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xù)不斷地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4](P52)人類的感性活動不斷把“自在的自然”轉(zhuǎn)化為“人化的自然”,“人化的自然”既體現(xiàn)自然的人性,又是人的自然性的彰顯。“工業(yè)的歷史是一本打開的工業(yè)的歷史和工業(yè)的已經(jīng)產(chǎn)生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xué)。”[4](P85)
其次,“感性世界”關(guān)涉人的社會關(guān)系體系。在馬克思的視野中,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人與人的關(guān)系是互為中介的,只有在人與人結(jié)成一定的社會聯(lián)系的范圍內(nèi),才有他們對于自然的關(guān)系。因此,人與人之間的狹隘關(guān)系制約著人與自然的狹隘關(guān)系,反過來亦如此。在這個意義上,“首先應(yīng)當(dāng)避免重新把‘社會’當(dāng)做抽象的東西同個體對立起來。個體是社會存在物。”“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礎(chǔ),才是人的現(xiàn)實的生活要素”。[4](P233、79)對現(xiàn)實的人來說,社會關(guān)系體系是有階級性的,這種階級性源于他們自己所不能決定的、自身在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所處的地位的差異性,階級是塑造人的感性的重要的社會因素,不同的階級身份往往伴隨著不同的“感性意識”。“富有的人同時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現(xiàn)的完整性的人,在這樣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實現(xiàn)作為內(nèi)在的必然性,作為需要而存在”。與此相反,“貧困是被動的紐帶,它使人感覺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財富是他人”。[4](P240)
最后,“感性世界”關(guān)涉人自身,人并不是站在感性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而是現(xiàn)實地處于感性世界之中。因此,人的感性活動本身也就感性世界的活動。對自身的反觀指向了人的自我確證問題,人何以自我確證?馬克思認(rèn)為,人只有在對象化的活動中才能實現(xiàn)這種確證。“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xiàn)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chuàng)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4](P54)這里,“一切對象對他來說也就成為他自身的對象化,成為確證和實現(xiàn)他的個性的對象,成為他的對象,這就是說,對象成為他自身”。[4](P236)
五、資本:“感性活動”的一種具體歷史性
資本文明生成了“感性活動”的一種具體歷史性,在其中,貨幣是作為私有財產(chǎn)外化的感性形式。“在不論對材料的性質(zhì)即私有財產(chǎn)的特殊物質(zhì)還是對私有者的個性都完全無關(guān)緊要的貨幣中,表現(xiàn)出異化的物對人的全面統(tǒng)治。過去表現(xiàn)為個人對個人的統(tǒng)治的東西,現(xiàn)在則是物對個人、產(chǎn)品對生產(chǎn)者的普遍統(tǒng)治。”[8](P29-30)貨幣建構(gòu)了一種普遍物化的力量,它使一切物的有用性都體現(xiàn)在可交換性上。“凡是我作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個人的一切本質(zhì)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憑借貨幣都能做到。”[4](P296)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活動構(gòu)成了資本文明下人的感性活動的主要方面,貨幣亦成為感性活動得以實現(xiàn)的普遍手段。“貨幣是需要和對象之間、人的生活和生活資料的牽線人”。[4](P292-293)它既是真正的創(chuàng)造力,同時,也是一種顛倒的力量。“貨幣拜物教”是資本邏輯的必然產(chǎn)物,貨幣帶來了普遍的交換關(guān)系和“個性的普遍顛倒”。[4](P297)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對象化活動變成了一種異己的、敵對的力量。
馬克思區(qū)分了“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識”與“希臘人的感性意識”,[4](P125)指出在希臘人的感性意識中,感覺直接導(dǎo)向精神生產(chǎn)的豐富性,它是由希臘人在自由自覺的勞動中創(chuàng)造的;而在“拜物教徒感性意識”中,“人本身被認(rèn)為是私有財產(chǎn)的本質(zhì)”。[4](P71)這個過程是對人本身的否定,在其中,“感覺”和“精神”是對立的。資本邏輯下的“需要”,即作為人的內(nèi)在體驗的感性,被抽象化為貪財欲,滿足這種需要的方式就是不斷的占有。“一切肉體的和精神的感覺都被這一切感覺的單純異化即擁有的感覺所代替”。[4](P82)通過物的占有來確證自身的存在,這種貪財欲遮蔽了人的感性的豐富性。馬克思指出:“正像人的本質(zhì)規(guī)定和活動是多種多樣的一樣,人的現(xiàn)實也是多種多樣的。”[4](P82)人的感性活動被等同于“感性的占有”,而“感性的占有”被等同于“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人的本質(zhì)規(guī)定和活動必然是單向度的。于是,一方面是“需要的精致化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是“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蠻化和徹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簡單化”,“相反意義的自身”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被生產(chǎn)出來。[4](P250)作為“感性活動”載體的“語言”本身也被資本邏輯所宰制,馬克思指出:“我們彼此進行交談時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語言,是我們的彼此發(fā)生關(guān)系的物品。我們不懂得人的語言了,而且它已經(jīng)無效了”。 “物的價值的異化語言”成為“自信的和自我認(rèn)可的人類尊嚴(yán)的東西”。[8](P36)
雇傭工人是這種普遍物化最直接的受害者,馬克思探討了異化勞動下工人生存的感性體驗,這種探討既關(guān)涉作為外部感知的感性,也關(guān)涉作為內(nèi)在體驗的感性。馬克思指出:“他(雇傭工人——引者注)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fā)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4](P50)勞動在這里不是人的主體性的現(xiàn)實生成與呈現(xiàn),恰恰相反,“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4](P50)工人的勞動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外在的勞動”,這種勞動體驗是非自愿的“自我犧牲”和“自我折磨”,勞動過程本身是主體性喪失的過程,是感性活動的豐富性被剝奪的過程,這個過程使勞動成為“他者”,勞動產(chǎn)品成為異己物,在這里,“生活本身僅僅表現(xiàn)為生活的手段”。[4](P205)工人日益成為自己對象的奴隸,“這種奴隸狀態(tài)的頂點就是:他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作為肉體的主體的生存,并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4](P49)“普遍的貧困”成為他的“現(xiàn)實”,工人在資本邏輯的物化力量中不僅成為物質(zhì)的貧困者,同時亦是精神的貧困者,這種“貧困”廣泛滲透于雇傭工人的諸種生活鏡像中,“人不僅沒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連動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4](P251)以人的居住活動為例,馬克思指出:“窮人的地下室住所卻是敵對的、‘具有異己力量的住所,只有當(dāng)他把自己的血汗獻給它時才讓他居住’”。[4](P261)對于雇傭工人而言,它從來都不是“家園”,而是資本化的空間,“倫敦的地下室住所給房產(chǎn)主帶來的收入比宮殿帶來的更多”。[4](P255)它是一個隨時可能被趕走的容身之所,從工廠到居住都成為被資本規(guī)訓(xùn)的空間。在這個意義上,雇傭工人的解放之路意味著對感性的拯救,當(dāng)代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關(guān)于“建立新感性”的探討正是沿著馬克思感性觀的致思路徑。馬爾庫塞指出:“鑒于發(fā)達的資本主義所實行的社會控制已達到空前的程度,即這種控制已深入到實存的本能層面和心理層面,所以,發(fā)展激進的,非順從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義。同時,反抗和造反也必須于這個層面展開和進行。”[9](P134)不難看出,馬爾庫塞在對資本的批判中凸顯了感性的向度,強調(diào)恢復(fù)愛欲、直覺、激情、本能等感性之維,所不同的是,在馬克思的視野中,并不存在感性的解放與宏觀革命之間的斷裂,二者是辯證統(tǒng)一的。
馬克思將共產(chǎn)主義作為真正意義上的“感性”的解放,共產(chǎn)主義揚棄了異化勞動。“對私有財產(chǎn)的揚棄,是人的一切感覺和特性的徹底解放;但這種揚棄之所以是這種解放,正是因為這些感覺和特性無論在主體上還是在客體上都成為人的。”[4](P235)共產(chǎn)主義將創(chuàng)造具有豐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覺的人作為這個社會的恒久現(xiàn)實。“人以一種全面的方式,就是說,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zhì)。”[4](P234)人的感性的豐富性得以彰顯,在其中,人的對象化就是人的現(xiàn)實化,勞動本身成為一種積極的自我生產(chǎn),體現(xiàn)著人能動的類本質(zhì)和類生活,是人作為自然存在物和社會存在物的統(tǒng)一。“共產(chǎn)主義是私有財產(chǎn)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并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zhì)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fù)歸,這種復(fù)歸是完全的復(fù)歸,是自覺實現(xiàn)并在以往發(fā)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nèi)實現(xiàn)的復(fù)歸。”[4](P230-231)共產(chǎn)主義是感性世界的全面復(fù)歸,是完成了的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統(tǒng)一,“是存在與本質(zhì)、對象化與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4](P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