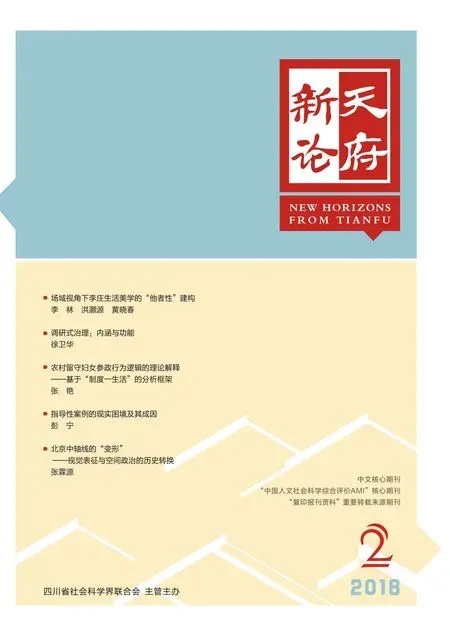資本主義與民主共存的幻象
——讀列寧的《國家與革命》
任 遠 宋朝龍
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寫作于十月革命前夕,是一部系統闡發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論述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要著作。該著作主要針對的是當時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的修正。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們認為革命暴力時期已經過去了,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以革命為中心的國家理論已經過時,現階段可以通過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制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而列寧結合當時的俄國國情,分析了資本主義民主并沒有改變國家剝削的性質,闡發了無產階級仍然需要不斷革命的理論。但是,在當代,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日益發展,似乎列寧所闡述的資本主義民主“殘缺不全、貧乏和虛偽”*列寧曾指出“資本主義社會里的民主是一種殘缺不全的、貧乏的和虛偽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數人享受的民主”。具體內容詳見列寧:《國家與革命》,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5頁。的特征非但沒有暴露,資本主義社會反而因制度的逐漸完善而自詡為了“平等與自由”的代名詞,并日漸成為當前政治體制的一種共識。這是否意味著列寧對資本主義民主虛偽性的揭示只是歷史的產物呢?或者說,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當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不平等與政治上民主并存的現象呢?
一、經濟剝削與政治民主并存的剖析
資本主義民主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興起而日漸確立起來的。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初期,資本主義民主雖然在反對封建專制制度方面起到了思想啟蒙與政治解放的作用,但其缺陷與局限性已經在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那里遭到了批判。
從資產階級革命到19世紀中后期,資產階級與舊的貴族地主階級圍繞國家政權的斗爭一直處于膠著狀態。資產階級一方面想通過擴大公民的選舉權來增強資產階級代議制民主制的社會基礎;另一方面,又害怕擴大公民的選舉權成為無產階級激進民主的工具,動搖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這種矛盾的心理決定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此時呈現出與舊勢力相妥協,與新力量相斗爭的特點。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基于對資產階級的不信任,對代議制民主展開批判,尖銳地指出:“資產階級口頭上標榜是民主階級,而實際上并沒想成為民主階級,它承認原則的正確性,但是從來不在實踐中實現這種原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89頁。具體體現在:
首先,資產階級通過對選舉權設置嚴格的資產限制來排除廣大無產階級的參與。在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初期,資產階級對選舉權設置了諸如年齡、財產、身份、種族等限制,雖然聲稱公民具有普選的權利,但實際上,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公民在總人口中卻并非多數。因為,“工業革命創造了一個大工業資本家的階級,但是也創造了一個人數遠遠超過前者的產業工人的階級”*《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6頁。,實現普選本身,就意味著占人口總數的工人階級會進入權力中心。馬克思在其著作《憲章派》與《普魯士狀況》中都揭示了這一點:資產階級通過制定市民的財產收入、納稅數目等規定,不僅將大多數人民排除在普選之外,還使其余享有特權的一部分人遭到官僚集團最肆無忌憚的擺布。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在按照財產狀況劃分階級的雅典和羅馬,就已經是這樣。在中世紀的封建國家中,也是這樣,在這里,政治的權力地位是按照地產來排列的。這也表現在現代的代議制的國家的選舉資格上面。”*《馬克思恩格斯恩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96頁。在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初期,對選民資格的限制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選舉制度對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利益的維護。不過,對選舉資格的限制也可以被看作資產階級向封建勢力示好的表現。在一些封建勢力較為薄弱的國家,資產階級為謀求自身發展,往往并不謀求動搖封建勢力的根基,而是以犧牲普選權的普遍性來謀求封建專制對自身價值的認同。比如在普魯士,資產階級試圖通過憲章規定人們的個人自由、財產不容侵犯、教育的權利。在馬克思看來,這也是一種專制獨裁的代表。馬克思認為,德國資產階級由于自身階級的軟弱性,并沒有能夠提供憲法法律所規定的現實基礎,只能是在專制獨裁的法律體制下被恩準,規定的“普魯士人的權利變成了一紙空文”*《馬克思恩格斯恩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60頁。,欽定的憲法將資產階級革命淵源的所有痕跡都連根鏟除了。
其次,資產階級在利用普選權與無產階級共同對抗君權獨裁時,卻背叛了革命同盟。馬克思在《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斗爭》《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等著作中,對資產階級普選制的不徹底性進行了深刻揭露。1848年法國的普選帶來的不是政治和社會的進步,而是歷史的倒退。法國的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站在同一戰線共同對抗金融貴族勢力,可是由直接普選產生的國民議會并沒有實現它建立的初衷。因為革命之后,聯盟共同的敵人——金融貴族——的勢力非但沒有削弱,反而是鞏固加強了。與此同時,當選舉制正成為無產階級民主訴求的工具時,資產階級就選擇了廢除普選權。因為資產階級害怕進一步的民主訴求和社會革命會造成對自身財富、地位權力的威脅,因此,他們被革命的群體推上了權力頂峰,卻變成了舊制度的支持者,資產階級中最富有的成員傾向于與反革命勢力同流合污。1848年革命不是舊制度同聯合的進步力量之間的對抗,而是維護秩序和社會革命之間的對抗。
可見,早期資產階級民主的局限性在于用代議制民主的方式制造成了一場“民主騙局”。這不是因為它采取了民主的方式,而是它運用了民主機制方式阻礙底層人民參與國家統治的可能性。早期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實際上是以普選權斗爭作為謀求自身發展的敲門磚,資產階級并不可能在發展初期就會讓無產階級同自身一起參與到國家治理中。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上創造和保持人民做主的幻象,實際上卻在破壞和限制人民施加影響。在19世紀末,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面代替了封建生產方式以及資本主義制度逐步確立和完善,資產階級為維護政權的穩定,逐漸放寬了選舉范圍與選舉資格的設定,開始允許工人階級政黨參與議會選舉,這就給第二國際寄希望于社會改良與和平過渡繪制了一個可預期的未來。但正如列寧所說:“民主共和制是資本主義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殼,所以資本一掌握這個最好的外殼,就能十分鞏固十分可靠地確立自己的權力,以致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中,無論人員、無論機構、無論政黨的任何更換,都不會使這個權力動搖。”*列寧:《國家與革命》,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頁。代議制民主的擴大,實際上反映了只有當時形勢同資本積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資本主義對國家政策形成和決策產生了廣泛影響的基本要求相一致,資本主義統治階級才愿意支持將選舉權擴大至多數成年人。
資本主義社會與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區別,在于政治權力本身不再是來自于政治體制本身,而是與其經濟生產方式緊緊聯系起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王朝掌握著對社會統治的絕對權力,政治權力來自政權本身。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是將政治權力與生產方式聯系起來。馬克思對這一發展的政治意義有明確的說明:“亞洲和埃及的國王或伊特露里亞的神權政治的首領等等的這種權力,在現代社會已經轉到資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單個資本家,還是股份公司那樣的結合資本家。”*④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7-388頁,第658-659頁,第662頁。政治權力與生產方式之所以能夠聯系起來,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商品交換的經濟機制實現了對一切社會勞動和資源的配置。所有權“取得了純粹經濟的形式,因為它擺脫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會的裝飾物和混雜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7頁。。
因此,資產階級對于剩余勞動的占有,實際上是通過使生產者與勞動條件完全分離,自己把生產資料作為自身的絕對私有財產來實現的。這種對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私人占有,就構成了對生產者的強迫,迫使生產者為了與生產資料結合而將對勞動的支配權交給資本家。“他(工人)進入過程以前,他自己的勞動就同他相異化而為資本家所占有,并入資本中了……工人本身不斷地把客觀財富當做資本,當做同他相異己的、統治他和剝削他的權力來生產,而資本家同樣不斷地把勞動力當做主觀的、同它本身對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實現的資料相分離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體中的財富源泉來生產。”④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占有和剝削剩余的權力并不直接依賴于法律或政治上的依附關系,而是以自由生產者與絕對的生產資料私有財產占有者之間的契約關系為基礎,“雇傭工人獨立性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經常更換以及契約的法律擬制來保持的。”⑤資產階級標榜資本與勞動在市場上是平等交換,但事實上,絕對的私有財產決定了生產者和占有者之間的契約關系是需要政治職能維護的。資本家將對生產的直接支配權轉移到國家手中,就是政治權力。在這個意義上,政治領域的權力關系實際上是占有者和生產者關系的從屬。勞動者之所以服從資本主義生產安排,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由于政治權威的逼迫,而是“市場經濟規律的獨立和資本行使權力的抽象性”*艾倫·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對資本主義》,呂薇洲、劉海霞、邢文增譯,重慶出版社,2007年,第41頁。。
這樣,在現代資本主義民主中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社會經濟的不平等和剝削與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共存。質言之,政治民主可以賦予參與政治的公民以平等的選舉權,而且政治參與的平等并不會直接影響到經濟領域中的不平等。民主被限定在政治領域中,反而從形式上遮蓋了經濟領域生產關系的不民主性。正如馬克思所說,“選舉的性質并不取決于這個名稱,而是取決于經濟基礎,取決于選民之間的經濟聯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9頁。生產方式本身不僅是一種技術方式與組織方式,生產方式中的剝削方式是一種權力關系,政治領域中對立的階級組織方式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者與占有者的關系。從直接生產者榨取的沒有付報酬的剩余勞動這種特定的經濟形式所決定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階級關系,與資本主義所宣稱的政治平等并行不悖。因此,無產階級通過爭取政治參與的權利是無法徹底實現自身的民主化的。“資本主義民主的自由純粹是一種形式,不平等從根本上削弱了自由,并且使大多數公民的自由僅僅是名義上的。資本才是起統治作用的。”*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燕繼榮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126頁。
資本對于勞動的統治地位,使得勞動者與勞動過程、勞動產品相分離,意味著勞動者本身只是獲得了形式上的規定,資本使得所有具體的使用價值都抽象成了交換價值。資本主義民主所承諾的普選權之所以能夠打破封建社會下人們對于等級身份的認同,就在于“在等級范圍內,個人的享受,個人的物質交換,取決于個人所從屬的一定的分工”。個體的享受以及對自己勞動產品的占用,在等級社會的表現是只有特權人物才能進行商品的交換,而“在階級的范圍內,則只取決于個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換手段……個人作為一般交換手段的所有者,進入同社會為萬物的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東西的交換”,在“貨幣制度充分發達的社會中,由此事實上造成了個人實際上的資產階級平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162頁。如果僅僅停留在交換本身,訴求普選的價值意義就在于取消更多的流通限制,來實現“個人自由最高實際的確認”,這正是“政治經濟學家……把這種(工人對資本家)的從屬關系描繪成買者與賣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1頁。的表現。簡言之,資本主義社會中表面的經濟平等實際上掩蓋了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社會關系,而資本主義的虛偽性正是表現在它通過不斷的社會再生產,使得人們更容易接受表面所呈現出的經濟平等與政治民主。
列寧正是基于認識資本主義形式上的民主一定要聯系其剝削的本質,才提出,民主所意味著的平等,是基于社會全體成員在占有生產資料方面的平等而言的。只有在社會生產資料歸全體社會成員共同所有的條件下,生產關系才不再是人與人壓迫剝削的關系,這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的經濟結構與社會關系前提。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有可能“從形式上的平等到事實上的平等,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列寧:《國家與革命》,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4頁。。
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意識形態化
在當代,人們對民主的關注往往更多地側重于政治形式的比較,而忽略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關系的不平等。這本身就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輸出。
馬克思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時就曾指出,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將一切都商品化,人們直接所面對的是由市場競爭的交換系統生產和建構出來的流通與分配的中介性過程,這個中介是以貨幣、資本為基礎的工具,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在追求價值的實現中發生了顛倒,本來是生產之外的東西,卻成了主導人與人關系的存在。這就是資產階級貨幣拜物教意識形態。“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社會歷史存在直接設定成經濟運行本身的自然的客觀屬性,所以,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相對于人類生存的本質顛倒,直接被指認為人的天然本性(自然法)和社會存在(生產)運作天經地義的正常形式。”*③張一兵:《回到馬克思》,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9頁,第572頁。馬克思意識到,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所創造出來的現代社會經濟生活中,一切過去的簡單社會存在的規定性在這里都具有了復雜的關系和表現形式,不再有簡單存在的人,只有為追求價值實現的各種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中介了的人。在經濟生活中,人與人之間通過市場交換形成的以貨幣資本為中介的經濟關系,在政治關系上的反映就是選票。
資產階級所宣揚的政治平等的理念賦予了選票“魔化”的力量,讓人們以為,只有爭取到普選的權利,才能表達自己的訴求。正如馬克思所說的,“貨幣是一切價值的代表,在實踐中情況卻顛倒過來,一切實在的產品和勞動竟成為貨幣的代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4-95頁。,這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顛倒與異化。選票原本是人們表達自己對于政策的意見的一種工具和手段,但在資產階級所建構的間接民主的規則下,選票成了人與人政治關系中的一種支配性東西,成了政治運作中真實的統治性權力因素。在當代社會,同貨幣產生利息、資本獲得利潤所形成的對于貨幣資本的拜物教意識一樣,選票代表著公民平等身份的意識,不知不知覺地成為人們無法批判性透視的無孔不入的常識。“整個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就建立在這個涂滿迷幻色彩的神話之上。”③資本決定了選票成為人與人政治關系的物化載體,而選票背后所代表著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又通過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方式成為人們的常識,并且讓人們接受現有秩序下所標榜的民主。
如果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剝削關系是整個社會結構的基礎,那么,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就是使這個社會結構不斷穩固的動力。在資本主義社會,政治上的民主平等掩蓋了經濟上的不平等,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則通過生產關系的再生產使被統治階級甘愿接受這種狀態。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不僅生產商品和剩余價值,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不僅僅再生產出資本家和工人,而且再生產出適應資本主義原則與制度的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了在計件工資制下,負責工人的工頭按照資本家制定的合同規定來招募工人并支付其工資。本來,工人應該團結在一起反對資本的剝削,而在這種情況下,沒有直接出面的資本對工人的剝削是“通過工人對工人的剝削來實現的,人們往往人為地助長這種自然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7頁。
馬克思從經濟領域闡釋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對于工人階級的分化。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爾都塞則將這種生產關系再生產對無產階級的影響解釋為意識形態的國家理論。該理論指出,作為統治階級的國家政權不僅具有鎮壓功能,而且還能進行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再生產,使生產者更加服從現存的社會秩序。維護生產關系再生產成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說,意識形態并不是停留在思想文化的教化之中,而是通過以物質實體為載體,使這種思想文化中的想象性關系成為人們自以為認識到的意識。有意識的主體采取某些實踐活動,實質是參與了特定意識形態機器的某些常規姿態。比如一個人信仰宗教,他就會自發地做宗教的某些行動,完全順從于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在不知不覺中使自己成為意識形態機器中的一部分,喪失了主見。
議會民主制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來使人們認為政治可以通過自由表達的方式來形成共識。這種平等參與的民主原則也向經濟領域滲透。不平等的私人決定權的經濟原則可以通過組織工會與資產階級達成協調,以合作主義的制度安排將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表與選民政策的訴求結合起來。這種社會化的制度形成正是通過教育機器、信息機器、宗教機器、家庭機器等形成集體共識。
教育機器側重于現存社會中勞動力技能的培訓。根據社會分工要求,通過一系列社會教育機構來培訓人們,使社會成員成為在階級社會與意識形態相適應的社會角色。生產者在培訓中需要根據所從事的工作服從對應的制度規范。而服從社會技術分工的規范實際上就是服從統治階級建立起來的秩序規范,也就使勞動者認同這種生產關系。信息機器通過各種傳媒媒介工具來宣揚自由民主的價值內涵,強調個人在經濟市場的私有權與平等的參與市場行為,就是對這種價值觀的踐行;宗教機器通過設立教堂,舉辦各種儀式來宣講資產階級博愛意識;家庭機器通過社區互助行為,讓其認可道德政治文化價值觀。在現代社會,教育、信息傳播、宗教、家庭都成了意識形態輸出的物質載體,被用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正如阿爾都塞所指出的,“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要求再生產出勞動力的技能,同時還要求再生產出勞動力對現存秩序的各種規范的服從,即,一方面為工人們再生產出對于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服從,另一方面,為從事剝削和鎮壓的當事人再生產出正確運用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能力,以便他們也能‘用詞句’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做準備。”*路易·阿爾都塞:《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陳越編,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5頁。
因此,在政治關系中,爭取民主選舉的行為就是資產階級輸出意識形態的行動實踐。資產階級通過宣揚普選權所代表的公民身份平等與政治自由的含義,來引導社會群眾形成某種意識,認為只有參與到普選權的政治行動中,才是自由的表現。這就使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滲透到人們的具體物質實踐中。因而,當工人階級開始組建政黨參與議會斗爭時,實際上已經是在扮演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規定的物質儀式。據此,也就不難理解德國社會民主黨派的修正主義的錯誤。一旦僅停留在試圖通過議會斗爭和平過渡的方式,就只能淪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代表者。不能從生產領域進行變革,政治領域所表現出的民主依然是虛假的。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列寧不放棄革命,強調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去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具有深刻意義。因為,不改變資產階級現存的國家權力機構,我們很容易淪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踐行者,而失去批判現實的維度。何萍就指出,列寧闡發的革命與民主的關系,不僅說明了統治階級如何運用國家的權力機構來實現自己的意志和目的,而且還說明了無產階級在面對國家權力機構,運用革命的方式來使自己從原有權力關系中解放出來,改變自己的地位,“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制度僅僅發展經濟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改變舊的社會權力結構。”*何萍:《列寧國家理論的研究范式:重讀〈國家與革命〉》,《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
三、列寧《國家與革命》的現實意義
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國家體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福特制經濟到后福特制的彈性經濟的轉變,相應的國家制度、機構、職能也在發生顯著變化。第一,民主制度多元化發展。二戰之后,西方國家在總結法西斯主義的教訓之后,不同程度的對民主制度進行了改革,不僅擴大了公民的自由民主權利,而且還給予了人民享有社會、經濟和文化方面的權利,允許民眾形成各種利益集團來廣泛參與政治過程,改變了傳統代議制民主的政治形式。第二,國家管理職能增強。現代國家所扮演的角色不再是早期資本主義時期資產階級鎮壓剝削無產階級的暴力機器,而是更多地承擔了調節經濟發展的角色。尤其是二戰以后,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凱恩斯主義在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盛行,國家通過制定產業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手段來調節經濟的發展,促進就業,提供經濟運行所需要的法律秩序,穩定社會政治環境,等等。
正是資本主義的這些當代變化,就使得列寧所揭露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假幻象,訴諸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政治理想,在當前社會話語中被有些人認為可能存在著不合時宜的解讀。尤其是傳統的工人階級群體的階級意識逐漸消失。我們應該承認,二戰以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繁榮,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工業和階級的沖突模式。如果說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所生活的時代是社會資源整體處于單向度的向資產階級流動的狀態,那么,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就是整體社會福利水平上升,以經濟為導向、以分配為中心的多元社會。在二戰后一段時期內,工人可以通過工會爭取自身福利、提高工資待遇,資本主義國家還一度加大在個人和家庭的收入、醫療保健、住房、教育培訓以及個人照顧服務方面的舉措,力圖通過各種社會福利政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工人階級內部出現分化,形成了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分,管理人員與被管理人員之分,并隨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工人階級逐步成為具有較高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工程技術人員,涌現出了大量的中間階層,他們不再以傳統的爭取經濟利益為基本訴求,而是以后現代的物質主義價值觀為基礎,尋求個性解放與認同。之前作為社會矛盾焦點被主要集中關注的勞工問題,轉變為了文化和倫理等方面的問題,尤其是涉及生活方式的基本問題,出現了一系列的反核運動、綠色和平運動,女權運動、同性戀權利維護運動、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等,各種主題的抗議運動層出不窮。工人階級作為社會建構的單一主體的中心地位,已經逐漸分散在中間階層所倡導的“新社會運動”中。高茲*參考吳寧:《工人階級的終結——兼析高資的〈告別工人階級〉》,《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0年第4期。甚至指出,無產階級不再是實現社會主義的中堅力量,現在更多地是以性別、種族、年齡和居住區為基礎的集團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斗爭中起決定性作用。
在當代條件下,再提無產階級專政,似乎已經沒有傳統的階級群體作為實質載體了。因此,有不少人認為,列寧的暴力革命或者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過時了。但他們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民主通過競爭性政黨的方式來吸引大量選民,就會形成以政治市場為導向的特征。資本主義民主制下的競爭性政黨紛紛掩蓋內部分裂、派系活動等對抗性特征來迎合選民需求,使得這些群體以為自己選出的執政政黨能夠體現自己的訴求。但事實上,群體訴諸問題的分散性與排他性,本質上是無法通過國家權力得到根本處理的,因為“后物質主義”價值無法為全部問題提供指導,一個政黨不可能用女權主義原則去處理稅收關系。這就說明,在當前,個人政治訴求表達的自由雖然能夠在資本主義民主體制下得到呈現,但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政治權力的分配方法,更不可能改變它由以產生的資本邏輯和社會經濟權力模式。另外,以身份認同為特征的各種新社會運動,雖然主題各異,但都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壓迫,他們激進運動的訴求是希望自下而上地影響某些社會政策,可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會促使人們希望得到并不局限于某些特性的認可,擺脫社會性建構的標簽,來被承認為完整的人。來自資本與勞動關系下的階級維度,就能夠使不同抗爭群體聯合起來。正如奧菲所說,“民主會戳穿資本主義。建立民主國家必須代表人民,所以民主國家就要迫使企業家按照不利于自己生存的原則行事——工人階級,作為絕大多數非資本家的代言人,會加強整個經濟領域中的政治首要性,當然,在政治領域中的情況也是一樣。”*克勞斯·奧菲:《福利國家的矛盾》,郭忠華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0頁。
從這個意義上說,堅持列寧關于無產階級的任務以及不斷革命的理論,需要我們在新的歷史時期下結合社會結構的變化,重新挖掘無產階級對資本權力的批判性,從而揭穿資本主義民主的幻象,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