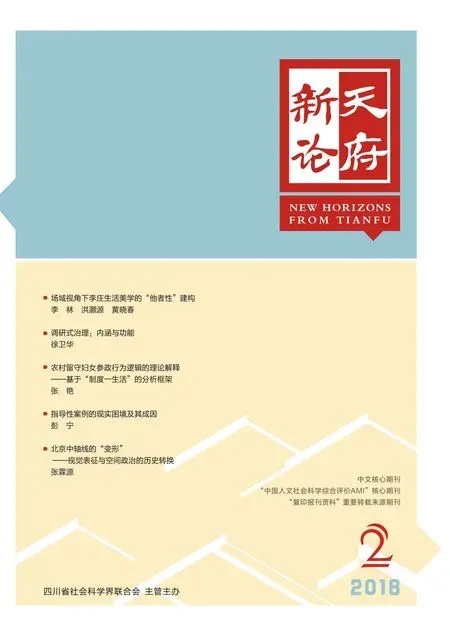北京中軸線的“變形”
——視覺表征與空間政治的歷史轉換
張霖源
在景山萬壽亭的石板地面上,嵌有標識北京城市中心點以及中軸線走向的圓形銘牌。依其所示,往南可俯望屋檐重重的紫禁城,往北則可遠眺鐘鼓樓……作為中軸線上的地理制高點,景山無疑是縱觀中軸線的絕佳位置。不過,明清時期的景山因其皇家御苑身份,并不具有理想視點的自明性,而觀覽中軸線的視覺意志也是到晚近的時候才成了一種廣泛且可行的訴求,這與當下的情況已是十分的不同。
在有關中軸線的研究中,尤以侯仁之的《試論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中的三個里程碑》一文為代表,里面不僅勾勒出了新中國成立之后中軸線的兩次大“變形”——天安門廣場的興建和中軸線的向北延伸,也從不同時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出發闡釋了中軸線變形的歷史意義。在此基礎上,本文則試圖從兩次變形切入,分析其中所涉及的視覺表征和空間政治的轉換,以揭示中軸線被升華為奇觀的意識形態癥候。需要強調的是,奇觀(spectacles),不應僅僅從表象的層面上來理解,據情景主義國際的創始人居伊·德波的觀點,“它是已經物化了的世界觀”*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頁。。雖然德波將奇觀視作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癥候加以批判,但事實上,這一批判所觸及的問題早已超過了社會形態的界限,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分析方法。在本文中,借由奇觀所要考察的是,不同歷史時期對中軸線的可見性建構以及其中交織的權力關系。
一、神圣的空間:《南巡圖》中的權力展示
今天,當人們登臨景山縱目游觀時,眼前所見的這條綿延無際的中軸線,已遠非明清時期的形貌了。據相關資料記載,中軸線先后歷經了元、明、清三代的不斷修整才得以定型:南起永定門北抵鐘樓,中間依次分布著天橋、正陽門(前門)、承天門(天安門)、紫禁城、景山、地安門等重要建筑單元。雖然許多研究者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語境,已對這一空間布局的意義進行了較為詳實的闡釋;但除了將中軸線視作文化觀念的一種顯現之外,它如何參與到明清時期的權力表征也同樣值得關注。
明清時期,由于缺乏現代媒介機器,中軸線的影像化似乎是難以想象的。然而,繪于1691年的《康熙南巡圖》和1764年的《乾隆南巡圖》,卻留存了有關中軸線在“原初”場域中運作的視覺“證據”。這兩幅出自清代畫院的長卷,是當時宮廷盛行的表征風格——敘事性繪畫——的典范。前者長15~26米,由王翚、楊晉等多位畫家耗時3年完成;后者長約154米,由畫家徐楊執筆,共耗時6年之久(絹本完成之后乾隆又命徐楊另作紙本)。作為對歷史的一種記錄,兩幅堪稱鴻篇巨制的南巡圖分別呈現的是清代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南巡事件。*《康熙南巡圖》描繪的是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的情景,《乾隆南巡圖》描繪的是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的情景(另有觀點認為此畫涉及乾隆的多次南巡)。其中,兩位皇帝對畫稿的直接審查更是確保了表征的權威性和神圣性,這不僅涉及自身形象的建構,在敘事性畫面展開中出現的不同場景也都被置于圖像的意義系統中。
雖然《乾隆南巡圖》各卷表現的內容是依據乾隆的御制詩而作,并非如《康熙南巡圖》一樣依據的是南巡的具體行程,*《康熙南巡圖》各卷中均題寫有一段文字,用于詳細交代時間、地點和相應事件。但從形制上不難看出《乾隆南巡圖》對《康熙南巡圖》的借鑒和模仿,如長卷形制、十二卷的構成、裝裱樣式等。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兩幅南巡圖都共享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敘事鏈條,即出發與返回。其中,出現于首卷和末卷的中軸線就標識了這一敘事的起始及尾聲。在《康熙南巡圖》中,首卷畫面起始于永定門,描繪的是康熙一行人出城時的情景:送行的文武官員站在護城河岸邊,路旁儀仗整齊鮮明,一直排列到南苑行宮門口。末卷則描繪了南巡結束返回京城時的情景:康熙一行人正沿中軸線穿過正陽門、大清門朝紫禁城緩緩行徑,此時,端門的五個城門已打開,嚴整的儀仗一直延伸至太和殿。在《乾隆南巡圖》中,首卷“啟蹕京師”由正陽門開始,描繪了乾隆一行人從正陽門的城樓和箭樓穿出,過護城河之后沿西河沿大街行進,前往位于良鄉的皇家行宮。末卷“回鑾紫禁城”描繪的是乾隆一行人結束南巡返回京城時的情景:道路路旁儀仗排列整齊,規模宏大,從護城河河岸一直排到宮門口,南巡隊伍則浩浩蕩蕩地沿著中軸線穿過午門進入紫禁城城內。
關于這兩幅南巡圖,國內外的研究者們已經強調了長卷對視覺的引導。如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的負責人也是中國藝術的重要研究者何慕文(Maxwell K. Hearn)指出,王翚繪制《康熙南巡圖》時采用了漢代畫像傳統,即長卷在從右至左的展開中,觀者的視線會隨之移動。*Maxwell K. Hearn, The Kangxi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 A Narrative Program by Wang Hui,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0, p.211.事實上,這兩幅圖中的中軸線有著與之匹配卻又更加復雜的視覺功能。盡管中軸線在兩幅南巡圖中并非表征中心,但它的在場,作為一種空間性的配置,卻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一定程度上來看,它們構成了某種癥候——通過圖像表征反思中軸線在特定歷史場域下的作用方式。
首先, 區別于今天中軸線慣常的南北縱深形象,這兩幅南巡圖中的中軸線以水平的形態呈現,從而強化了長卷的視覺移動機制和敘事展開方式;其次,與其他各卷所描繪的地理空間相較,中軸線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成為了展示皇家威儀與國家權力的理想場所。因此,在首尾圖卷中,畫家借由中軸線筆直開闊的御道事無巨細地鋪陳了皇家的鹵簿禮制,甚至還以人與物的形體組織起祝語,如《康熙南巡圖》卷末的“天子萬年”。在這種連續性中,中軸線不僅以重疊出現的方式標識了敘事的完整合一,更標識了一種純粹的展示性。但這種展示性并非指向中軸線自身,而是通過有限與無限的辯證交織,使中軸線在可見性中成為展示權力的神圣空間。
一方面,圖中的中軸線是實體性的,永定門為其最南端,向北依次經過正陽門、天安門、端門和午門等重要建筑單元,并通向紫禁城內部。然而,作為明清時期國家權力中心的所在,紫禁城內的景象卻沒有被呈現出來——兩幅南巡圖都真正結束于午門外。另一方面,通過這種“缺失”,可以發現圖像背后存在著關于空間的表征意志,即內與外、不可表征性與可表征性的分界。但中軸線卻具有某種溝通的功能。除了在實體層面上連接起城內與城外,長卷的形制以及中軸線的水平形態強化了視覺的延伸,使中軸線具有非實體性的效果。加之中軸線出現在首尾卷中的敘事意義,其余十卷表現的南巡活動可以被視作中軸線的想象性展開,并且是一種權力話語的展開。這也就意味著,其他各卷中的山川和城鎮都內在于由中軸線所引導和組織起來的符號系統中,而不同的地域形貌恰好構成了對無限的權力空間的隱喻。
雖然不可見的紫禁城內部和可見的山川城鎮之間,通過中軸線建構起了由中心到邊緣的空間規制與權力流動關聯;但與此同時,中軸線的整體形貌(紫禁城以北部分)及其與北京城的空間關系卻是“不可見的”。這種局部化的可見性與南巡圖的表征意圖密切相關,也折射出中軸線在該時期所扮演的角色,即它并非作為審美化的景觀在場,而是作為儀式的、神圣的空間獲得定位。在這一空間中,筆直開闊的道路、恢宏的建筑單元以及相應的禮制規定等都是對權力的展示,并且它自身的局部化表征又暗示了權力的無限維度。這種有限與無限的辯證關系以及該空間的神圣性之所以能被建立,依賴于一套相對完整的意識形態話語,確保中軸線的表意是明晰的、統一的和秩序化的。然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當梁思成面臨北京城的改造問題時,他的相關論述就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參照來考察意識形態話語的轉變對中軸線的表征的影響。
二、天安門廣場:意識形態的改寫策略
20世紀90年代,侯仁之通過考察中軸線在歷史發展中呈現的不同特點形成了所謂的“三個里程碑”思想。他指出,天安門廣場的改建是北京城市規劃建設史上的第二個里程碑,這個“在北京城的空間結構上、突出地標志著一個新時代已經來臨的天安門廣場。它賦予具有悠久傳統的全城中軸線以嶄新的意義”*侯仁之:《試論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中的三個里程碑》,《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9月。。正如列斐伏爾所說,“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么‘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頁。,而天安門廣場的改建作為高度自覺的歷史行為,它與新中國成立之后對北京的城市性質的重新定位是密切相關的。因此,中軸線的“變形”的發生及其癥候性意義需要放置在意識形態話語的轉換中加以理解。
以侯仁之為代表的諸多研究者,已突顯了由天安門廣場改建所折射出的權力意志。作為新舊時代更替的重要象征,它不僅標識了中軸線空間屬性的轉換,即從宮廷廣場變為人民廣場*參見侯仁之,吳良鏞:《天安門廣場禮贊——從宮廷廣場到人民廣場的演變和改造》,《文物》1977年9月。;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種意識形態化的空間改寫策略,建構了一種新的視覺慣例及相應的歷史敘事。但事實上,由回溯性的視野呈現的這一變形,遮蔽了話語轉換過程中的其他面向,并尤為表現在審美維度在中軸線的空間政治中的消隱。而梁思成在20世紀50年代寫下的《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一文成為某種歷史蹤跡,可借以重新審視中軸線變形所涉及的話語轉換和策略選擇。
新中國成立前夕,北京市人民政府組建了都市計劃委員會著手北京的規劃建設。時任該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在與蘇聯專家的激烈討論中,與陳占祥一起提出了在西郊另建中心和保護歷史名城的“梁陳方案”。1951年4月,梁思成在《新觀察》上連載了這篇《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詳細闡述了北京的城市特點及其保護性改建的構想。作為有關北京城市研究乃至所謂的“北京學”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獻,他在“北京的城市格式”部分,不僅強調了中軸線在城市結構中的重要性,還以審美性的語調突顯出它的特征——“一根長達八公里,全世界最長,也是最偉大的南北中軸線穿過了全城。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生”*②④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110頁,第107頁,第107頁。。
盡管梁思成是以文字而非圖像來描繪中軸線,但他那極具視覺性的文字鋪陳出中軸線的全新形象,即一種審美化的奇觀。與南巡圖相比,梁思成筆下的中軸線已發生了重要的表征變化,這首先表現在它自身成為了觀賞的對象。讀者不僅可以直接從梁思成抒情化的寫作中感受到他作為一位審美者由衷的贊美與作為一位建筑師的喟嘆;更為重要的是,梁認為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觀賞中軸線獲得相似的體驗。事實上,這種體驗的獲得依賴于理想視點的建構,即“在有了飛機的時代,由空中俯瞰,或僅由各個城樓上或景山頂上遙望”②。于是,中軸線呈現為一條貫穿全城并主導北京城市格局的垂直線,這就不同于南巡圖中水平的和局部化的中軸線形象。
即便在那個年代這種俯瞰的視角不一定是觀看的常態,更不用說以 “中軸線”*據很多人考證,“中軸線”一詞出自具有西學背景的梁思成,可追溯至他于1932年發表的《敦煌壁畫中所見的中國古代建筑》一文。梁思成發明這一新詞,原是用以表述中國古代建筑的某種共性。的方式去感知北京的空間格局;梁思成的文字卻替代性地呈現了這種視覺景象,也由此定義了北京城的中軸線奇觀。而壯美,這個具有中國傳統美學精神的概念,便被定型為某種對中軸線的體驗模式,并延續至今。
但在他奇觀化的描述中,不難發現存在著一處明顯的敘事斷裂,使南起永定門、北抵鐘鼓樓的中軸線的整體性受到擾亂。在此,爭執的焦點不再是明清時期作為中軸線核心單元的紫禁城,而是轉移到天安門及其附近空間。他寫道,“由中華門到天安門,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這中間千步廊(民國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長度,和天安門面前的寬度,是最大膽的空間的處理,襯托著建筑重點的安排。這個當時曾經為封建帝王據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當的回到人民手里,成為人民自己的廣場!”④不同于侯仁之對這一空間的改建的回溯性禮贊,在梁思成的情感化表述中潛藏著一種焦灼,它源自于如何應對意識形態話語之間的張力及其轉換。這就涉及了審美奇觀作為一種空間改寫策略的意識形態訴求——通過保護性改建完成權力話語的轉換。
雖然梁思成的這一策略,尤其是中軸線的審美性重構,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北京城市規劃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參照;但是,“梁陳方案”卻因不符合當時政府對北京形象與功能的期待而被棄用*依據1953年編制的《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要點》來看,從消費型城市轉向生產型城市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城市規劃的主導方向。。隨著眾多舊建筑物的拆除(如永定門、前門牌樓和地安門等)、街道的調整和土地的分區,中軸線及其相關的空間格局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中軸線的這一次變形中,最具象征性的是天安門廣場的改建。而由于審美維度的逐漸消隱,空間的意識形態色彩變得尤為鮮明,天安門廣場的改建也就實質性地呈現為新的權力話語置入和確立的過程。由此,不僅使舊中軸線的空間屬性被轉換,也同時生產出了一種新的歷史敘事。
首先,由前門到天安門,原本是一段狹長而封閉的過渡性空間,經過多次擴建,天安門廣場不僅在體量上遠遠超過了紫禁城的規模,其作為現代廣場的政治功能也不斷被強化;其次,東西長安街的連通和拓寬,打破了舊中軸線的連續性和整體性,使得天安門廣場最終從舊中軸線的表意系統中獨立出來,成為新的表征空間并實踐歷史敘事的重構。
這個敘事的原點便是天安門,作為“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以及宣布新中國成立的神圣之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與之遙相呼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天安門廣場內最早決定修建的重要建筑,*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在天安門廣場上修建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當天下午毛澤東為紀念碑奠基,1958年5月1日正式落成。它大致坐落于前門到天安門的中心位置,37.94米的高度不僅超過了紫禁城內太和殿的高度,而且確保了“由北面任何一點望過去,在透視上碑都高過正陽門城樓”*③④⑤梁思成:《梁思成全集》(第五卷),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1年,第463頁,第462頁,第463頁,第107頁。。這是與當時眾多設計方案者的根本共識一致的——“中國古碑都矮小郁沉,缺乏英雄氣概,必須予以革新”③。這座新落成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憑借它自身的體量無疑成為了中軸線上新的視覺中心,內在地引導著廣場的視覺運動。事實上,早在紀念碑設計之初,它就被置于了一個關鍵的空間點,并先在決定了天安門廣場的規模,④也改變了舊中軸線的視覺節奏。
隨著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建于1958年,后更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和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建于1958年)的修建,北邊的天安門和南邊的前門與之構成了一個半閉合的空間。這些體量巨大的新建筑及其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不僅強化了廣場空間的崇高風格,也構成了新意識形態話語的自我展演。而在中華門原址上興建起來的毛主席紀念堂(建于1976年),則在繼紀念碑之后進一步將視覺重心南移;同時,天安門廣場也在不斷往南擴展,最終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現代廣場。由此,紫禁城與天安門廣場,在視覺規模和符號配置上的差異,呈現出意識形態話語之間的對立和壓制。
在中軸線的這一變形中,天安門廣場不再是原有權力表征秩序中的一個節點,而是取代紫禁城成為了新的權力中心。盡管舊中軸線的某些基本形貌依然留存了下來,但無疑在新的話語系統中衰落了。但無論是梁思成還是侯仁之,都已洞見了天安門廣場的興建是對中軸線的一次強力改寫,即賦予它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內涵;不同的是,梁思成試圖借助審美性的策略,弱化天安門與紫禁城之間的對峙,使岌岌可危的中軸線得以持存。與之相較,侯仁之提出的三個里程碑的觀點,則突顯了凝結在中軸線之中的不可抵消的沖突。不過,這種沖突或對峙卻在隨后的話語系統中被整合,共同構成為有關北京的敘事鏈條中前后銜接的階段。而整合之所以可行,乃是基于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訴求——將北京置入全球化的視野中。
三、延伸中軸線:奧運時代的奇觀政治
如前所述,舊中軸線分別以永定門和鐘樓為南北端點,全長7.8公里。但及至2008年奧運會舉辦之時,沿南北方向延伸后的新中軸線,已長達25公里。其中,中軸線的北延,作為侯仁之所說的第三個里程碑,標志著中軸線“變形”的再次發生。與第一次變形即天安門廣場對舊有空間秩序的意識形態改寫不同,世紀之交的這次變形則是在他者與自我目光交織下的奇觀轉化。那么,與亞運會和奧運會的相繼舉辦密切相關的這一轉化,又是如何生產與被生產出來的?
雖然梁思成在20世紀50年代已指出,北京城的舊中軸線是“全世界最長,也最偉大的南北中軸”⑤,而由中軸線貫穿的建筑總布局和空間規模也是獨一無二的;但是,由于梁的方案并不切合社會主義生產型城市的建設要求,隨后,包括中軸線在內的一些歷史文化古跡在愈發失控的城市改建中遭到嚴重破壞。及至80年代,新舊意識形態話語之間的沖突似乎“消解”了,在諸如《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1983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1991年—2010年)》和《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等文件中出現了雙重北京形象的建設構想——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現代國家城市。與1953年的規劃草案相比,80年代以來關于北京的形象與功能定位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前者要將北京建設為一個大工業基地,后者則要將北京改建為現代化的國際大都市,而中軸線作為重要的城市文化景觀和有效的空間組織形式也被不斷強化。隨之,那些曾經遭到破壞的中軸線建筑逐漸得以修復,*在這一時期,不僅永定門和前門大街得以重建,地安門內外大街得以整治,鐘鼓樓、皇城墻、萬寧橋等建筑也得以修繕。并且由于籌辦亞運會和奧運會,中軸線一反傳統地向北延伸,被侯仁之視為北京城市規劃建設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
事實上,侯仁之提出的三個里程碑,與中軸線的兩次變形密切相關。變形的發生伴隨著一種新的建筑語言的置入,讓原本的空間結構發生變異,從而生產出適應意識形態訴求的表征慣例。如果說天安門廣場的改建所帶來的西式廣場與古代宮殿的對立,反映出現代民主話語對封建皇權話語的抵制,那么,中軸線的延伸及奧林匹克公園的興建則代表了另一種轉折—— “北京走向國際性大城市的時代已經到來”*侯仁之:《試論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中的三個里程碑》,《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9月。,即建設多元、開放、現代的北京。
“新北京·新奧運”的申奧口號的提出,進一步表明城市轉型與中國轉型的自覺意識。不過,“新”之為新,并非與過去的截然對立,它表征的乃是一種奇觀化的空間意志和話語運作,即試圖在過去—現在—未來的聯動中將北京重塑為國際化的大都市。德波曾指出,奇觀也“是我們被卷入其中的歷史運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王昭鳳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頁。,在這一過程中,中軸線再次成為展示意識形態訴求的理想場所——壯美震撼的視覺觀感和獨一無二的人文價值,并且通過舊中軸線的延伸,奇觀的視覺效果不僅得以綿延和強化,也傳達出一種富有癥候性的北京想象。
及至2008年8月8日北京奧運會開幕當晚,伴隨著蔡國強設計的焰火表演和電視、網絡及攝影等現代媒介的傳播,全新的中軸線在“大腳印”的漸次燃放中展示了自身的奇觀姿態——不僅被“戀物化”地建構為中國傳統文明的重要符號,同時,奧林匹克公園以及新地標建筑物的興建,又傳達出了某種與空間革新有關的表征意志。雖然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梁思成已用文字實踐了中軸線的奇觀化,但當奧運會舉辦之時,被奇觀化了的不只是中軸線自身,還包括它所象征的整個中國文化,甚至中軸線作為第一個出場的表征意象,就表明了它的圖騰特征;而這卻是梁思成的文字所無法達到的奇觀效果。二者的根本差異在于,凝結于中軸線這一特殊空間的社會關系已發生了改變。
隨著傳統中軸線的修復和延伸,梁思成提出的城市改建方案再次受到關注,被視作一種關于當代中國的預言,并且是正在上演的預言。誠然,對中軸線的保護以及延伸所帶來的城市空間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已經失落的舊北京的拯救,不僅希冀恢復原初的壯美景觀,也試圖賦予其與時代相應的生機與活力。不論是蔡國強的大腳印,還是奧林匹克公園的規劃,抑或舊中軸線的保護與修繕,所具有的修辭功能在于,試圖完成新舊之間的過渡并賦予新北京一種合理性。
2001年7月北京申奧成功之后,奧林匹克公園的規劃設計備受矚目。截至2002年7月北京奧運設施規劃設計方案展開幕時,共有87個方案參加競選,最終美國薩薩基(SASAKI)公司和天津華匯工程建筑設計有限公司的合作方案“人類文明成就的軸線”最終獲選。從題名不難看出,這支國際化的團隊有意識地強化了中軸線的概念,借此不僅將當下的北京置入中國自身的歷史傳承中,還將北京置入了人類文明史之中。例如,他們在中軸線北端設計了一條長約2.3公里的 “千年步道”,在其兩側分布著眾多的體育場館以及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宋元明清各個歷史時期的紀念物;他們還設計了一條斜軸——由亞運會場館、國家體育場、體育英雄公園組成——與步道交匯,并在交匯處建立大型廣場;等等。無論是對中軸線的強化,還是對眾多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如龍、山水等)的運用,這種空間組織形式及其修辭技巧,都力求高度契合北京乃至中國的自我設想——一種在全球視野之下可觀可知的“新”形象,“綠色”、“人文”、“科技”三大理念就是其概括性表達,而這已成為了當時諸多設計方案的共識。
與此同時,作為新中軸線的北部終點,奧林匹克公園內頗具后現代風格的建筑物也使得視覺節奏發生了改變。隨著鳥巢和水立方被認同為北京的新地標和表征中國的新符號,中軸線的表意重心也向北移動。由于鳥巢和水立方的后現代建筑外形和高科技功能特性,使得北部延長線的空間具有了不同于傳統中軸線的權力象征功能和政治經濟屬性。不過,新的延伸部分并不排斥舊中軸線。毋寧說,它正是通過挪用舊中軸線的空間組織形式,從而生產出了一種與新的社會秩序相稱的表征關系。
就像列斐伏爾曾指出的,空間“被各種歷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式鑄造”*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2頁。,北京中軸線的變形,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的重構,則依賴著新的空間生產策略和奇觀政治經濟學。這也就意味著,傳統中軸線的南北延伸事實上具有城市再開發的性質,它不僅打破了舊有的中心與邊緣、城市與郊區的界域以及原本所固有的生產系統,還主導性地作用于新的空間架構和功能分配。如果說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中軸線變形,是一種以對抗性的姿態改寫舊中軸線空間屬性的歷史過程,那么從80年代末期以來的中軸線延伸,則試圖以更為宏大的敘事視角實踐城市空間的重構。
據《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新中軸線可分為三大段落并呈現出不同的發展側重點——北部作為體育文化區、中部作為歷史文化區、南部作為城市新區。這種分區規劃,在更為廣闊的地理想象中實踐著中軸線組織城市空間的功能,并表現為一種秩序化的空間圖景和現在—過去—未來的城市敘事。在此,如列斐伏爾所說,空間的改變反過來會影響生產方式的改變以及社會的改變,中軸線的三大分區也意味著一種新的社會構型及其相應的空間結構正在被生產出來。
沿新中軸線進行的分區規劃,既是對當前越來越快速流動的人口、文化及經濟等社會現實的呼應,也是為適應全球化的境況所進行的調整。從這種規劃定位,不難發現,中軸線的保護和建設正成為促進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它不僅影響著人口與經濟的地理分布,也帶動城市新空間的建設,如奧林匹克公園周邊的改建和南部新區的規劃等。而隨著這些新空間的出現,奇觀的政治經濟學也在微觀層面上變得越來越重要。諸如前文已提及的鳥巢和水立方等建筑,因其后現代的風格造型和政治象征意味不僅成為了中軸線北段的重要景觀,也成為了北京的新地標。如果說,將中軸線視作北京(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奇觀式重構是從一種整體視角出發的話,那么,中軸線上那些新異的建筑的出現,則是在具體空間中象征性地實踐著人口、資金等方面的分類,并日益充當了城市當下的文化形象。對于當前文化記憶逐漸淡化的危機而言,奇觀化的中軸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重塑認同的積極意義,同時,其“變形”也表征著對城市未來發展的一種預見。
當前,新近發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依舊延續了保護北京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訴求,并明確了建設國際一流的和諧宜居之都的發展目標。隨著“一主、一副、兩軸、多點”的城市空間結構的提出,作為兩軸之一的中軸線及其延長線也將被納入新一輪的布局調整和功能優化的過程中,這或許會成為中軸線再次發生“變形”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