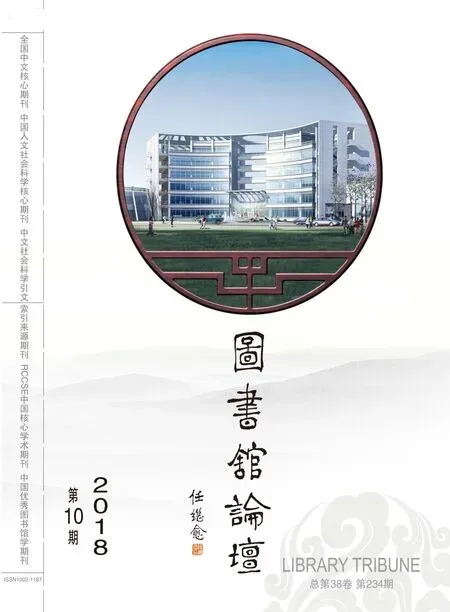閱讀遴選視域的中外文學及相關問題思考
——對2017年大學圖書借閱榜的解讀
由《文摘報》微信公眾號2018年4月18日匯聚的“北大、清華等17所名校圖書借閱榜”廣受關注,這份源自各高校圖書館發布的本校2017年閱讀報告的借閱榜①,其關注視野極大限度地超越了圖書館界。比如,登上這份榜單的圖書,其搜狗百科的內容介紹一夜間添加了一條信息:“2018年4月,XX(書名)排名XX大學借閱榜第X位。”[1]這說明圖書館的閱讀數據蘊含極高的文化信息價值,有待挖掘和利用。從這份借閱榜可以讀出不少引人興味的信息。本文僅就其中文學閱讀取向背后的信息略談三點:網絡文學已成主流;日本文學倍受青睞;大學教育的失敗。
1 網絡文學已成主流
1.1 網絡文學明顯占優
這份高校圖書借閱榜涉及的學校并非都是名校,包括了湖南工業大學、廣東財經大學等普通院校。其實,學校的多樣性更能反映中國高校的閱讀實況。就這17所高校的圖書借閱榜來看,有14所高校排在榜首的借閱書目是文學作品。其中,浙江大學、天津科技大學、東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等四所高校排名榜首的是傳統紙本小說《平凡的世界》;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外國語大學、廣東財經大學等三所高校排名榜首的是網絡小說《盜墓筆記》;中山大學、山東大學等兩所高校排名榜首的是網絡小說《明朝那些事兒》;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兩所高校排名榜首的是法國19世紀小說《基督山伯爵》;武漢大學、湖南工業大學、河南大學等三所學校排在榜首的分別是《神雕俠侶》和日本的《嫌疑人X的獻身》《源氏物語》。如果在這些小說中剔除外國文學,那么,源自傳統紙本的《平凡的世界》《神雕俠侶》,以及源自網絡文學的《盜墓筆記》《明朝那些事兒》均五次榮登榜首,看起來傳統紙本文學與網絡文學打了個平手。但若加入時間維度,網絡文學明顯占了上風。傳統紙本小說,無論是《平凡的世界》,還是《神雕俠侶》,均是20世紀的中國文學創作;新世紀的文學,在這個借閱榜中屬于網絡文學的天下。如果將這個榜單的視野再放開一些來看,北京大學排行前十的圖書,只有一本是小說——網絡小說《明朝那些事兒》。中山大學排行前三的《明朝那些事兒》《盜墓筆記》《藏地密碼》都是網絡小說。山東大學排名前三的《明朝那些事兒》《藏地密碼》《你好,舊時光》也是網絡小說。就17所高校借閱榜全部書目中文學作品的總頻次來看,《平凡的世界》出現11次,排名第一;《明朝那些事兒》出現9次,排名第二;《盜墓筆記》出現8次,排名第三;《藏地密碼》(也是源自網絡小說)出現7次,排名第四……在總頻次上,網絡文學也是明顯占優的。
雖然如今各類閱讀排行榜可謂多矣,但大學圖書館的借閱排行榜不存在商業利益動機暗藏的貓膩,而且高校畢竟是文化高地,部分大學生畢竟更能代表中國文學的未來。所以,其信息對判斷中國文學發展狀況的意義不可低估。
行文至此,需要就網絡文學的界定補說幾句。關于網絡文學,有一種十分寬泛的定義,泛指一切在網絡上傳播的文學。如此寬泛的理解,在媒介文體學上沒有意義。本文認可北京大學中文系邵燕君的觀點:網絡文學“專指在網絡上生產的文學”[2]。從網絡上生產出來之后,經過網絡閱讀的汰選,優勝者再出紙本,是網絡文學經典化的一種方式。故源自網絡文學的紙本,應該屬于網絡文學范疇。
1.2 文學汰選機制的博弈
很難將21世紀傳統紙本文學在大學圖書館借閱榜上敗下陣來的原因歸結為藝術質量的優勝劣汰。這其中關鍵的因素,可能還是在兩種文學汰選機制的博弈中,網絡文學成了贏家。
一般來說,隨著信息量的劇增,信息汰選變得尤其重要。在如今這個信息空前大爆炸的時代,網絡文學比之于傳統紙本文學,擁有更具優勢的汰選機制。就紙本長篇小說的產量而言,1919-1949年我國出版的原創長篇小說不過400余部,而今一年生產紙本原創長篇小說在4000部以上,生產網絡原創長篇小說在15萬部左右[3]。無論是傳統紙本文學還是網絡文學,其汰選機制都必須以閱讀為基礎。但是,傳統紙本文學是一種“個人化”的從“密室寫作”到“密室閱讀”的方式,“密室閱讀”的封閉性使其能見度主要體現在文學批評文本上。因而,傳統紙本文學汰選機制主要依賴專業文學批評家的評論及這種評論對讀者的影響。在紙本文學時代,常見的情形是一撥作家的出道常常伴隨著一撥批評家的出場,比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經典化與劉再復、何西來等批評家的業績關聯;再如,莫言、馬原、余華等先鋒作家的經典化與季紅真、吳亮、陳曉明等批評家的成就關聯。但是,當一年產生4000余部紙本長篇小說的時候,批評家們有限的閱讀能力必然使傳統紙本文學的汰選機制陷入掛一漏萬、盲人摸象的尷尬。而網絡文學的汰選機制是建立在互動閱讀的開放可見基礎上的,并以量大、速高、累進式計量來顯示人氣指數,它可將每年15萬部長篇小說進行以人海閱讀為基礎的年復一年的累進式人氣指數排序。因此,網絡文學汰選機制與傳統紙本文學汰選機制的PK就演變成為大數據與專家眼光的PK。如果說,在數據偏小的情況下,專家眼光勝出是大概率,那么在數據如此龐大且日益龐大的情況下,大數據就顯出它的優越性。雖然可以憂心忡忡地質疑這種“數字人文”之審美趣味,以及這種審美趣味對社會文學鑒賞力的平面化牽引,對文學生態多樣性的破壞,但無以抗衡它對作品的巨大舉薦能力。
1.3 媒介變革的文學迭代經驗
談及網絡文學,通常會因其門檻過低而導致規模龐大、質量堪憂、品位低俗,讓人低看一等。其實人類史上哪一次媒介革命,如果以習慣的舊媒介標尺度量,不都是一次內容的下墜與墮落?從龜甲楔刻神諭到紙代簡帛之私人書信的涌現,其文字內容由神圣之言走向家長里短、兒女情長是下墜與墮落;機印術開啟通俗小說大行其道當然也是下墜與墮落。
機印術發明之后,誕生了世界文學史上第一部偉大的長篇小說《堂吉訶德》。通常認為,塞萬提斯的這部小說意在嘲諷當時風行的騎士小說,這當然是不錯的。但這部小說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將當時騎士小說的風行與機械印刷興起關聯起來,認為正是歐洲機械印刷的興起使得以贏利為目的的書籍生產成為可能,才導致胡編濫造的騎士小說的涌現。這一內容寫于該書“第六十二章 通靈頭像以及其他不可忽略的瑣事”[4]。可惜的是,后來關于《堂吉訶德》的闡釋雖然層出不窮,高見迭出,卻恰恰忽略了塞萬提斯特別提示的這一章所“不可忽略的瑣事”(即機械印刷革命導致內容生產的下墜與墮落)。有意味的是,《堂吉訶德》不僅同樣是當時機印術的產物,而且在它出版后近200年的時間內都被歸屬于情節隨意且漏洞不少的地攤逗笑讀物。對其評價越來越高是200年以后(即18世紀以后)的事。直到19世紀,評論家才認識到,“在歐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學作品中,把嚴肅和滑稽,悲劇性和喜劇性,生活中的瑣屑和庸俗與偉大和美麗如此水乳交融……這樣的范例僅見于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5]。因此,在對待網絡文學的態度上,需要具有將今天的閱讀觀察放進歷史視野的能力,否則,不能鑒往知來而超越流俗觀念。
2 日本文學倍受青睞
2.1 日本文學占半壁江山
這份圖書借閱榜顯示的是各高校圖書館借閱排名前十的書目。在這些書目中,外國文學總計29種38頻次,而日本文學就占據了14種17頻次。其他國家的排序是:法國5種7頻次(《基督山伯爵》《小王子》各出現2次,《悲慘世界》《偷影子的人》《羊脂球》各出現1次);英國5種5頻次(《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一九八四》《呼嘯山莊》各出現1次);美國2種5頻次(《冰與火之歌》出現4次,《銀河帝國》1次);阿富汗1種2頻次(《追風箏的人》);哥倫比亞的《百年孤獨》、挪威的《蘇菲的世界》各出現1次。
在14種17頻次的日本文學書目中,出現最多的是東野圭吾的小說,計有《嫌疑人X的獻身》《白夜行》《十一字殺人》《分身》《變身》《白馬山殺人事件》等6種9頻次;其次是連續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卻未能獲獎的感傷作家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海邊的卡夫卡》《且聽風吟》3種各上榜1頻次;其余上榜1頻次的作品是安倍夜郎的《深夜食堂》、美嘉的《戀空》,以及《青山七惠小說集》《日本精彩推理小說選》。在當代作家之外,還有一部公元11世紀的古典名著《源氏物語》。
這份書單閱讀總頻次排名前三的國家中,進入中國大學生眼簾的作品,無論是排名第二的法國文學,還是排名第三的英國文學,主要都是過去時代的經典之作。當然,法國有一部當代暢銷書《偷影子的人》進入了借閱榜。閱讀總頻次與英國并列排名第三的美國文學則幾乎都是當代作品。之所以說“幾乎”,是因為阿西莫夫的《銀河帝國》屬于1950年代的創作,而擁有4頻次的喬治·馬丁的系列長篇《冰與火之歌》的創作一直延續至今。日本文學14種17頻次中,當代作品占據13種16頻次。由此可讀到這樣的信息:外國當代文學對中國青年形成的影響,首當其沖是日本,其次是美國,法國再次,英國則屬于輝煌往昔的余輝,而曾經在1950年代對中國構成絕對影響力的俄羅斯文學已經從中國青年的閱讀偏好中遠去。
2.2 東野圭吾的中國讀者
東野圭吾是當代日本推理小說的頭牌。世界推理小說重鎮原在英美,自1960年代開始移向日本。東野圭吾作品于2008年引進中國之初,其版稅是每部萬元人民幣,到2012年躥升至每部百萬元人民幣。截至2017年,其作品在中國發行106部,發行量超過800萬冊。有報道說:“打開北京開卷統計的暢銷書排行榜,沒有哪位作家能夠撼動東野圭吾的位置,比如從2017年以來,他的三部作品長時間連續霸占虛構類排行榜,沒有什么值得懷疑東野圭吾在中國讀者心目中的位置。”[6]從2017年高校圖書借閱榜看,東野圭吾的閱讀熱潮還帶來了國人對推理小說的熱情。第一代推理小說頭牌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全集》、第二代推理小說的頭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尼羅河上的慘案》也都上榜;東野圭吾是第三代。
為什么中國會迎來這么一波以東野圭吾為旗的推理小說熱浪?有調查從微觀層面顯示,它可能與中國1999年引進日本動畫《名偵探柯南》有關。在該動畫引進的隨后數年里,在中國排名前50的動漫作品中這部動畫位列前二。當年浸潤于該動畫的少年兒童十年或十幾年后成長為今天熱捧推理小說的讀者。所以,熱衷東野圭吾的讀者91%是18-30歲的青年人[7]。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中國工業化社會的進程日益偏向于工科理性思維,其對校園文化和社會文化的塑造與推理小說注重嚴謹理性和精湛的邏輯推理以揭示案情迷題的過程相契合。這或許是理工科出身的東野圭吾及其推理小說廣受歡迎的社會文化基礎,更何況中國民間一向崇尚孔明、吳用神機妙算的智慧之光,并擁有源遠流長的公案小說傳統。
2.3 浮物之下的流動
中國近代以來所遭遇的創痛,雖然并非全部來自日本,卻以日本最多最巨,因此中國人對日本人積怨深厚。2012年釣魚島事件以來,無論是主流媒體中有關中日外交、軍事的報道,還是網吧微信的民間八卦傳播,都令歷史積怨找到了火山口,以至于愛國與不愛國在許多國人眼里直接與是否反日甚至抵制日貨簡單地劃上等號。在這樣的情緒氛圍之中,高校的閱讀以及它所反映的當前中國的閱讀文化卻呈現出一角爛漫櫻花,著實令人尋味。這是否意味著,相比于文化之潛沉,社會層面的恩怨以及由釣魚島事件激起的政治外交事件及民眾情緒可能更像是浩浩湯湯歷史長河之上飄蕩聚散的浮物。在這浮物之下,一衣帶水的鄰居間千百年來最熱烈的文化學習有其不受一時一事干擾的定力。日本民眾曾經是中國文化最熱烈的學習者,正是這種學習令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華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比如服飾、建筑、書法、圍棋和禪宗。近代以來,日本作為東亞現代史上的先發國家又成為中國學習歐美現代文化的中介,以至現代漢語中社會和人文學科方面的名詞、術語,70%來自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最近20多年,從日本動漫到村上春樹,再到東野圭吾,一定程度地伴隨國人從少年到青年一代的文化成長。郭敬明們以《幻城》為代表的奇幻文學的風靡與日本動漫及受此動漫文化浸潤成長的一代人有著內在的聯系,而翻開中國80后的青春文學,村上春樹小說那種以修辭的華麗支撐作品的感情、人物、邏輯,那種都市時尚色彩的意味,尤其是那種憂傷、孤獨、無奈的情緒,俯拾即是。東野圭吾是動漫、村上春樹之后又一波日本流行文化在中國的涌流。這涌動澎湃而起于2012年,竟然與釣魚島事件爆發的年份重合!釣魚島事件之后中日關系的持續緊張顯然并未構成對東野圭吾在中國人氣的打壓。
而中國當代文學,如果在異國成為暢銷書,也多半是在日本。比如,1960年代中國與日本的邦交尚未正常化,楊沫的《青春之歌》就曾是風靡日本的暢銷書;新世紀莫言摘取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之前,在日本早已成為“中國的馬爾克斯”[8]。
3 學校教育的失敗
3.1 令人沮喪的信息失控
這份圖書借閱榜呈現的高校閱讀遴選視域中的中外文學,從教育的立場看,則著實令人沮喪。如果說信息并非知識,知識是基于特定認知與理解目的而組織起來的信息,那么這種“組織化”首先體現為對信息的濾選。通過濾選而納入一定的結構系統,才可能建構成知識。北美媒介生態學者尼爾·波斯曼將信息的知識化建構看成是對泛濫信息的限制和控制,學校則是對泛濫的信息實施有效限制和控制的最重要機構。一個有趣的故事是,印刷機的出現給聰明的學生通過自主閱讀而超越老師掌握的知識提供了機會,以至于15世紀有一位歷史綱要的作者發問:“既然年輕人可以依靠勤奮讀書學到同樣的知識,為什么還要老師呢?”[9]這個歷史學者的發問包含這樣的意思,即印刷機的發明使學校變成多余。但事實剛好相反,在1480年由印刷機引發信息爆炸之前,英格蘭只有區區34所學校,至1660年學校總數達444所,平均每12平方英里就有一所學校。在尼爾·波斯曼看來,現代學校的大規模誕生與發展,實乃對印刷機所帶來的信息泛濫的必要回應。“課程設置的發明就是邏輯的第一步,目的是對信息源頭進行組織、限制和區分。……它們使一些信息流動合法化,另一些信息流動聲譽掃地。”[10]就中國高校對中國文學信息進行的組織、限制和區分來說,網絡文學就處于聲譽不佳之列,它雖然來勢浩蕩,卻基本上未能在大學的文學課程、教材以及推薦參考書目中占據合法性地位。它在高校圖書館的借閱書榜上獲得如此亮眼的頻次會令許多資深的人文學教授感到羞愧。同樣,在我國高校外國文學教學體系中,亞洲文學是被邊緣化的,印度文學與日本文學常常點到即止,其教學重點是歐美文學和俄羅斯文學。但在這份借閱榜單上,日本文學幾乎占據外國文學的半壁江山,俄羅斯文學竟未露面。
這份圖書借閱榜所呈現的文學河山與我國高校文學教學導向大相徑庭,它意味著學校教育的信息失控,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國學校教育的失敗。
3.2 如何應對新的閱讀文化
如上所述,現代學校教育誕生于對印刷機所造就的泛濫信息環境的回應。而聲光影像、數字傳媒、“互聯網+”所造就的數字化文明已遠非印刷文明的信息環境可望項背,它使信息生產與傳播的形式、數量、速度、可獲得性以及信息的偏好等都發生了深刻改變。這些深刻改變重塑了社會話語結構,重組了文化知識和其價值秩序——傳統的金字塔形的結構和等級已經趨于扁平化、平等性。比如,在今天,荷馬的《伊利亞特》、但丁的《神曲》、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曹雪芹的《紅樓夢》、喬治·馬丁的《冰與火之歌》、東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獻身》、南派三叔的《盜墓筆記》、當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兒》都進入了“讀秀學術搜索”之類的數據庫。在這類數據庫中,讀者可從諸如題名、作者、主題、關鍵詞、引文、文本片段、時間等多種路徑直達自己所需要的文本及文本局部。尤其是在搜索凸顯的文本局部面前,任何著作,無論是曾經顯赫的經典抑或是地位卑微的消遣讀物,它們之間的閱讀價值鴻溝都接近消失。閱讀價值只與讀者特定的甚至是臨時的需求相關,唯有讀者個人化的需求才是至高無上的。數據庫是這樣,互聯網的各種搜索引擎也是這樣。信息技術與互聯網就這樣塑造了去文化等級化的、以個人化需求為價值標尺的閱讀文化。
新的閱讀文化必然包括閱讀味蕾的改變。曾經“只是看不厭”[11]的《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如今赫然排入“死活讀不下去的書”排行榜的前十位②。它意味著新的閱讀文化已經將經典邊緣化。老師勸說學子閱讀經典的理由大多是:經典屬于經過漫長時間過濾后剩下的精華,是經過了人類歷史上最智慧的人所挑選,或者說它有千百年來最智慧頭腦的背書,知識含金量高,因此閱讀經典的投入產出比高。但是,既然已經“死活讀不下去”,其投入產出比顯然會走向反面。
其實,道理(觀念)總是片面的。如果唯經典是瞻而厚古薄今,就意味著生在塞萬提斯的時代你會錯過《唐吉坷德》,因為它從地攤讀物達到經典標準需要至少兩百年的時間。同樣,生在羅貫中時代的你會錯過《三國》《水滸》,生在曹雪芹時代的你會錯過《紅樓夢》,生在魯迅時代的你會錯過《吶喊》《彷徨》,這難道不也是一種閱讀的大不幸?從年齡代際的特征來說,年輕人更傾向在好奇的意義上閱讀,易于厚今薄古;上年歲的人更傾向在回味的意義上閱讀,易于厚古薄今。因此,信息的知識化與學校對信息的限制與等級化區分,實際上也是一種代際文化話語權的博弈。
傳統社會的文化話語權掌控在長者手中,因其文化價值迭代的周期相對漫長。孔子時代以30年為一“世”③,唐代李世民做了皇帝,為避諱,“世”以“代”替,仍然是30年。民間俗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的正是這樣一個世代周期。但現代信息社會的“互聯網(以及移動互聯網)+”時代,世代周期明顯縮短。其重要表征即人文書籍的文獻半衰期縮短,因而厚今薄古的閱讀取向壓倒厚古薄今的閱讀取向。
面對如此新時代和如此新閱讀文化,學校基于印刷文明的一套信息組織、限制和區分之管控體制應該如何變革自身來回應這巨變的時代?學校教育的信息失控,將此問題凸顯出來。
注釋
①參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天津科技大學、天津外國語大學、廣東財經大學、湖南工業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西南財經大學、東南大學以及河南大學等圖書館發布的2017年閱讀報告。《文摘報》微信公眾號(2017-04-18)對這些閱讀報告的圖書借閱榜的匯聚,其鏈接地址為https://mp.weixin.qq.com/s/i69bhjv0JvcQ6wEAI OJWZA.
②“死活讀不下去排行榜”是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于2013年6月通過對近3000名讀者吐槽最多的“讀不下去”的書進行統計后發布的排行榜。榜單前十名依序是《紅樓夢》《百年孤獨》《三國演義》《追憶似水年華》《瓦爾登湖》《水滸傳》《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西游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尤利西斯》。
③《說文解字》卷三之卅部曰:“三十年為一世。從卅而曳長之。亦取其聲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說:“如有一位王者興起,也必三十年時間,才能使仁道行于天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