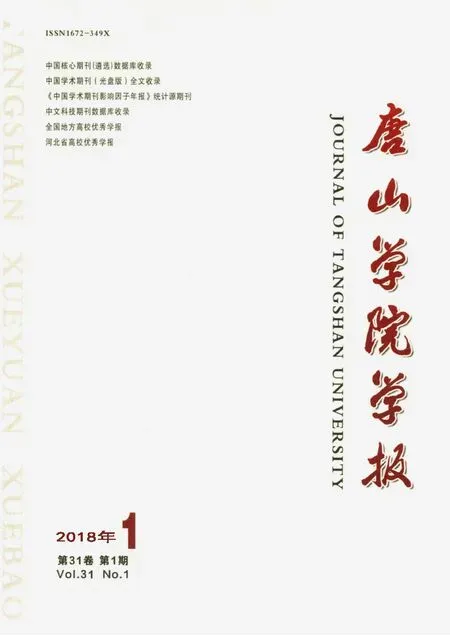全球化背景下英語非洲工人運動與民族國家認同
杭 聰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民族國家認同構建是英語非洲現代發展進程中的普遍性問題。工人群體的民族國家認同可被簡稱作“工人民族主義”。它的產生和變化持續受到西方主導下全球化的影響。20世紀非洲的全球化環境有兩次突出變化:一次是1950-1960年代殖民帝國體系瓦解,另一次是1980-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無條件市場體系(華盛頓共識)席卷而來。殖民帝國瓦解是由于民族矛盾讓非洲各族群、各階層人群凝聚在一起,工人民族主義初步形成;新自由主義市場體系席卷而來使階級矛盾削減了民族凝聚力,各族群和階層之間的矛盾激化,工人民族主義重構并得到升華。通過分析工人運動所反映出的民族國家認同變化,可以看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群體特殊利益與民族國家普遍訴求之間的分合關系,及國家制度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
學界既有的不多的研究與介紹忽視了全球化背景下工人運動和民族國家認同之間的關聯[1-2]。筆者的研究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一、殖民制度與工人民族主義的形成
國家因素在工人民族主義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恩格斯對國家的作用曾有過精辟闡述:“這種力量(國家)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之內。”[3]國家成為協調各種社會矛盾最主要的工具,國家因素滲透到生產過程、組織方式和意識形態塑造的方方面面。從國家制度的兩個層次來進行分析:一是一般性制度,如政治權力結構、民眾權利規定、強制力使用等;二是由一般性制度決定的勞動制度,如國家與工會關系的制度和勞工權利規定等。
秉持種族主義的原則,殖民制度將殖民地人口分為白人和非洲人兩個群體,實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工人問題被轉化作民族問題處理。白人享受各項政治權利和勞動權利。政治權力把持在白人殖民者手中,非洲人毫無政治權利,沒有任何勞動權利,更沒有集會、結社與提要求的權利。殖民主義作為西方主導下全球化的手段,慣用超經濟強制力處理經濟整合問題。非洲勞動力被強制動員進入商品農業和礦業生產,以及附屬的運輸業。直到戰后,非洲大陸上都廣泛存在著強迫勞動體制。在主要的殖民時期,即1885-1945年,非洲工人群體同其他社會群體的分化不明顯,非洲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人運動,也便不存在工會監管制度,自然不存在工人民族主義問題。
1945年后,殖民政府實行“文明勞工”政策,部分非洲工人被賦予準白人的身份,工人民族主義才真正發端。隨著白人優越論的破產、工人群體壯大,一部分非洲熟練工人逐漸被官方承認作為一個單獨的社會群體,被承認有組織工會的權利和其他的權利,這便是所謂的“文明勞工”政策。政策的實質是賦予這些被選出的能獲取穩定工資的工人以準白人工人地位。這種承認是半心半意的,因為英國政府在殖民地施行遠較本土嚴厲的工人政策。官方工人政策的核心概念是隔離。一是同非洲傳統文化隔離,以將非洲工人同非洲社會其他部分隔絕開來,成為有“效率”的工人。官方認為非洲社會不適應工業時代的要求,這是由“他(非洲工人)在許多工業技術上是無效率的,因為他出生、成長和本土文化的性質”[4]決定的;二是同民族主義政治隔離,或者退而求其次創造一個政治溫和的工人群體,作為合作者反對“傳統社會”培育出來的危險、落后的非洲大眾。這便需要加強對工會的監管,以便“避免不負責任的個人或群體為政治或非工業目的組織工會”*殖民地工人問題顧問委員會會議記錄,1949年4月21日,mss.292/932.5.1,轉引自Paul Kelemen,Modernising Colonialism: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and Africa,第231頁。。英國政府想通過殖民地工會,將工人培育成只專注于經濟利益,而不參與政治斗爭的“馴服合作者”。具體而言,殖民政府實行以下五個方面的政策。
第一是執行不同于英國本土的單獨工會法律,為政府保留更多的權力。殖民地工會立法將不執行英國早已簽署的《國際工人公約》(International Labour Conventions)中的規定。政府保留干預工會組織和運轉諸多方面的權限,諸如當選為工會管理層的人選、限制政府雇員自由參加工會、在工會立法中排除特定階層的工人、還有限制工會的合并與聯合*英國殖民部檔案:CO859/183/3,no.29,1951年7月26日,[工團主義問題]:殖民大臣格里菲斯(Griffiths)致各總督的通閱急件,見Ronald Hyam,edit.,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45-1951,London: HMSO,1992,第4冊,第369號文件。英國殖民部檔案:CO859/183/3,no.47,1951年10月,[工人關系]:殖民地工人部門領導人大會報告(殖民部,9月24日~10月5日),見Ronald Hyam,edit. The Labou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45-1951,第4冊,第370號文件。。種種限制顯示出英國政府并沒有將非洲人工會接納入體制的誠意。非洲工人自然同它離心離德。
第二是堅持“有色人種禁令”(Colour Bar),繼續將非洲勞工排除于大多數高級崗位和技術性工作之外。這代表了白人雇主和白人工人的利益。白人雇主極力主張非洲人勞動力僅能獲得臨時工性質的工資,以壓低整體工資。包括政府雇員在內的白人工人則希望盡可能多的占據高級和技術性的崗位。于是經濟問題和種族問題聯系起來,進而和政治問題聯系起來。這一禁令成為許多罷工的導火索,而罷工又成為全體非洲人反抗的引信。
第三是實行工會注冊制度。殖民政府對工會選舉和工會會費進行監督,限制工會參與政治活動。一是限定工會的領導層必須為工會所屬行業從業者,來制約當時的許多工會領導人同時也是民族獨立運動領導人的實際情況。二是規定工會基金不能用于政治活動,工會財務狀況要處于政府監管之下。實際上,工會運動同民族獨立運動的聯系并未被切斷。
第四是制約罷工權。一方面實行硬的一手,總督有權定義“基本服務”的范圍來限定罷工為非法。在1950年代,在坦噶尼喀有15個廣泛的基本服務大類被列出,在肯尼亞有13個,在尼亞薩蘭有10個。另一方面實行軟的一手,引入法定的工資確定體制(Fixing Salary System)和局部罷工權。這種半心半意的讓步并未能軟化工人們的立場。
第五是為本國工會同殖民地工會的聯系牽線搭橋,以培養殖民地工會的親英情感,搭建影響力渠道,破壞國際工人的團結。在殖民統治時期,許多懷有反歐和反英情緒的殖民地民族領導人,也不得不向英國職工大會(Trades Union Congress)*英國工人運動興起較早,起初按行業建立了各種工會組織,1868年進一步成立了全國性的統一組織——職工大會。和英國工會尋求有關工會組織管理問題的幫助*英國殖民部檔案:CO859/748,no.24,1954年7月19日,[殖民地勞資關系]:李特爾頓和英國職工大會和海外雇主聯合會于7月12日討論的殖民部記錄草稿,見David Goldsworthy,edit.,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London: HMSO,1994,第1冊,第504號文件。。這就為英國職工大會開展活動奠定了基礎。英國政府出臺專門文件建議英國職工大會,從民族獨立運動發展的形勢出發,優先在東非、中非建立聯系,同時維系西非已經建立的聯系,再兼顧加勒比和東南亞地區*英國殖民部檔案:CO859/752,no.8,1956年12月,[英國職工大會和殖民地工團主義]:12月10日英國職工大會代表會議殖民部記錄草稿,見David Goldsworthy,edi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1-1957,第1冊,第510號文件。。臨近統治結束時期,英國公司和雇主要求英國職工大會繼續保持和加納工會的既有聯系。因為工會聯系渠道是英國方面唯一能直接影響加納政府工人政策的渠道。當然,通過英國駐加納高級專員干涉加納政府的工人政策也是一條渠道,但這是一種極端的措施,只能用在對英國的終極利益形成主要威脅之時*英國殖民部檔案:CO859/1229,no.6,1958年10月7日,殖民地工人問題顧問委員會和緊急狀態地區事務的關系,見Ronald Hyam and Wm Roger Louis,eds.,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1957-1964,London: HMSO,2000,第2冊,第358號文件。。
由于政治權力把持在白人殖民者手中,工人沒有政治權利,對工人運動的武力鎮壓仍非鮮見。1949年東非聯合工會建立,但被拒絕注冊,因為政府擔憂東非聯合工會被一個顯然是共產主義鼓動者的印度人所領導。1950年,肯尼亞非洲工人聯合會和東非聯合工會領導人被逮捕,奈洛比的總罷工被武裝警察、軍隊和皇家空軍沖散。300名工人被逮捕,一些工會領導人被判處懲罰或監禁,理由是組織非法罷工。肯尼亞的事情并非孤例。1949年尼日利亞恩奴古(Enugu)的煤礦業罷工,23名罷工礦工被武裝警察射殺,超過100名礦工受傷。恩奴古的屠殺在殖民地工業史上并非沒有先例,卻成為民族反抗的最后導火索。
“文明勞工”并沒有被真正納入殖民地政治體制,卻由此促進了工人群體的同一性,更促進了民族統一的政治身份的形成和統一訴求對象的出現。享受組織工會權利的“文明勞工”只占工人群體不超過10%的比例,更多的是“流動勞工”。“流動勞工”占多數的狀況既是由殖民地原材料出口型經濟的特點所決定的,也是由于殖民官員們不愿意完全放棄利用鄉村部落組織的管理結構。該群體往往在農村有耕地,迫于生活壓力到城鎮提供廉價勞動力。有些人在農忙季節要返回農村耕作,有些人長期在城鎮居留從事簡單勞動但終究還是不得不回到農村,無論是哪種情況他們的工資都不足以養活整個家庭,甚至他們個人的生存也只能勉強維持*英國殖民部檔案:CO822/657,1952年11月11日,非洲人工資政策,轉引自Paul Kelemen,Modernising Colonialism: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and Africa,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34,Issue 2(May 2006),第224頁。。這部分勞工占多數的情況導致工人群體的利益往往和其他社會群體相混雜,易于彼此聯合。于是,“文明勞工”聯合了“流動勞工”、“流動勞工”聯合起其他社會群體,一致地反對殖民體制。
殖民政府半心半意的措施并未能實現其將工人群體同非洲其他社會群體隔離、同民族主義政治隔離的目標,反而激發了非洲工人的共同體意識,在階級層面上表現為工會的興起,在民族層面上表現為“工人民族主義”,他們將自己階級的命運和民族矛盾緊密聯系在一起,反抗殖民統治。受過西式教育的精英和西式廠礦中的工人將自己爭取權利的行動同爭取全民族解放的事業聯系起來,形成現代性全民群眾運動,使得爭取獨立的要求具備了現實基礎[5]。這便是英國將工人問題轉化為民族問題的結果。
二、新自由主義危害與工人民族主義重構
非洲各國獨立后,國家制度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發展。在一般性制度層面,非洲人自己掌握了政治權力,非洲工人獲得了選舉權,在政治法律層面獲得了權利保障。在勞動制度層面,國家工會納入體制之內,保障勞工權利。政府通過承認工人權利、保障工人福利來換取工人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如埃里·凱杜里所認為的那樣,當國家中的統治階級轉而信仰民族主義時,就很容易用這種學術設想來管理和影響國家[6]。總體上,政府處理工人運動的國家制度設計秉持民族團結的思維。同時,工人運動促成國家制度的調整。
在這種條件下,“工人民族主義”的內涵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由于殖民者被趕走,民族主義的凝聚力受到削弱,工人的階級意識得到增強。這是因為對于普通工人而言,他們仍舊處于權利遭忽視和廉價雇傭勞動力的地位。尼日利亞聯合工人大會(United Labour Congress)在1962年5月的一份政策文獻中說:“獨立日,1960年10月1日,使我們從殖民控制下解放出來。不幸地是,它沒有讓我們自主地從殖民體制中解放出來。特權的大廈仍舊保留,只是它的所有者不同了……聯合工人大會將繼續戰斗以反對階級對階級持續的剝削,就如它熱誠地戰斗反對帝國主義一樣。”[7]另一方面,反殖民時期形成的民族共識仍舊存在。如一名贊比亞年輕礦工所講:“獨立給礦業帶來很小的變化。即便是有(資產)國有化和(員工)贊比亞化,所有這些都是表面現象,因為白人控制每件事情。”[8]繼擺脫政治控制之后,擺脫西方經濟控制,獲取切實的經濟福利成為凝聚民族認同的共識。
在此種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政策極大地沖擊了工人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西方以債務脅迫非洲國家采取新自由主義思想主導下的以結構調整為中心的經濟改革,導致非洲陷入嚴重的發展危機。1986年非統組織峰會上,布基納法索前總統桑卡拉(Sankara)指出,“在這些債務的背后,實際上隱藏著一個‘新殖民主義’體系”,“當前,在帝國主義的控制和統攝下,外債成為殖民主義者精心設計的重新占領非洲的工具”[9]。非洲政府被迫削減公共開支,取消基本食物價格補貼和減少公共醫療支出,這對包括工人在內的中下層人群影響很大。新自由主義要求政府放開對國內產業部門的扶持,吸收大量就業人口的制造業和小規模農業不再受到扶持,直接加大了就業困難。國有企業私有化刺激了工人共同體意識。新時期共同反對私有化的經歷讓工人獲得相似的社會身份,維護了工人共同體意識。自然而然,許多社會運動都由工人罷工引發、由工會組織領導人發起。
面對此種局面,各國政府采取不同的措施,試圖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代表的外資利益和工人利益之間維持某種均衡,盡力爭取工人對政權合法性的認同。
為配合新自由主義政策,尼日利亞主要采取的是壓制工人要求的解決路徑。工人們的民族國家認同遭遇曲折。受新自由主義影響,1993年尼日利亞工人真實工資只有1983年工資的20%[10]。這種情況在整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具有普遍性。20世紀90年代,工會如非殖民化時代一樣再次成為積極的反體制力量。1993年拉各斯和其他大城市爆發大眾抗議,以求結束軍事統治和推舉民選政權。包括政府服務在內的公共服務、金融中心、燃氣站和大多數市場和工廠全部停止運轉。聯邦軍隊進入拉各斯恢復秩序,大約150人被射殺,同時數百人被政府安全部門(State Security Service)逮捕。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工人都走向街頭。到了1994年8月中旬,60%的工廠停工。軍人政府制定出限制工會的法律,用指定的領導人替換原來的領導人,但并未徹底取締工會、否認工人的權益。工會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地位要遠好于殖民時期。軍人政府提供了發展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所需要的秩序,能夠壓制住工人們的訴求。這是軍人政府能夠維持到1999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軍人政府缺乏工人們的認同也為民選政府登臺埋下伏筆。
在津巴布韋,工人運動促使新自由主義政策收縮。工人們的民族國家認同僅獲得暫時的鞏固。1996年的津巴布韋,先是公共服務聯合會、護士聯合會、教師聯合會、健康部門,從清潔工到醫生罷工,之后全國范圍內所有公共部門一天內全部罷工,選舉產生統一的罷工委員會。1990年代新一代工人成長起來,他們生長于城區受過教育,不同于他們有鄉村背景的父母。他們受新自由主義政策影響,只能找到合同工或臨時工崗位,工作穩定性沒有保障,因此他們成為罷工的主力軍。穆加貝總統不得不部分從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撤回到國家干預經濟的激進論調。從意識形態上講,執政黨日益采用反白人農場主的種族主義政策論調凝聚國家認同。政府試圖以此為基礎完成勞動力體制重構。然而不管是穆加貝還是他的反對者都沒有明確提出解決生產增長問題的方法。
新自由主義政策激化的社會矛盾,導致南非政權更迭,工會直接參與到政權中。工人們的民族國家認同感達到新高度。在非洲人國民大會黨和白人政府談判期間,工會發動了48小時的聲援罷工。為紀念索韋托事件12周年,南非工會大會發動了包含制造業70%雇工在內的大罷工。從1986-1990年間,罷工造成的工時損失超過了之前75年的總量[11]。正是在工會的支持下,1992年10月,以非國大為首的三方聯盟(包括非國大、南非工會大會和南非共產黨)接受同白人分享權力的策略,為重組國家、資本和勞動力的關系,重塑社會穩定提供了新框架。在這一框架下,1994年南非政權實現和平過渡,種族隔離制度瓦解。南非工會大會直接參政的結果之一是黑人家庭在種族隔離結束之后的頭十年里平均收入增加71%[12]。2006年,這一組織代表了65%的有組織工人,占所有工人數量的14%[13]。通過反對私有化、反對黑人內部不平等分配,構筑起工人運動新共同體意識基礎,作為平衡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新基礎,確保了南非民族國家的向心力。
工人階級中誕生出“非傳統民族主義”意識,階級獨立意識更為明顯。正式部門的工人又一次成為反體制的先鋒。非正式部門的勞動力由于生活問題、城市化問題或鄉村土地問題同正式部門的工人形成新共同體意識。殖民時期,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以殖民政府為化身直接掌握政治權力,在不發展狀態下以壓制本土工人權益為基礎處理勞資矛盾。工人以融入民族解放運動為斗爭形式,民族意識更為明顯。在后一時期,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更多以經濟手段逼迫當地政府犧牲發展權,放棄對工人權益的保障。工人以對政府化解渠道的疏離為斗爭形式,階級性得以彰顯。此時,非洲工人運動相比歷史上任何時期具有更大的獨立性和組織性。
另一方面,工人們的“非傳統民族主義”仍舊包含著民族國家認同。傳統、政治法律承認、社會福利照顧共同筑起工人民族主義的界限不被突破。共同的反殖民經歷、數十年居于共同民族國家內的經歷和西方壓力塑造的壓迫感構筑起民族共識的大框架,已形成工人民族主義的傳統。不管各政府或采取壓制、或采取妥協、或吸收工會進入政權,各政府都承認工人的政治法律權利、提供或多或少的福利。所以工人運動一直保持在體制之內,并且在重塑自身的同時塑造了國家制度。工人們的民族國家認同在挫折中增強。
三、結語
民族國家認同依靠民族主義來尋求同一性。同一性的獲取有兩個來源,一是外部民族的壓迫,二是民族內部協調。從歷史上看,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反而激發起英語非洲人民反全球化民族主義浪潮。正是西方資本促使不同的工人利益凝聚為一體,創造出工人共同體意識。該意識又同其他社會階層的訴求相結合形成民族共同體意識,反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分別表現為反殖民運動和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反對外來民族壓迫為民族主義構筑起共識的大框架。以包容性的民族政策為基礎的國家制度建設是維系民族主義的支柱。民族主義的維系需要將民族內部不同階級、階層的利益沖突融入到制度性框架,根據力量對比進行利益分享。獨立后的非洲人政府保障工人的政治法律地位并給予公共經濟福利,使得工人運動在捍衛自身利益的同時,終未突破民族共識的底線。非洲民族國家構建在曲折中前進。
[1] 唐同明.戰后英屬東非的工人運動[J].西亞非洲,1987(3):39-46.
[2] 利奧·蔡利格,克萊爾·塞魯蒂.貧民區、反抗與非洲工人階級[J].徐孝千,譯.國外理論動態,2008(6):23-28.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4] COOPER F.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the labour question in French and British Africa[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40.
[5] BOAHEN A Adu. Africa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Colonialism[M]. New York: Diasporic African Press,2011:63.
[6] 埃里·凱杜里.民族主義[M].張明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104-105.
[7] MELSON R. Nigerian politics and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64[M]//ROTBERG R I,MAZRUI A A. Protest and power in Black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776.
[8] BURAWOY M. 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belt[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2:74.
[9] ISMI A. Impoverishing a continent: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MF in Africa[R/OL]. Halifax Initiative Coalition Report,2004.[2016-11-11].http://www.halifaxinitiative.org/updir/ImpoverishingAContinent.pdf.
[10] ZEILIG L. Class struggle and resistance in Africa[M]. Chicago, Ill: Haymarket Books,2009:138.
[11] DWYER P, ZEILIG L. African Struggles today: social movements since independence[M].Chicago, IL: Haymarket Books,2012:108.
[12] 潘興明.南非:非洲大陸的領頭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02.
[13] MARAIS H. South Africa pushed to the limi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ange[M]. London: Zed Books,2011:445-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