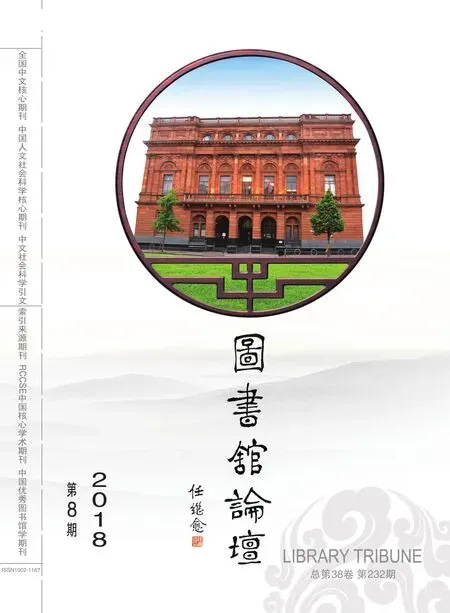文獻流傳史的完善與傳統閱讀價值的回歸
——評《中國閱讀通史》
國外閱讀史研究已經出現較為系統性的專著,如曼古埃爾的《閱讀史》(1996)、費希爾的《閱讀的歷史》(2009)、戴聯斌的《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2017)。關于中國人閱讀歷史的考察,一方面以資料集的形式散見各種史書、傳記、筆記和文論作品之中;另一方面,又與出版史、藏書史、圖書館史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閱讀通史》的編撰出版,將積累眾多的閱讀史料進行系統梳理,并與業已問世的出版、藏書、圖書館等通史著作形成呼應,完善了中國文獻流傳史體系。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閱讀通史》修撰所包含的精神寄托與文化傳承的理念,在閱讀和文化價值觀日趨多元化的今天,具有深遠的意義。
1 中國人閱讀的歷史研究
1.1 中國閱讀史研究框架的建立
梁啟超指出,撰寫新史是學界的迫切要求,史學的進步在于客觀資料的整理、主觀觀念的革新兩方面[1]。《中國閱讀通史》便是在編撰者長期關注閱讀史領域,并積累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的設想。主編王余光長期在圖書館學、出版學專業任教,長期圍繞“文獻的生產、收藏和傳播”進行思考。承載著人類文明的文獻典籍在悠久的歷史文化中如何被接受、使用和繼承,為文明的發展創造價值呢?這有賴于閱讀行為的存在。作為一位歷史文獻學學者,王余光在教學和科研實踐中,以文獻學的研究方法和眼光開掘閱讀文獻資料,逐步勾畫出中國閱讀史研究的新領域。1990年王余光教授與徐雁教授合作主編《中國讀書大辭典》(該書2016年出版修訂版,更名為《中國閱讀大辭典》)過程中,搜集了大量的中國閱讀史資料,包括“名人讀書錄”中的“名人讀書史跡”“名人讀書生活”,“讀書博聞錄”中的“中外讀書典故”等。1997年輯錄古人讀書事跡和掌故的《讀書四觀》出版,包括祁承的《讀書訓》、吳應箕的《讀書止觀錄》、陳夢雷的《讀書紀事》和周永年的《先正讀書訣》,編者做了注釋和翻譯工作,推動了先哲的閱讀理念和學習精神傳播。此后記錄中國近代名人讀書活動的叢書“中國名人讀書生涯”10種出版,對閱讀史中的個體閱讀活動進行了考察。此外,“讀好書文庫”(1999)、《中國讀者理想藏書》(1999)、“世紀閱讀文庫”(2001)等成果分別從經典閱讀、推薦書目、暢銷書等角度進一步豐富了閱讀史和閱讀文化的內容。加之一系列閱讀史和閱讀文化研究論文的發表,閱讀史研究的資料準備已逐漸完善,研究范圍初步形成。
2004年11月,《中國閱讀通史》編撰會議在北京大學召開,確定了《中國閱讀通史》的框架和主要內容,計劃分七卷出版,第一卷緒論,第二卷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第三卷隋唐宋五代,第四卷夏遼金元明,第五卷清代,第六卷民國,第七卷1949年至2000年。王余光教授提出《中國閱讀史撰寫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作為“緒論”,并作為中國各階段閱讀史論述的主要框架。《綱要》分八個問題,分別是“閱讀史研究的基礎”“理論研究”“社會環境與教育對閱讀的影響”“社會意識與宗教對閱讀的影響”“文本變遷與閱讀”“學術、知識體系與閱讀”“中國閱讀傳統”“個人閱讀史”。應該說,這是中國閱讀史研究的開創之舉,一方面奠定了閱讀史研究的理論框架,涉及外部環境和內部要素,為后續深入研究提供寶貴的視角;另一方面以著閱讀“通史”而非斷代史,對閱讀的起源、發展、轉折和復興的脈絡做了整體觀照,澤被后人。《中國閱讀通史》編撰跨度十余年,期間《綱要》做了調整,在定稿中“閱讀史研究的基礎”作為國內閱讀史研究的一部分并入“理論研究”;“文本變遷與閱讀”提前到第二章,說明在閱讀的發展過程中,文本的演變是活躍的影響因素;“個人閱讀史”的內容暫且不表,這方面的案例和資料非常多,全部納入進來內容過于龐大,可以作為后續的專題研究。最終稿擴展為十卷,時間跨度從先秦到民國,并增加第十卷“圖錄與索引”,提供直觀的文本和閱讀的相關圖片,豐富資料內容。下文從社會閱讀的理論體系和中國閱讀史的分期兩個角度具體揭示《中國閱讀通史》的編寫主旨。
1.2 閱讀史和閱讀文化理論體系的確立
閱讀史是一門交叉學科,本質上屬于歷史學,但又涉及社會學、文化學、文學批評學等領域。閱讀史與閱讀文化密不可分。讀者與文本是閱讀研究的兩個要素,閱讀是讀者與文本相互影響的過程,是閱讀主體(讀者)實踐活動與精神活動的一種體現。錢穆認為“文化”是指“群體”的人生[2],閱讀文化則是“閱讀群體”的人生。梁漱溟將文化分為“精神生活”“社會生活”“物質生活”三個方面,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閱讀通史》將閱讀文化的相關內容納入進來,根據“文本”與“讀者”兩個要素,從社會環境和精神活動兩個方面確立了閱讀史和閱讀文化理論體系。
《中國閱讀通史》“理論卷”確立了閱讀史和閱讀文化的理論體系。首先,第一章“閱讀文化和閱讀史”的總論部分從民族性、時代性、區域性等空間和時間維度構建閱讀文化的理論內涵。其次,關于“文本”要素,第二章“文本變遷與閱讀”探討了不同視角下文本的概念,以及文本載體的變化對閱讀的影響;第五章“學術變遷與閱讀”從知識體系流變、文本闡釋、工具書等角度分析了文本內容的變遷和接受對閱讀的影響。再次,社會環境方面,第三章、第四章、第七章分別從閱讀的經濟基礎、出版業、圖書館事業等行業保障,家庭與教育,影響閱讀的政治意識、群體意識、宗教信仰等以及閱讀傳統、方法、精神的繼承和延續等角度進行分析。最后,關于“讀者”要素,第四章中的“群體意識與閱讀”分析了讀者群體的特點、行為特征和影響機制;第六章“文人生活與閱讀”探究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群體的閱讀特征、審美情趣和文化價值觀。值得說明的是,讀者群體類型多樣,閱讀需求也不同,可以在后續研究中進行兒童閱讀史、女性閱讀史、老年人閱讀史等閱讀的專題史研究,以填補空白。
1.3 閱讀史的分期
從廣義上講,閱讀行為在文字出現之前就已經存在,由于“文本”的概念長期以來是指以書籍為主的紙質文獻,因此文字的產生、書籍的出現開啟了中國閱讀史的篇章,也不可避免地與書籍史、出版史、藏書史、圖書館史相照應。不同時代的社會環境決定了文本的形制和內容,決定了讀者群體和閱讀風尚,后兩者又反作用于社會環境,閱讀環境和閱讀要素在不斷前進的歷史車輪中相互作用,造就了承前啟后、環環相扣的閱讀生態。《中國閱讀通史》按朝代分為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遼西夏金、元、明、清(上、下)、民國。從“文本”和“讀者”兩個閱讀要素出發,結合《中國閱讀通史》的時代劃分,筆者認為中國閱讀史的分期可以歸納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文本生產力偏低,讀者群體集中在貴族階層;第二階段是隋唐五代到兩宋,印刷術普遍使用提高了文本生產力,科舉制度的施行擴大了讀者群體;第三階段是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新思潮,文本創作日趨活躍,讀者群體多元化發展;第四階段是民國時期,新出版業的誕生、新圖書館運動的開展,為文本生產、收藏和利用開啟了新時代,閱讀權利得以保障。
2 《中國閱讀通史》的出版意義
2.1 完善了生產、收藏和利用的文獻流傳史體系
在和“書”有關的歷史研究中,出版史、藏書史、圖書館史都因研究對象相對客觀而有利于研究的開展,而閱讀是“一個思想與認知的過程”,閱讀史是一部人與文本互動的歷史,是一部文本的接受史。這種“接受”一方面由于個人閱讀感受又千差萬別難以窮盡;另一方面也由于人腦信息的難以采集而令研究者望而卻步。因此,《中國閱讀通史》編撰規劃的提出是一種挑戰,也是適應時代需要、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該書“緒論”中提到了編寫初衷[3]:“中國是一個史學發達的國度。傳統史學如正史、編年史高度發展,而專門史、專題史發育不良。近百年間,受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專門史得到很快的發展,大多齊備。二十世紀后期,圖書文化史的研究,受到學界的重視。圖書文化史中的三大支柱出版史、藏書史、閱讀史,研究成果逐步增多。在本世紀初,中國出版史與藏書史,均有通史出版,但閱讀史的研究相對薄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在歐美的一些大學中,已開設閱讀史的課程,并開展相關研究。有幾千年閱讀歷史的中國,還沒有加以系統的敘述與總結,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緒論”提到的藏書通史和出版通史,分別是指2001年由寧波出版社出版的《中國藏書通史》(上下冊)和2008年由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出版通史》(九卷本)。而在《中國閱讀通史》即將殺青的同時,《中國圖書館史》也于2016年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這些研究成果圍繞圖書的生命周期及社會化歷程,從生產、收藏、傳播和使用的不同角度入手,共同構成了一部完整的文獻流傳史,為相關學科領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個考察“書文化”史的一個全面的視角。《中國閱讀通史》的問世從某種程度上形成了對以往研究內容的一種反饋,出版史、藏書史和圖書館史的考察對象主要是“文本”,閱讀史的考察對象是“文本”與“讀者”及其互動過程,尤其關注讀者在獲取文本載體、閱讀文本內容和接受文本思想過程中的影響因素和心理狀態,以及由此形成的閱讀方法和文化傳統。這也是《中國閱讀通史》的問世和構建完整文獻流傳史體系的學術價值。
2.2 總結了中國的閱讀理論、方法和傳統
歷史研究的目的是“以史為鑒”,當代的社會實踐能夠從中吸取有用的經驗。中華民族長期以來保持著良好的閱讀習慣,歷史上涌現出了許多勤學苦讀的事跡,也總結出了獨具特色的閱讀方法。進入信息時代,人們閱讀的內容和方式越來越多元化,但能夠獲取的知識和有用信息卻越來越少。在全社會號召建設書香社會,呼吁閱讀價值回歸之時,公共圖書館等閱讀推廣機構究竟應該如何開展閱讀推廣服務?古人的經驗和方法能夠給予啟示。
《中國閱讀通史》各卷中有專門探討閱讀理論、閱讀方法和閱讀傳統的章節,將其摘錄出來便能夠成為獨立的閱讀學史和閱讀文化史。《中國閱讀通史》認為中國漢文閱讀學產生于先秦時期,表現為經典闡釋學,從學術上看經學的出現標志著閱讀學的開始[4]。漢代知識體系的形成使讀者突破原有的閱讀限制,實現了自主性閱讀。魏晉南北朝時期閱讀理論與方法逐漸形成,出現了閱讀知音論、閱讀滋味說、閱讀功能論等相關理論和讀書法,推薦書目初見端倪。隋唐兩宋以降,出現中國傳統文化發展鼎盛時期,印刷術的發明和科舉制度的推行開啟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盛世閱讀風尚,系統閱讀理論誕生,讀書方法百花齊放,名人閱讀事跡層出不窮,其中朱熹對讀書理論和讀書方法進行的系統研究,總結為“朱子讀書法”。明清、民國時期,讀書理論和方法更加豐富,讀書名家閱讀方法為私人閱讀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女性閱讀與大眾閱讀等群體性閱讀特征顯現。而民國進入傳統和現代的閱讀轉型時期,傳統經典的選擇和推薦書目成為閱讀領域繼往開來的焦點。《中國閱讀通史》中的閱讀理論、方法和傳統能為當代的閱讀推廣和書香社會建設提供理論依據和經驗借鑒,值得相關人員學習和應用。
3 全民閱讀時代傳統閱讀的價值回歸
3.1 文化軟實力建設需要以史為鑒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的重要部署,文化自信的重要性達到新的高度,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是重要的國家發展戰略,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增強文化軟實力和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加強文化軟實力建設應充分借鑒歷史經驗,在重視優秀文獻收集整理工作的同時還應加以宣傳推廣,既要有廣博厚重的內容,又要有因時制宜的推廣方式。我國歷朝無論是官府還是民間,皆有重視修書的傳統,繼而有書目作為大規模修書的“衍生品”,當然也會相對純粹地編撰一些引導學子及世人讀書的推薦書目。這其中固然有統治者加強集權的因素,但客觀上也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歷史文獻——優秀傳統文化的載體。因此,現今要增強文化軟實力,一方面應加強優秀文化的整理和編撰,并以豐富的形式出版發行,以滿足多樣化的需求,如紙質圖書、電子圖書、聽書、數據庫;另一方面,要以適當的手段和方式加以推廣,如制定推薦書目、提倡家庭藏書、宣揚親子共讀等,推進優秀傳統文化進校園、進家庭、進社區。促進和提升全民閱讀是文化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黨和政府對文化建設的重視對推進全民閱讀、構建書香社會而言也是一重要歷史契機,推進全民閱讀應綜合考慮出版、藏書和閱讀等三方面的因素,文獻資源的生產、傳播和使用三位一體,應是高質量的內容生產、便捷高效的傳播途徑和個性化的內容消費。
3.2 傳統閱讀內容和方法是閱讀史研究的意義所在
網絡時代,文獻資源迅猛增長,獲取手段便捷,在提供便利的同時卻容易讓人們經常陷入信息迷失的狀態,就如網絡搜索引擎的使用一般,點擊檢索按鈕后返回的結果往往會成千上萬,使用者如果沒有豐富的經驗和科學的訓練,想必是很難知曉哪一條是其想要的結果。這就如同萊辛說過的,一本大書就是一樁大罪。所以讀什么,怎么讀是需要指導的。閱讀是一種個性化的行為,讀者的性格、家庭、教育、所處的環境都對其選擇文獻資源產生影響,但閱讀在一定的時代又具有共性,即時代性,受政治制度、閱讀內容、傳播方式、教育理念等因素的制約。閱讀史的研究旨在為社會提供優秀的閱讀內容和適合的閱讀方法。傳統閱讀內容應是經過歷史長期傳播被普遍接受的經典著作,閱讀經典對提升人文素養和塑造個人精神具有重要的意義,是跨越時空的界限與作者的交流與共鳴,讀書應該讀經典好書。人的一生不可能讀完所有的書,因此要閱讀和體悟經典就需要一定的方法,《中國閱讀通史》中提到“讀思結合、讀習結合、讀行結合”就是一種重要的讀書方法,速讀、精讀、熟讀、抄讀等傳統的閱讀方法都是在不同環境下可采取的閱讀方式。
3.3 全民閱讀的進步和發展需要立足傳統
推進全民閱讀已成為各界共識,政府高度重視,已連續5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為持續深入開展全民閱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全民閱讀促進條例(征求意見稿)》《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公共圖書館法》實施,全民閱讀正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美好發展時期,有著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每年“兩會”期間也有關于設立全國閱讀節(日)的提案,且各地政府部門也越來越重視全民閱讀,每年在“4·23世界讀書日”前后都會舉辦形式多樣的閱讀活動,以倡導全民閱讀。圖書館界更是不遺余力地宣傳全民閱讀,引導民眾走進圖書館,全民閱讀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不過,不少的閱讀推廣活動關注點還停留在數字記錄層面,而忽略了閱讀的內在價值和精神。因此,提倡和推進全民閱讀,更應注重閱讀效果,如《中國閱讀通史》提到應明確“志”與“趣”,以明了閱讀的方向與動力。《中國閱讀通史》講到古人的讀書情懷對當下的閱讀推廣工作也有積極的借鑒意義,文本尊重情結不正是告訴讀者要珍惜書本和敬畏知識嗎?精心構建閱讀環境不正是時下流行的閱讀空間構建嗎?所以,傳統的閱讀價值、閱讀精神、閱讀情懷對目前的全民閱讀具有重要的價值,應加以弘揚和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