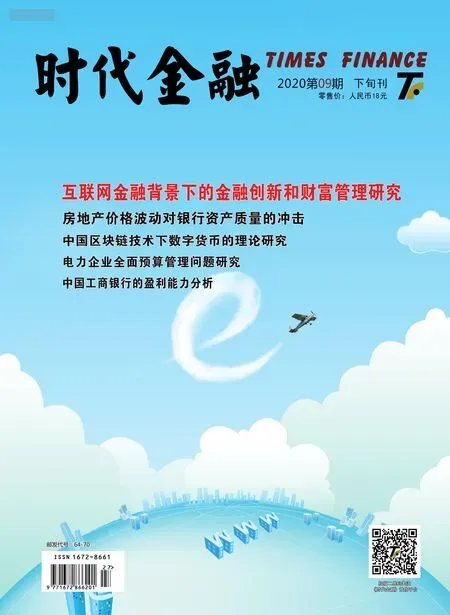醫療數據導向糾葛的產業模型之困
——兼論醫療產業收入分配模型的系統整合
王 斐
(無錫和美婦產醫院有限公司,江蘇 無錫 214101)
有人問歐美國家的醫生是否有職業保護?有,也沒有。
歐美國家醫生的沒有保護,體現在治愈率考核的層面;而中國醫生沒有職業保護,則是因為考核“聚焦”的點并不在治愈率。
現在國內的醫療體制,一言以蔽之:不考核治愈率,偏重產業化。在這種制度下,各自為陣、單兵作戰、散兵游勇的現象嚴重,因為大家都需要完成考核。藥占比、耗占比、床位周轉率……以及各種必須完成的,與工資獎金掛鉤的指標,這都是醫生必須遵守且完成的“硬杠杠”。
舉例來說,醫生為了把病人的病看好,藥物開了超大劑量,那么中國的患者就會對醫生充滿懷疑。然而類似情況若發生在歐美國家,則是另一番圖景。為了治好患者的病,醫生多大劑量都敢開。因為劑量不到位就治不好病,沒有治愈率。而治愈率又綁定著醫生的薪酬。所以,醫生的利益其實是和患者的利益綁定在一起的。歐美國家的家屬呢?他們在治愈率考核的體制之下,知道醫生不開這么大劑量,治不好病飯碗就砸了。在這樣的前提下,一方面是為了自己能治好病,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對這種形式的“利益綁定”的理解,因此,歐美國家的患者們普遍都很配合。
毋庸諱言,中國的大眾對國內公立醫療體制的信任度并不樂觀。在很多患者看來,醫生給患者開這么多藥,大多是為了藥代及藥品回扣,甚至是為了工作量考核。因為患者也清楚,國內的公立醫療體制,并不對治愈率進行切實的硬性考核;故而既然醫療體制不管患者死活,患者又何必信任?而作為醫生呢?即便是想給患者治好病的“良心醫生”,他們既難得到患者的理解,更難得到體制的寬容。醫療體制沒有治愈率考核,只有藥占比、耗占比考核,大家都在“演繹數據”,你想給人家治好病,別人不想、患者不信、體制不允許……
由此說到歐美國家醫生的薪酬,他們的薪酬為什么高得離譜?而且歐美國家的醫生,其家屬待遇也近乎等同于中國的軍殘烈屬。這一切的“豐厚回報”,都是有前提的。
有一年,瑞典有幾個地方的行政當局,說要給醫生把工資調低,因為醫生的工資高的太離譜了。結果此言一出,第二天全城滿街都是游行的人。老百姓說,你們要調低醫生工資,我們就用選票干掉你們。因為高薪的醫生有高治愈率考核,低薪醫生,你拿什么資本去考核他們的治愈率?市長說財政負擔不起,市民說我們可以多交稅。結果市長還是不同意,三天之后,議會選舉,市長換人。
國外乃至未來中國的醫療制度:一切以治愈率主導。那么,也就是財政主導醫療,而不是老百姓的錢主導醫療。用百姓的高稅負,讓官方為醫療體制進行財政“背書”,醫療才有可能不在高收費、高稅負、高藥價等“多高”的條件下運作。稅收、財政體制,決定了醫療體制的整個體制模型。
國外的醫療:全民免費,全民收稅,全民間接財政供給。因此,醫療考核治愈率,醫患之間有信任,患者也不會去傷醫。
中國有著自身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國情,財政必須要用于更加重要的國防、軍費及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由此造成了公共衛生支出財政支撐相對較少的情況。對患者而言,他們不僅要交稅,還要自己掏錢供養醫療;對醫療而言,由于財政畢竟不能負擔全部的醫療開支,因此醫療體制本身也需要高度的產業化來自給自足,以滿足醫生最起碼的薪資及行業、體制利潤的需求。在這種體制下,患者就醫,醫生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在“滿足考核指標”(不扣錢或少扣錢)的前提下給自己帶來利潤,而不是首先考慮患者的利益,所以患者不信任醫生,也可以理解。雙方不信任,醫患矛盾,不僅有傷醫事件,醫生的“傷患”事件,也時有發生。
譬如用藥:
歐美醫療體制下,家屬思維:醫生用這么大劑量,他們考核治愈率,副作用他們也要負責。因為我們交了稅、出了錢,讓政府給他們發高薪,他們同等薪酬同等責任,因此,就算出了事,政府會找醫生,進而幫患者把事情搞定,患者用不著那么煩。通常情況下,醫生也不會出事,因為醫生自己的利益與患者利益是相輔相成的。
中國體制下,家屬思維:醫生自己都吃不飽,這么大劑量,是不是有別的什么目的?我們掏錢看病,他們賺不該賺的錢,財政支出也相當有限,治愈率考核我們就沒聽說過,醫生居然管治愈率?這怎么可能?錢是我們自己掏的,醫生也不管我們治愈率,那就只有我們自己用自己的方式管了。
其實,表面上看,的確中國醫生對患者有做得不對的地方,“醫患矛盾尖銳”,醫生群體本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究其根本;醫療的產業模型的基礎缺陷,乃是題中應有之義。醫生的錢與政府制定的考核指標掛鉤。治愈率不考核,而是考核藥占比、耗占比、床位周轉率,除此之外還有抗生素使用率、平均處方金額……那一條條的緊箍咒。既然如此,醫生便但求無過。患者是否能治好,那是不需要考核的;反正每個病患,所考核的都只是過程數據,不看結果,那對于醫生而言,最好的方法,便是按規定用藥“施治”。結果如何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按規定辦事了。順便,如果能多開點藥,藥代那邊,還能給我點回扣。本來工資就低,再不從藥代那兒填補一些缺口,醫生們難道要回家喝風?
一言以蔽之:財政直接支持、全民稅收的間接支持,以及考察過程(形式主義)還是考察結果(唯結果論),構成了中國現行醫療利益模型與歐美發達國家醫療利益模型的根本差異。
為什么中國的醫療職業保護法到現在都沒出來?按人大的立法速度,這種法律如果是真正的出于公心,那幾個傷醫事件出來之后,早就該落地了。為什么沒出?關鍵是決策層對中國醫療體制現實存在的問題認知的非常清晰。他們知道醫患糾紛的根本問題在哪里;若是貿然出臺這個法案,反而會在客觀上加劇醫患矛盾。患者本就在這個體制下,對醫生不信任;你再把醫生搞得碰也碰不得,高聲說話都是有危險的,那患者就不去醫院好了。“小病自己診斷,大病自己了斷,不給祖國添亂”,如此,醫院還如何生存?
而且,這個法律一旦落地,便會出現一個違法行為認定寬幅的彈性風險。舉個例子:在某個小縣城里,如果作為縣醫院醫生的前女友想給作為患者的前男友找點麻煩,那么這位醫生女士便可給本院的醫生同事說一聲,致使前男友來看病的時候,被故意刁難、直至激化矛盾;前男友只要一發火,便是違法,直接行政拘留15天……想想吧,那樣的醫院,誰還敢去?
醫院現在這樣的利益鏈模型,再配上一個這樣的醫生職業保護法;那么醫生,就會成為活著的“特權群體”;相對存在缺陷的利益鏈條,就會被“依法”掩蓋起來。患者當然不是傻子,他們可以選擇不去醫院看病,可以“用腳投票”。到時候,去醫院要拿出進局子的勇氣;把醫生惹毛了,本來今天是來開藥的,結果今天變成了來自找行政拘留甚至自找判刑的。那么,患者出于安全考慮,就算有點小毛小病,還有必要來醫院嗎?
在現行體制下,醫生本就不管是否治愈;患者找醫生看病,只是聽聽專業意見,找點專業設備、專業人員,不說能看好,至少減緩向壞發展的速度。若是醫生在這樣的利益分配模型下,又有了職業保護法的“加持”,那么醫生便可跟著藥代一起為所欲為。患者當然理解醫生,醫生薪酬普遍不合理,醫院自身收入分配模型倒置;那么,底下的醫生,不靠藥代靠什么活命?醫生不管患者死活,因為藥占比、耗占比、床位周轉率在上面壓著;對此,患者當然明白。在這種體系下,患者渴望良心醫生,但當良心醫生出現在眼前,患者又不相信這是良心醫生。“怎么可能?良心醫生怎么可能被我碰到?我買彩票從沒中過獎,這不可能。”因此,患者對真正的良心醫生,也是充滿狐疑的。患者不懂醫,他們不能分辨醫生良莠。除非你一劑藥下去,他們藥到病除,而且跟他們“咬耳朵”:“我要這么快給你治好了,對上面不好交代啊……你千萬別說出去啊!”這樣,患者才信你。
如果職業保護法落地,那么患者就連聽專業意見也都可以省略了。患者到醫院來,是尋求專業援助的,根本就沒指望看好;這下可好,別弄得專業援助沒搞到,把自己給搞進局子里去了。
換言之,如果要激活民營醫療,那醫療職業保護法是最好的“催化劑”。公立醫院,說錯話、態度不好有罪,我不敢去,那我就去相對寬松的民營醫院。畢竟惹不起,我躲得起。
然而現在看來,官方大的方針,并非把人往醫院外面趕,而是把人往醫院里面趕。藥房禁售處方藥、嚴格監管民營醫療、嚴管民間偏方、打擊民間自主醫藥……這些政策行為,都是為了保證醫療體制的核心利益。因此,這個保護法案暫時不應該貿然出臺。現行的公立醫療體制,本就是一個眾人皆知且大家都有切身感受的有待從根本上改變、創新的體制;在它改變、改革之前,你讓大家盡最大可能選擇相信并使用這個體制的副產品還來不及;現在非要立法去把人往外趕,讓人遠離這個體制,這并非明智之舉。
比起醫療職業保護法,現在更加重要的,乃是對于醫療利益模型乃至相適應之考核導向的根本調整。在產業化聚焦的基礎上,應當引導醫療體制模式向治愈率聚焦。這并不意味著患者進了醫院,就一定能治好病;而是意味著醫療機構側重于考核醫生所接診患者的治愈效果、癥狀殘留、用藥合理性及相關成因,從而評估療效及本級醫生、本級機構對于相關病癥的最大治愈限度。適當弱化過程考核,強化結果考核。“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貓”,這樣,配合“兩票制”的藥品銷售模型,既能保障患者利益,也能保障醫生利益,更能保障藥品-器械生產-銷售渠道的利益。在這個基礎上,大幅提高醫生的薪酬,使得醫生薪酬達到相對較高的水平,讓醫生“有恒產”,進而“有恒心”。
財政應當適度加大對醫療行業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對公立醫療體制的資金支持。中央層面,在保證其他更重要的財政開支能夠正常運轉的情況下,可通過增加稅收的形式,提高醫療經費在財政預算中的比例;當然,亦可直接提高相應比例。另外,地方省、市兩級財政,可在削減其他不必要開支的基礎上,將更多的財力、精力向醫療領域聚焦,從而最大限度地支持醫療領域的科研、人資、設備乃至藥品更新迭代等切實工作。中央、省、市三級財政,應當適當降低甚至取消藥品附加稅負,從而促使財政自身醫療支出成本的降低,乃至促成醫療、藥品及器械機構整體價格的下調。進而為醫藥成本/利潤的性價比最大化,奠定良好的基礎。
中國需要好的醫生,更需要好的醫療體制;好的醫療體制,來源于對醫療收入分配模型的精準調控。找準并正視現實所存在的要點、難點,敢于擔當、狠抓落實,這樣,才能使得中國的醫療產業乃至相關行業,在這個偉大的新時代,取得新的成績,進而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向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