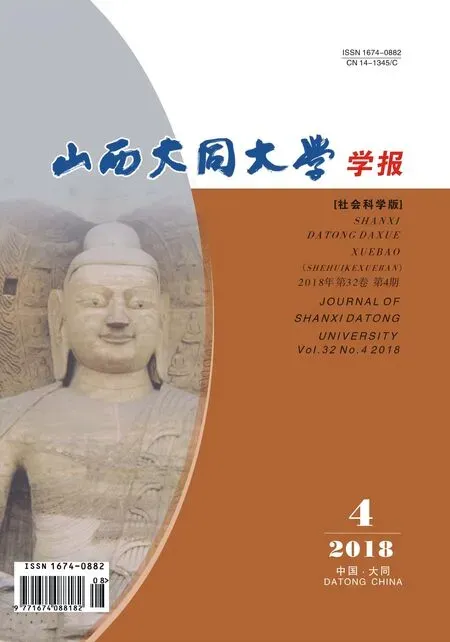王安憶小說中“空間”的意義
崔佳琪,謝 納
(遼寧大學文學院,遼寧 沈陽 110136)
人類自誕生之日起便變生活在特定的時空之中,時間和空間對于人類而言有著同等重要的作用。小說是人類如實或虛構書寫某一固有時空故事的文本,小說在時間和空間相交叉的坐標中產生,同時也記錄著時間和空間中發生的種種奇聞異事。正如讓·伊芙·塔迪埃所言:“小說既是空間結構也是時間結構。說它是空間結構是因為在它展開的書頁中出現了在我們的目光下靜止不動的形式的組織和體系;說它是時間結構是因為不存在瞬間閱讀,因為一生的經歷總是在時間中展開的。”[1](P224)由此可見,只有同時考察小說中空間和時間這兩個要素,才能實現對小說文本全面且透徹的了解。但是大多數小說創作者和文學批評者卻更注重小說和時間之間的關系,注重以時間為主線探究小說創作動機、情節進程和人物形象,而忽略空間在小說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空間(位置)和時間在應用時總是一道出現的。世界上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空間坐標X、Y、Z和時間坐標T來確定。”[2](P251)因此,在進行文學作品鑒賞和批評時將關注的視角放在文本中存在的“空間”上,我們才能獲得對相關作者和作品的全新闡釋。
王安憶的小說文本中包含著諸多具有鮮明特色的空間,如“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弄堂(《長恨歌》)、“寧靜”“文雅”“閑適”的城市蚌埠(《蚌埠》)、“是天生麗質,也是歷代文人騷客的艷情裝點”的杭州(《杭州》)等等。王安憶小說創作過程中不惜筆墨以瑣碎細致的筆觸刻畫空間,顯然可見她對小說中空間的重視。王安憶將自己親身接觸過的物理空間視為寫作經驗的源泉,這些對王安憶產生重要影響的空間不僅激發了王安憶的創作動機,而且經由王安憶精巧敘述后的空間,還具有塑造人物形象、推進情節演進的重要作用。
一、“存在空間”激發創作動機
小說作者在創作時不僅需要擁有非常高超且熟練的寫作技巧,同時也應該具備新奇豐富的寫作素材。作者只有掌握大量的生活經驗和人生閱歷,才能夠將諸多情感體悟融入小說文本中,進而促使小說文本因充沛的真情實感而打動讀者。作家成長過程中經歷的生活環境,無疑是作家積累和獲取經驗的重要場所。其實在許多作家文本中,我們都可以找到他們生活過的空間,如威廉·福克納筆下的“杰弗生鎮”、馬塞爾·普魯斯特筆下的“貢布雷”、沈從文筆下的“湘西”、王安憶筆下的“上海弄堂”等,這些空間都是作家內心深處的“存在空間”。諾伯格·舒爾茲在《存在·空間·建筑》一書中提出了“存在空間”的概念,他指出“存在空間”是我們非常熟悉,并注入了情感的空間。龍迪勇認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對故鄉這一特殊空間(存在空間)的追憶和重構,是促使作家進行創作的內在動力。”[3](P30)
王安憶筆下空間眾多,就連廚房、車廂、舞臺、化妝間等狹小地域也可成為她作品中的景觀,但若總覽王安憶小說作品,則會發現她描述最多的空間還是繁榮但腐朽的上海、陰暗且燥熱的弄堂以及樸實簡單的鄉村。王安憶對這些空間著墨頗多,無非是由于這些地方作為王安憶長期居住和生活過的場所,它們早已化作作者內心深處的“存在空間”。作者在這類空間中曾有過的喜怒哀樂等諸種情緒,不斷激發起作者對此類空間及空間中所發生事件的敘述欲望。
以王安憶成長其中且多次描寫的空間——上海為例,王安憶筆下的上海并不像海派文人描寫的上海那樣充滿狂歡色彩。在王安憶看來,上海的繁華不過是表面想象,只有上海的弄堂才最能體現上海的本質。因此,描寫弄堂這一“存在空間”中的種種人情事態,便成為激發作家創作的動機。如《鳩雀一戰》展現了弄堂中的保姆小妹阿姨為爭奪自己的容身住處而做的種種努力;《角落》描寫的是弄堂街角的“布店”在時間流逝過程中的變遷;《后窗》是對狹弄里“過去的日子和過去的面容”的追憶和沉思。這一類小說對于上海弄堂的全面展示,傳達出作者對弄堂這一“存在空間”的情感投入,反之也正是由于作者對弄堂豐富的情感體驗,才促成了這些小說的問世。了解王安憶成長歷程的讀者都應知道,她不僅對上海有著敏銳的感受能力,作者年輕時插隊下鄉的經歷,使質樸自然的鄉村也成為王安憶心中的“存在空間”,因此作者對鄉村生活的回望和重構,便成為《稻香樓》、《招工》、《喜宴》等小說的創作動機。
王安憶對內心“存在空間”的挖掘,使她的小說呈現出鮮明的地域色彩。上海弄堂里的瑣碎和晦暗,激發作者探測弄堂中人們生存狀態的欲望;鄉村生活中的簡單恬淡,引起作者對過往插隊鄉村的回首。這些“存在空間”不僅僅是作家建構小說的素材,同時也是促使作家進行小說建構的重要因素。
二、借空間變化推動敘事進程
任何一部優秀小說的創作都不能離開時間、地點、人物、情節等要素,凡是有吸引力的小說文本,其情節中和敘事進程相關的起因、經過、高潮、結尾都應經過作家精心的布局。王安憶暢談小說創作經驗時提出:“作為一個小說家,故事就是他的生命線。”[4](P397)而一個故事若想扣人心弦必須有引人入勝的情節和巧妙的敘事節奏做支撐。推動小說敘事進程的藝術手法多種多樣,既可以以時間為主線順勢安排故事進程,也可以通過人物性格的變化引領敘事的走向,而王安憶進行小說創作時,則是另辟蹊徑的以空間變化作為推動敘事進程的重要方法。
在時間流逝過程中展示故事發展經過是許多作家會選擇的創作方法,其實描寫小說的敘事進程不僅僅只有時間這一個支點,“在許多小說中,尤其是現代小說中,空間元素具有重要的敘事功能。小說家們不僅僅把空間看做故事發生的地點和敘事必不可少的場景,而是利用空間來表現時間,利用空間來安排小說的結構,甚至利用空間來推動整個敘事進程。”[3](P40)
王安憶的許多小說通過空間的轉移推動敘事向前發展,這類小說中人物的性格、人際的摩擦、故事的緣由等都是隨空間的變化而變化。如長篇小說《紀實與虛構》,小說開篇便引入作者對當下生活的空間體驗:“我們在上海這城市里,就像是個外來戶”,因此探究“我們”在“上海”這一空間中孤獨感、陌生感的緣由,便成為作者開始“紀實與虛構”的出發點。小說以“我”祖先從“遙遠的漠北草原”到“我母親的江南家鄉”這一段空間上遷移的經歷為主線貫穿全篇,作者將“我”祖先在不斷征戰過程中空間上的變化作為推進情節向前運作的敘事節點,她以空間轉移進行小說脈絡建構的寫作手法創作出《紀實與虛構》這部長篇小說。
又如短篇小說《姊妹行》中的空間要素也對敘事進程具有重要意義,小說開篇,作者指出主人公“分田”和“水”出城的正確路線應該是韓集—大王集—曹城—商丘—徐州,但在接下來的敘事中,作者卻借主人公“分田”和“水”從“徐州”誤闖入“徐州西”引起的空間變化,推動小說情節發生轉向。兩位主人公陰差陽錯地在“徐州西”被販賣到不同的村莊,于是作者又依據兩位主人公在空間上的隔離展開余下敘事,即“分田”從村莊逃出后,為救出伙伴“水”而再度重走二人進程的路線,歷經波折終于救出“水”后,果敢堅定的二人最終如愿到達“徐州”,至此故事結束。王安憶在這篇小說中以人物在不同空間的轉移作為敘事主線,表現出作者通過利用小說中空間變化推動敘事進程的寫作意識。
客觀呈現出作品人物在不同空間中的游走,詳盡敘述作品人物在不同空間中經歷的悲歡離合,并以空間作為小說的主線,以空間上的變化作為故事發生轉移的契機,是王安憶在小說創作時自覺選取的寫作手法。王安憶對于空間要素在推動敘事進程作用上的投入性關注和創作實踐,豐富了小說寫作手法,也使自己的小說文本增添了一個全新的闡釋角度。
三、以明暗空間對比達成敘事目的
中國古代建筑往往以屏風作為劃分空間的工具,經由屏風劃分后的空間往往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受中國古代建筑的影響,中國古代小說中也常常可見借助屏風的分隔性作用展示人物心理、輔助故事敘述的寫作技法。如古代小說中就存在許多描寫深閨中的小姐在屏風前后對心儀男子的不同表現,屏風前的世界象征的是公共空間,在公共空間中,閨中小姐往往遵從禮教,表現出應有的矜持和柔婉,而屏風后的世界則是內心的私人空間,處于私人空間中的小姐更多流露出的是對“心上人”的欲望和渴求。
這種借助屏風劃分空間進而輔助敘事的寫作手法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比比皆是,而對于中國現代小說而言,受敘事內容影響,如若繼續借助屏風作為劃分空間、輔助敘事的媒介,則顯得不合時宜。在這種情境下,王安憶小說創作中以明暗空間的對比代替古代小說中“屏風”的作用,通過對小說中空間的色調給予詳盡描寫達到劃分空間目的的寫作手法,為中國現代小說創作提供一種新的范式。
王安憶的許多小說都通過將晦澀陰暗的空間和明亮艷麗的空間進行對比,從而實現將一處空間劃分為兩處或多處的目的。作者利用空間的色調變化進行空間劃分,在渲染小說氛圍、彰顯作品主旨、呈現客觀生存環境等方面作用巨大。如《長恨歌》“愛麗絲的告別”一章里,已和“王琦瑤”心生嫌隙的“蔣麗莉”去找“王琦瑤”時,作者寫道這是一個“陰霾很重的下午,烏云壓頂的”,“天就要像擠出水來的樣子,陰的不能再陰。”作者對于天氣的描寫勾畫出一個整體沉悶、晦澀、壓抑的空間,這一空間的存在襯托出已被“王琦瑤”傷過心的“蔣麗莉”沉郁的心情。當“蔣麗莉”進入到“王琦瑤”家里時,她看到的是“客廳里很暗,打蠟地板反著棕黃色的光,客廳那頭的房門開著,有一塊光亮,光里站著王琦瑤”,“窗簾上透進些微天光,映在王琦瑤的臉上”。在這一部分敘述中作者將“王琦瑤”放在有光的空間里,從而和“蔣麗莉”所處的“陰的不能再陰”的空間形成鮮明對比,這種空間上的劃分不僅借助空間的陰郁感渲染了小說的氛圍。更為重要的是,“王琦瑤”的有光空間和“蔣麗莉”的暗淡空間的對比,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盡管“王琦瑤”居住在“愛麗絲公寓”這樣靠男人生活的地方,但“蔣麗莉”面對“王琦瑤”的風姿綽約,仍會頓時感到黯淡無光的事實。小說中,王安憶并未刻意描寫“王琦瑤”的高人一等,作者僅僅通過展示兩人所處的亮與暗的不同空間,便詮釋出上海女子“王琦瑤”雖命運波折卻依舊是時代的弄潮兒的小說主題。
小說創作中通過刻畫空間的不同色調進行空間劃分的寫作手法,對于作家實現敘事目的具有重要作用。王安憶作為一位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作家,她在小說創作中通過運用明暗空間的對比進行敘事的創作方法,促使她的小說因色調變化而生成更多的審美意蘊。
四、通過“空間表征法”塑造人物形象
人物是小說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與否對作品價值的呈現具有重要意義。凡是古今中外經典小說作品,其間都有讓人印象深刻、難以忘懷的人物,如《紅樓夢》中的寶玉、黛玉,《巴黎圣母院》中的愛斯梅拉達,《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等等。小說創作中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有很多,憑借動作、語言、心理等描寫展現人物是多數作者普遍使用的藝術手法,而“通過在敘事作品中書寫一個特定的空間并使之成為人物性格的形象的、具體的表征,則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種新方法——空間表征法”。[3](P51)
“空間表征法”在塑造人物形象時作用巨大,不僅可以塑造集體性格,還可以呈現個體性格;不僅可以塑造典型人物,還可以刻畫多層次人物。作家創作時可以采用“空間表征法”描寫人物群體生活的公共空間,如花園、街道、廣場等,借由公共空間的特征襯托集體普遍的精神面貌;與此同時,作家還可在公共空間之外為主人公營造個體生活的私人空間,如私人住宅、某個只有主人公自己知道的隱秘場所所等,這種私人空間的存在更有利于展示人物回歸自我時的本質特征。我國古典名著《紅樓夢》中黛玉的“瀟湘館”、寶玉的“怡紅院”、寶釵的“蘅蕪苑”等私人空間的描寫,就在塑造人物形象時發揮巨大作用。此外,作家在小說創作時也可以通過描寫不同空間中的異質性,暗示處于這兩個不同空間中人物本質的沖突,如許多小說作者就借此表現城市人和鄉下人在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上的矛盾。
王安憶在小說中塑造人物形象時頻繁地運用“空間表征法”,不僅通過細致刻畫人物生活的公共空間展示人物和社會文化背景的關系,而且還投入大量筆墨對人物生活的私人空間進行冗長瑣碎的描寫,進而展示人物內心的思想流動狀態。在《乒乓房》里,作者寫道“我們”居住的公共空間有著“明朗整潔的街面,殷實樸素的日常生計”,可是“在我們所住的同一條馬路上,越過一道橫街······明亮的街景也頓消,取而代之的是森涼的水泥氣味”,這便是“微弱的散發著一些銅臭味的”乒乓房。作者著意展示乒乓房中閑逛的“社會青年”的“頹廢的、沒落的、腐朽的”臉色,與“幽暗而陰沉的”乒乓房彼此協調,借乒乓房中黯淡的氛圍展示處在時代變遷中部分“社會青年”落寞和萎靡的心理。同時作者又通過描寫乒乓房“窗戶外面,那葉片枝頭上跳躍著陽光的梧桐樹,明亮得、明亮得就像另一個世界,一個理想的世界,天堂”,將乒乓房內部空間的頹廢和外部“天堂”式的公共空間進行對比,表現出舊時代培育下成長起來的“社會青年”和新時代的不相容性。小說中,作者并未著意描寫人物外貌,也沒有對人物心理進行深入的分析,而是僅僅通過展示乒乓房內部的腐化氛圍,以及這種氛圍和外部空間的沖突,襯托出當代部分“社會青年”的精神面貌。
王安憶運用“空間表征法”塑造人物形象,改變了以往較為陳舊的人物描寫手法,給人一種新奇感。“空間表征法”的運用不僅僅能夠從側面展示出人物內心本質特征,展示出人物之間、人物和時代之間的融合與沖突;更為重要的是,王安憶將“空間”視為創作小說時可以利用的要素,發揮了“空間”在寫作中的重要作用,無疑是對小說創作方法的開掘和補充。關于空間的重要性,福柯指出:“今天人們焦慮不安地關注空間——這很重要,它毫無疑問地超過了對時間的關注。”[5](P21)王安憶將“空間”融入到小說創作中,并不斷探索“空間”在小說中存在的重要意義,體現出她在開拓小說多種創作方法可能性方面的努力。